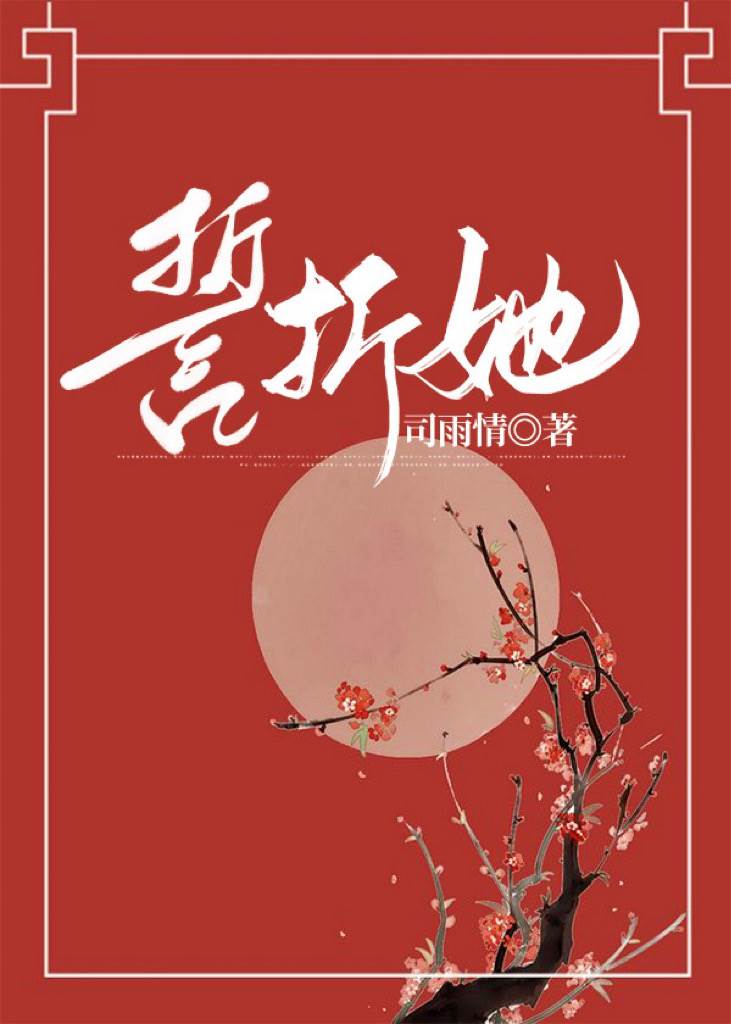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嫡女貴不可言》 第132章:溫叔叔回來了?
「這倒是有長進了,」喬玉言手了的臉,「看來容姐兒在這上頭有些天賦,這才拿起來就能看出問題,不錯不錯。」
喬玉容被這揶揄的語氣鬧得有些窘迫,氣哼哼地將賬冊放下,「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這點問題也看不出來?不就是幫著大伯母管家之時貪墨的嘛!」
「趨利而為,乃是人之本,實則無可厚非,只要不是太過,尚在適當範圍之,也沒必要太過追究,可若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很多事就很難說了,說不得就是再親近的人,都有可能會生出異心,更遑論其他。」
喬玉言的話說得喬玉容心下一,目落在那賬本上,似乎在思索什麼。
喬玉言也不說話,仍舊撥著手裡的算盤。
最近這段時間,姚家人又來了兩回,態度卻是一次比一次好,只把姚氏說了姚老太太最疼的兒,心底里最放心不下的那個,說得姚氏回回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好在喬玉容警醒,聽到靜就往母親院子里去了,瞅著機會就科打諢,愣是將姚氏守了個嚴嚴實實,沒能讓姚家人榨去。
姚家人踹了什麼心思,喬玉言看得一清二楚,只是在這件事中,終究是外人,還是個不怎麼悉的外人。
若是一個說得不好,反而生了嫌隙,所以乾脆就借著看賬本的機會,跟喬玉容掰扯掰扯。
Advertisement
第二日便沒見著自己那小堂妹了,也不知道是在搗鼓什麼,到了晚間似乎聽到二房有些靜。
事關人家的私,也沒派人去打探。
等去宋家的時候,喬玉容瞧起來就是神采奕奕的樣子了,喬玉言只但笑不語,也不多問,一心準備去宋家的正經事兒。
徐氏難得出門一趟,前一日還特意請了王太醫過來看過了。
太醫也知道伯府上下對這一胎的重視,細細地把過脈之後,才點頭笑道:「夫人如今脈象平穩有力,胎兒十分康健,只是看夫人狀態,應當是心中有些憂思難解,適當出去走走,於大人小孩都有利,不必過分擔心,反倒加重心理負擔。」
聽了這話,喬謂升和徐氏才算是放下心來,又打發人去跟喬玉言說。
雖然前兩天提過一,喬玉言還是沒有想到自己娘親竟然真的要出門,登時打起神,一面安排徐氏出行的馬車,一面將品蘭了過來,「去打聽一下,太太去宋家做客的主意是誰在老太太跟前提的?」
到了晚間,品蘭才得了確切的消息,「是從外頭聽來的,珍珠說,原是幾個老太太坐在一塊兒說笑,宋家老太太便說起了宋家剛出生沒多久的小公子,就自這上頭說起養胎來。」
品蘭想著珍珠的話,接著回,「是誰起得頭,珍珠已經記不得了,不過幾位老太太與咱們家老太太都是多年的手帕了,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Advertisement
聽到這麼說,喬玉言才略微放下了心,「明日府里沒人,多留意一下棲雲閣那邊,還有二房,若是姚家又來人了,就說二太太出了門了。」
「是!」
姚家發生了那麼多的事兒,姚氏縱然心裡對娘家有意見,卻也無法置事外,加上娘家時不時地就過來一趟,這段時間一直鬱鬱寡歡。
終日悶在屋子裡,也不怎麼出來走了。
這宋家的滿月宴,便直接派了個丫鬟過來說上不大爽利,不大方便過去。
老太太也不管,徑自帶了長媳和兩個孫兒出門。
老太太和徐氏一輛馬車,喬玉言和喬玉容便跟在後面。
一路上,喬玉容便小心地起簾子打量外面的店鋪,時不時地問起喬玉言關於經營鋪子的事。
也不知道怎麼忽然對這個興趣了,喬玉言只好盡自己所能地替解答。
只是兩世經驗加起來,這方面仍顯不足,也就只能隨意應答一二。
「你說書齋怎麼樣?讀書人總是肯花錢的。」
喬玉寧忽然指著馬車外的一家書坊問道。
喬玉言隨意一瞥,目卻登時頓住了,連忙起簾子往那邊看過去,果然看到溫停淵站在夢坡書齋裡面。
溫叔叔回來了?
這是幾時的事兒?
好幾次打發人去問,都說還沒回,難道是這幾天來的?
怎麼也不給帶個信呢?
思慮間,馬車已經轉了道兒,看不到那頭的形了。
Advertisement
喬玉容卻很疑,「大姐姐,你在看什麼呢?」
喬玉言與溫停淵的相識不好對外說,隨口找了兩句話敷衍了過去,姐妹倆又說了會兒話,馬車便到了宋家的側門。
宋家二太太帶著幾個府里的眷迎了過來,先跟老太太請了安,目便轉到了徐氏的肚子上,「都說你懷了孕之後,膽子變小了,大半年沒見著你走,可見還是我家的小孫兒面子大,將你給招出來了。」
徐氏便有些不好意思,「懷相一直不大好,出來沒得大家都張。」
一行人說說笑笑地便往正房去。
宋家大太太正在招呼裡頭的眷,宋家大跟在旁邊,一個抱著襁褓的婦人跟在旁邊被眾人簇擁著。
宋老太太坐在上首吃茶與眾人說笑,見著人來,親自下來,跟老太太說笑了兩句,又問起徐氏的飲食來。
屋子裡其他大部分也都是互相走的人家,說話間也沒有那麼拘謹,徐氏便被人簇擁著坐下了,宋大便機靈地母將孩子抱過去給瞧。
喬玉言這才和喬玉容一起給屋裡的長輩們請安。
也有沒見過的,這便拿了荷包過來,作為見面禮。
宋老太太便誇讚起們姐妹二人來,「真真一對姐妹花兒,一個端莊一個伶俐,還是喬家老姐姐好福氣。」
不過是客套的寒暄之詞,誰來都著待遇,喬玉言和喬玉容也都習慣了,只是含笑陪坐在一旁。
宋家大太太便小丫鬟過來,帶姐妹二人往宋家大姑娘屋裡去。
誰知才剛起,就聽到一陣悉的笑聲傳來,「我可來得不算晚吧!」
聽到這個聲音,喬玉言和喬玉容相視一眼,臉上的表都有些不大好,們怎麼也來了?
疑間,溫大太太便扶著溫家老太太的手一起進來了。
宋家老太太笑著走下位子,「這老天拔地的,你竟也過來了,今兒這是吹得什麼風?」
猜你喜歡
-
完結699 章

農門醫妃寵上天
家窮人弱?醫術在手,賺得萬貫家財,橫著走。 極品親戚?棍棒在手,揍他滿地找牙,誓不休。 流言蜚語?夫妻聯手,虐得小人自苦,猶不夠。 …… 深夜,蘇果抱著錢罐子數完錢,顰眉問:“相公,你瞧我們還缺點啥?” 宋安之漫不經心的撩著她的發:“嗯~缺人……娘子,不如我們來聊聊怎樣添個人吧。”
121.1萬字8 288981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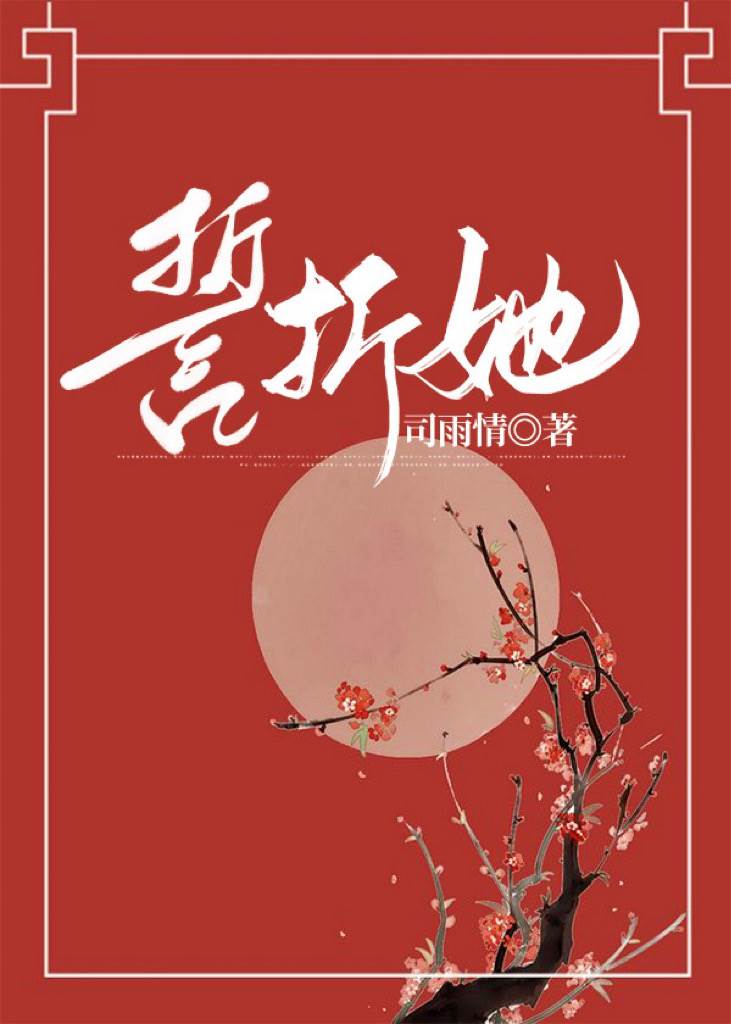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182 章

芳菲記/重生之盛寵
阿黎出生時就被睿王府討回去當兒媳婦,也就是定了娃娃親。據說是睿王府世子來吃週歲酒席,見她玉雪可愛,央着母親說要討她做媳婦兒。大人們笑過後,果真就定下來了。阿黎覺得沒什麼不好的。容辭哥哥長得好看,本事也厲害。教她讀書認字,送她華美衣裙,有時還會偷偷給她塞零嘴。後來皇帝駕崩膝下無子,睿王榮登大寶,容辭哥哥變成了太子哥哥。人人都說阿黎命好,白白撿了個太子妃當。阿黎不滿,怎麼會是白白撿的,她昨天還在太子哥哥馬車裏被欺負哭了呢。.世人都道太子殿下容辭,風姿卓絕、溫潤如玉。但只有容辭自己清楚,他是從屍骸堆裏爬出來的鬼。容辭跟阿黎做了兩輩子夫妻,可惜前一輩子他醉心權勢,將阿黎冷落在後院。他的阿黎,無怨無恨默默爲他操持家業,後來他招人陷害,阿黎也跟着慘死異鄉。上輩子重活,他步步爲營手刃仇敵,終於大權在握。轉頭想對阿黎好時,但晚了,阿黎病入膏肓香消玉隕。這輩子,他再次重生回來,早早地就將阿黎定下。權勢他要,阿黎他也要!他要寵她一世榮華!
26.4萬字8.57 37621 -
完結263 章

表姑娘
陳家有個生父不詳的表姑娘,還和京城的煞神許嘉玄結了仇。 眾人都看表姑娘熱鬧的時候,陳家卻在為這表姑娘張羅親事。 許嘉玄表示:誰娶誰倒霉。 沒過多久,給表姑娘賜婚的圣旨就砸到他頭上。 許嘉玄:???!!! 成親前的許煞神:士可殺不可辱。 成親后的許煞神:求辱。 ””追妻火葬場系
40萬字8 185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