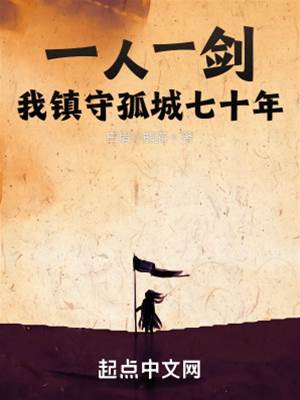《大明武夫》 1492.第1492章 聖君獨裁
「孔司長這可就小看我等了。」趙松微微一笑,「這些年來蒙皇上之恩,軍一直都在開展掃盲教育,有皇上的恩義關照,大伙兒都用心極了!這幾年我們裡面很多軍都已經學得很好,雖然詩作賦可能比不上那些積習多年的老秀才,但是天文地理,醫務理財樣樣都有的是人才,我看是不會比哪個閣機關要差的。如果監理礦山事務要靠舞文弄墨寫文章,也許我等還有些發憷,可是記賬算稅,這個我們可在行!另外,就算裡面有一二宵小之徒趁機弄鬼,軍法可是比國法還要嚴的,不管誰這麼大膽子,趙松也定能讓他死無葬之地!」
在孔璋趙松等人發言之後,其他來參會的文武大臣們也紛紛發言了,不過基本上文職的員附和丞相的意見,而武們則紛紛表示贊同元帥的看法,然形了一種文員集團對立的態勢。
丞相財相是今天列席的最高職位的文,而石元帥是列席的軍方最高職位的武,他們幾個人的影響力,在分列兩邊的文武大臣們中間必然會擁有巨大的影響力,他們幾個人的意見對立,當然也會為大臣們整之間的意見對立。
藉由對日本金銀礦的置一事,新朝從一開國開始部就暗中潛流的矛盾,終於公開地擺到了朝堂之上。而且在爭論當中,兩派人之間的火藥味也越來越濃,詞鋒也越來越激烈了。
「諸位大人,我明白諸位是想要將利源握在閣手裡,但是我等皆為朝中大臣,不可以私心忘國事!」石滿強元帥皺了眉頭,「這事自然要由駐軍來辦,才算妥帖!」
「為私心忘國事的人,到底是我等還是元帥呢?」平原侯冷笑著接過了話,「財計之事本來就是閣所管,天下民生更是閣所持,為何元帥要為這等利源來心呢?而且應由我等來議定的事,是否有無視閣之心?」
Advertisement
「我等怎麼會無視閣?閣是國家治政的最大依仗,誰敢無視?」石滿強元帥沉下了臉來,「我等只是為了更好地效勞君上而已,財相說我們有私心,我們哪有什麼私心?」
接著,他突然站了起來,然後朝皇上躬下了。「皇上,閣諸位大臣說臣有私心,臣一時無法辯駁,臣也知道,單靠臣自己用口舌是難以辨清的。因此,臣敦請將戰後派駐在日本的金銀礦監理機構由皇上親自統屬,由駐軍來負責,每年的出產和孳息由皇上帑一應理。請皇上聖斷!!」
新朝建立並沒有多年頭,雖然很多制度都按照皇上的喜好和現實需要進行了重大改進,但是因為畢竟上下力有限,所以很多制度依舊草草地予以沿用,國家的賬目財計即是如此。
在前明時代,朝廷的府庫和皇帝的私人財是分開的,那些遍布各地的皇莊以及宮中的帑也有專門的宮機關負責,朝堂的支出無法從中取,只能在有需要的時候進行借用。新朝也沿用了這個制度,不過因為之前大明皇室私有的皇莊和其他大部分產業都被沒收然後納了民政部和商業部等等閣機關來進行管理『以及雲山行也由閣來負責管理的緣故,所以新朝宮廷的帑規模比之前明要小了許多,皇帝的收也比前朝小了不。
也幸虧皇上和皇妃們都不好奢華,而且大大減小了宮廷宦和機關的規模,宮廷的支出比之前朝被到了一個極低的地步,帑所以倒也勉強能夠支用,偶爾甚至還有一點結餘。
正因為新朝的這個局面,所以聽到了石滿強元帥的話之後,丞相和財相都驟然變,一下子變得有些驚慌起來。
Advertisement
新朝皇家收不高,但是如果應了石滿強元帥之意見,將日本的金銀礦務由皇家直屬機關負責,並且進廷賬目的話,那況就會完全不同了,以日本的金銀礦藏之富,到時候皇家司庫的收將會為一個巨額數字,前明末年那種帑耗竭的況將不再出現。
所以,他們能夠想象到元帥的提議對皇上的吸引力,如果能把這些金銀礦務都納到手中的話,可比一座離宮要讓人心多了。
如果真要是沒皇上手中,他們倒也不是十分反對,畢竟皇上聖明,在閣缺錢的時候他肯定會從帑中撥款。但是石元帥的提議在他們看來,本來就是有私心的,扯上一個獻給皇上的名義,只是為了某一面大旗而已。皇上對軍隊一向偏,而且十分寬容,讓駐軍負責監理礦務的話,名義上歸皇上最後豈不還是讓軍隊達到了目的?
而且,在朝會辯論當中,居然把皇上作為大旗拉了上來……這真是讓人難以接。
「石元帥此言不無道理,我們都是大漢的臣子,孜孜以求的就是為了大漢,就是為了皇上的江山!打下來的東西,自然也都是為了皇上打下來的,直接獻給皇上並無不可。」丞相板著臉同意了對方的意見,「不過,正如我等之前所言,讓駐軍來負責監理礦務,弊多多,實在難以實行,不如現由閣建立新機構,獨立於其他部署之外,和皇上司庫合署,然後由這個新部門來監理礦務,這樣的話有專人為皇上理事,當為萬全。閣之中一片拳拳之心,都是為了讓皇上的天下更加穩固,還請皇上考慮臣之前所進之言!」
說完之後,他也和元帥一樣突然站了起來,然後也躬下了自己的,「請皇上聖斷!」
Advertisement
當今天在場的文武兩位最高臣僚同時站起來請求聖斷的時候,原本因為大家熱烈發言而變得有些吵鬧的會議大廳,瞬間就變得沉寂了下來,群臣再也沒有人說話了,大家要麼垂首不語,要麼就是地將自己的視線往皇上上瞟了過去。
文武兩方的意見對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明顯和尖銳過,兩方爭執了很久都沒有達共識,於是他們同時做出了請求聖斷的決定。
聖斷,就是最後的裁決了。
而太子,則被這一幕幕朝堂上的表演,弄得有些目眩神迷,他睜大了眼睛,視線四逡巡,想要從中找到一些自己可以領悟的規律。
群臣們的爭議,在他看來十分激烈,但是年紀尚小的他,還弄不懂兩邊為什麼突然會發出這麼激烈的爭執,在他看來兩邊都在高喊忠君,而且是大大的忠臣,他不明白既然想法一樣,兩邊還會這樣吵起來。
同時,他也不理解,為什麼自己的父皇竟然一直都默不作聲,任由這些文武大臣們吵起來,不顧朝堂大臣的統尊嚴。
他雖然年紀還小,但是也過多位老師長時間的教育了,因為他是太子,未來將會執掌國家的人。這些老師雖然很多觀點都不一致,有些傾向於儒學有些傾向於制之學,還經常教給他一些有衝突的觀點,但是這些老師有一點觀點卻幾乎是共同的,他們都認為朝堂不能陷到政爭當中,大臣們一旦政爭就會結黨,然後論人不論事,最後朝堂失控,群臣忙於互相攻訐當中,政事都會被放到一邊,國勢就會傾頹。
這些老師,都是從前明過來的,耳濡目染的都是前明末年東林黨和其他大臣黨派那腥風雨的朝堂鬥爭,有些人甚至還是當時那些鬥爭的見證者,自然,在大明亡了之後,他們就肯定會將群臣的政爭當是亡國的最大教訓之一告訴給太子了。
所以,太子就不太明白為什麼已經吵到了剛才的程度,父皇還是默不作聲。現在很明顯已經是吵得翻了天了,文武大臣已經各自集團對立了啊!
在群臣們吵得最激烈的時候,他渾然忘卻了自己今天只是作為旁聽者列席的事實,幾次想要出口發言,但是總是在最後的時候忍住了。他知道自己只是太子,不能夠在這種國事會議上面髮言。
可是,他心裡這麼著急,端坐在座上的父皇卻一直都紋不,這實在讓他大不解。
皇上一直沒有做出裁斷,群臣在等著皇上的聖斷,太子也在等著皇上給出個結果來,這種異樣的寂靜,讓每個人心裡都有些惶不安。
「請吾皇聖斷!」丞相再度深深地鞠了一躬,他害怕皇上出於老兄弟的舊面忘記了他之前的諫言,所以忍不住再催促皇上拿出決斷來,打掉這群軍頭的囂張氣焰。
他相信皇上是會聽從他的意見的,畢竟剛才私下的求見當中他已經說了很多道理,皇上這麼聖明難道會聽不進去嗎?再說了,他也已經承諾了讓皇上的府來私領那些金銀礦的監理權,只是讓閣負責執行而已——離宮,監理權,都已經到了皇上手裡了,他又有什麼理由不聽取閣的建議呢?
*******
謝謝大家的訂閱、月票和打賞,謝謝大家
猜你喜歡
-
完結288 章
小兵傳奇
他自小就有野心,希望當一個統領天下兵馬的元帥.他認爲要當元帥就要先當將軍,而要當將軍就要從小兵幹起.…
174.4萬字8.18 37396 -
完結498 章
上品寒士
現代資深驢友穿越到東晉年間,寄魂於寒門少年陳操之,面臨族中田產將被侵奪、賢慧的寡嫂被逼改嫁的困難局面,陳操之如何突破門第的偏見,改變自己的命運,從而維護自己和族人的利益?且看寒門少年在九品官人法的森嚴等級中步步攀升,與顧愷之為友,娶謝道韞為妻,金戈鐵馬,北伐建功,成就穿越東晉第一書。
129.9萬字8 18429 -
完結4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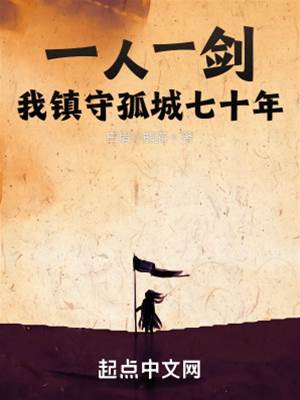
一人一劍,我鎮守孤城七十年
大漠孤城,褪色的戰旗,斑駁的白發,染血的長纓……宋云穿越到異世界的邊塞軍鎮,被老兵收留,成為城中唯一的年輕人。敵軍兵臨城下,三千老兵孤立無援,盡皆壯烈戰死。宋云撿起一柄青銅劍,成為安西軍鎮的最后一個守卒。一人一劍守孤城。只身獨擋百萬兵。從此…
84.4萬字8 18576 -
完結553 章
重生之大唐最強駙馬
一覺醒來,竟然成了大唐駙馬房遺愛。 (ps:本書為歷史小白文,相信各位看官不會失望滴。 )
132.9萬字8 18323 -
完結509 章
從嬴政開始:歷代皇帝陸續降臨
秦始皇死后,被傳送到了一座圍城之中。他發現這里的一天等于外界的一年。而且還會按時間線傳送來更多的皇帝。于是第三天胡亥到來:“父皇,您要為兒做主啊!”十二天后劉邦到來:“政哥,難道你還不知道你的大秦已經亡啦?哈哈哈...”王莽到來:“你們這群無知的古代人。”劉備到來:“高祖,我真的是咱老劉家的人!”武則天到來,驚呆眾人,變成團寵。成吉思汗到來:“論江山面積,我不是針對你,我是說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朱棣到來:“爹,你先別動手,兒不是故意篡位的...”溥儀到來:“我給大家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83.5萬字8 1335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