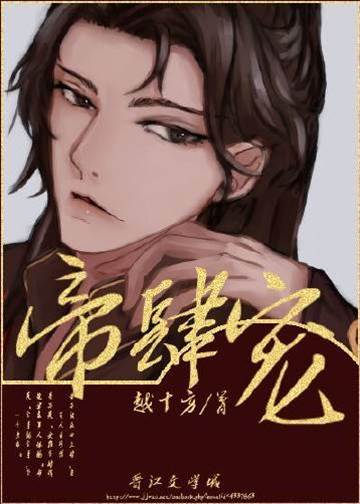《娘娘她千嬌百媚》 [娘娘她千嬌百媚] - 第 109 章
番外六
惟哥兒眼淚還沒有乾, 漉漉的狐狸眼清澈明亮,眼眸像兩顆黑玉珠子,正好和周津延目撞上, 週津延默默地手, 手掌蓋住他的小臉。(m.k6uk.com手機閱讀)
淡淡地說:“已經理乾淨了。”
安點點頭,見他擋住惟哥兒的小臉:“咦?”
“頭頂有燈籠, 對惟哥兒眼睛不好。”週津延只這般解釋。
安抬頭看看屋頂散發著芒的大燈籠, 覺得他說得對:“那度度你擋嚴實些。”
週津延薄微彎,低聲:“嗯。”
惟哥兒了擺在臉蛋旁攥小拳頭的手指,到週津延地手掌,又輕又。
週津延許是良心發現,托著他的脖子抱他起來,輕輕拍著, 哄他睡覺。
安坐在一旁, 看得眼熱, 亮晶晶地眼眸地看著他們,小臉寫滿了躍躍試, 也想抱抱惟哥兒。
週津延到刺人的目,低聲說:“等你養好了子再抱。”
安只能裹上的豹紋皮子,挪到他後, 看惟哥兒。
在周津延強勢的迫下, 安坐了雙月子,剛生出來還有些紅皺的惟哥兒, 現在已經長得白白,十分漂亮了。
惟哥兒得像豆腐, 很好的面頰枕在周津延肩頭, 長長的睫乖乖地散在眼下, 他閉上眼睛的模樣和周津延很像。
看得安心都要化了,忍不住湊過去親親他的小臉蛋。
惟哥兒睜開眼睛,看了一眼安的方向,又閉上眼睛,安心地睡,小小的瓣微微咧開,像是在笑一樣。
安鼻尖忽然有些酸,臉頰在周津延後背蹭了蹭。
聽周津延刻意低的的嗓音問:“怎麼了?”
安小聲說:“我們惟哥兒好幸福哦!”
Advertisement
靜謐的深夜,燭台了個燭花,週津延上粘著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兩個人,他目和,角噙著笑意,此刻幸福的不止惟哥兒一人。
把睡著的惟哥兒送回搖床,週津延回頭來找安。
橫抱起安,週津延眉頭忽而一皺,明明剛生產完,卻總覺得倒像是輕了許多。
把安塞進被窩裡,週津延也跟著上了床。
安帶著被子滾到他懷裡,週津延怕他睡夢中不小心到安,讓暫時一個人睡了一條被子。
這會兒想了想,還是手把拉進了自己的被子,摟,下顎抵著的發頂。
髮上殘留著濃濃的藥香,是今日中午嬤嬤們幫洗頭時留下的,週津延肩骨,竟一點兒都沒有。
低頭過淡淡的燭看小臉,掌大的面龐因氣不足,而顯得蒼白。
週津延心尖一痛,這些年養比養惟哥兒還細,陸翀常背著嘲笑自己把當小兒養,他向來不反駁,就這好不容易養來的,一下子又像是回到了從前。
安趴在他懷裡,瓮聲瓮氣地說:“度度,你抱好。”
週津延回神,手掌放鬆,了的肩膀,惟哥兒可,是他們滿心期待的骨,亦是捨了半條命生下來的,週津延不願意說什麼後悔的話,只暗自思緒養的計劃。
“困了嗎?”週津延低聲問。
安搖搖頭:“白天睡好多,現在不困了,想听你講故事。”
安孕後期夜晚偶爾睡不著覺,就听週津延講他手中那些神奇的案子。
週津延無奈,膽小,偏聽那些離奇又詭異的案子,越害怕越興。
安已經迫不及待地調整好了姿勢,側枕著周津延的手臂趴在他上,胳膊抱著他的腰,一隻兒翹到他上,這是最喜歡的聽故事的姿勢。
Advertisement
週津延眼裡閃過笑意,開口語氣也帶了笑,和咬耳朵:“等會兒怕了別啊!”
安下在他膛一啄一啄,不做思考地答應了,不過小手還是從他腰間挪開,放到旁,以免過會兒尖時摀住,別把惟哥兒嚇醒。
週津延著帳頂,在發頂蹭了蹭,倒有自知之明,握著的小手,薄輕啟,低聲道來。
不知何時屋外悄然落了雪,安枕在他懷中,呼呼大睡。
*
還有兩日便出月子了,安卻在屋裡憋不住了,趴在窗戶旁眼地看著雪景。
的那棵柿子樹立在院中覆滿了白雪。
經過五年的風吹雨打,柿子樹已經漸漸長大,生長茂,今年還結了好些柿子。
被安採摘下來,做柿子餅,現在正掛在廊下呢!
安“哈”了一口氣,小手明瓦窗,著窗戶歪頭瞧了瞧,的一串串柿子餅正在雪中飄揚。
安,彎著眼睛,笑得開心,再等一些日子就能吃到親手做的柿子餅啦!
還記得當初種樹的時候,就想著,有一日,能給哥哥姐姐,還有綰綰送上和度度親手所栽的柿子樹結的柿子做的柿子餅。
安莫名有些傷,麵頰,搖了搖頭,揮去腦中的綰綰的影。
抿笑了笑,吃了這麼些年外頭買的,這還是第一次親自手做呢!
安滿心期待。
這時珠珠帶著幾個侍僕抬了一個個大箱子進來。
是周津延怕趁他沒有防備,溜出去,派人抬了惟哥兒滿月時,京城各個家族,府邸送來的賀禮給拆著玩。
那日滿月禮實屬盛大,陸翀都親自過來了,除了一大堆金銀珠寶,還給了惟哥兒一塊他戴著的玉佩,惹得京城眾人十分眼紅。
Advertisement
而那塊玉佩現在,在惟哥兒搖床上掛著。
週津延說是用來辟邪。
安轉頭瞅瞅玉佩,也不知道落灰了沒有,不過有侍僕們打掃,應當沒有。
除了陸翀的賀禮,最厚的就是紀忱的了,紀忱很喜歡惟哥兒,安想可能是惟哥兒眼睛長得像舅舅。
們都說惟哥兒眼睛像,但安覺得男孩和孩還是有些不一樣的,私以為惟哥兒的狐狸眼和哥哥的更像。
陸翀和紀忱一個是惟哥兒的叔叔,一個是舅舅,厚些也正常。
但除此之外,收到的賀禮也不薄。
不過特別的是衛國公府送來的賀禮是分作兩份,一份是顧錚送來的,還有一份是顧家老宅送的。
安坐在坐榻上看老宅的賀禮,珠珠把一摞摞緻的紅漆盒子放到小几上。
“怎麼這麼多?”安看了看,驚訝道。
顧錚送的已經夠貴重的了。
“來老宅參加顧老夫人六十壽辰的親友們也送了禮。”珠珠說道。
安咬了一下,翻開禮單,找到末尾的裴家。
這裴家是顧大夫人的娘家。
上回在繡莊遇到的那個姑娘就是裴家的姑娘,很巧,竟然也與顧家有關係。
更巧的是裴文菀。
綰綰,菀菀。
安心中,忍不住的期待,但周津延說,這個小姑娘並沒有異常。
安找到裴家送的禮盒,是一隻水晶冠和一些尋常嬰兒佩帶的小金手鐲等飾品。
安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麼,默默地嘆了一口氣。
“誒,這隻小銀鎖真可。”珠珠拿起盒子裡的一隻銀鎖,嘆道。
安抬頭瞧了一眼,只是一隻樣式普通的銀鎖,剛準備收回目,就听珠珠說:“夫人你瞧,這鎖面兩邊刻的紋樣很特別呢!並不是是尋常的麒麟鸞鳥。”
安手:“給我看看。”
珠珠把小鎖放到手裡。
安舉到眼下,凝神一看,鎖面一邊刻的是柿柿如意,特別是圓盤上擺著的除了圓圓的飽滿的新鮮柿子,還有又扁又小的柿子餅,因為柿子餅不好看,很有人繡這個紋暗。
另一面更怪異了,竟是一隻小馬駒,這小馬駒的四隻格外的短,和養在馬場的那隻矮腳滇馬一樣。
安愣住了。
“是不是很新鮮,小世子肯定也喜歡,要不然放在一旁等小世子回來了,給他戴上去。”珠珠笑著說。
這會兒週津延正帶著惟哥兒在隔壁洗澡。
安卻是手掌一合:“不給,這是送我的。”
“好,好,好,夫人喜歡,那就是夫人的,我給夫人那瓔珞串起來。”珠珠點頭說道。
安眼眶慢慢的有些紅。
珠珠嚇了一跳:“夫人怎麼了?是我說錯話了?這銀鎖就是您的,不給小世子。”
“沒有,我沒事兒。”安搖頭。
安一邊說著,一邊飛快地趿拉起繡鞋,跑到櫃前,拿到一隻扁長的盒子,這只盒子裡放著綰綰送給的。
安蹲在地上,打開盒子的手有些抖。
好不容易打開,舉起擺,比對服上繡著的和銀鎖上刻著的柿子餅紋樣,低著頭眼淚忽然掉出來,竟然是一模一樣的!
而另一側的小馬駒……
安深吸一口氣,那日在場的除了和周津延,也只有顧錚和綰綰了。
安心尖都在,有些不敢往下細想。
“夫人,你怎麼了?”珠珠慌張地扶起來。
安吸吸鼻子:“珠珠,你幫我給這個裴姑娘下個帖子好不好?”
“就只有裴姑娘嗎?”珠珠連忙應聲。
安又怕這是多想:“你再隨便多請一些人吧!”
安攥著小銀鎖,看窗外,忽然扯了架上的披風係到肩頭,往外跑。
珠珠一個不覺,沒有攔住。
安走到廊下,踮腳紅著眼眶,期待地看的柿子餅,希真是綰綰,這樣就能吃到自己做的柿子餅啦!
安小手拉住掛著柿子餅的細繩,盯著黑乎乎的皺的一團,和上頭的灰斑,眨眨眼睛,像是呆了一樣,忽而臉一變:“哇!度度,我的柿子餅黴掉啦!!!”
猜你喜歡
-
完結245 章
愛妻如命之一等世子妃
大婚前夕,最信任的未婚夫和最疼愛的妹妹挑斷她的手筋腳筋,毀掉她的絕世容顏,將她推入萬丈深淵毀屍滅跡!再次醒來的時候,殘破的身體住進了一個嶄新的靈魂,磐涅重生的她,用那雙纖纖素手將仇人全部送進地獄!爹爹貪婪狠戾,活活燒死了她的孃親,搶走了她價值連城的嫁妝?用計把嫁妝翻倍的討回來,讓渣爹身敗名裂,活埋了給孃親陪葬!妹妹口腹蜜劍,搶走了她的未婚夫,得意洋洋的炫耀她的幸福?那就找來更加妖嬈更加勾魂的美女,搶走渣男的心,寵妾滅妻,渣男賤女狗咬狗一嘴毛!繼母狠毒,想要毀掉她的清白讓她臭名昭著,成爲人人可以唾棄的對象?用同樣的手段反擊回去,撕開繼母仁慈僞善的假面,將她狠狠的踩到泥濘裡!她手段殘忍,心狠手辣,視名聲爲無物,除了手刃仇人,她沒有別的目標,然而這樣的她依然吸引了那個狡詐如狐貍一樣的男人的目光,一顆心徹徹底底的爲她沉淪,併發誓一定要得到她!片段一:"你這個喪心病狂的女人連給露兒提鞋都不夠格,怎麼配做本王的未婚妻,定情信物還回來,別死皮賴臉纏著本王不放!看到你這張臉本王就覺得噁心."氣焰囂張的男人一手摟著溫柔似水的美人,一手指著她的鼻子罵道.
142.8萬字5 65928 -
完結286 章

神醫毒妃手下留情
一次意外,她和自己養成的偏執九皇叔在一起了。“幼安,你得對我負責。”“……”“請立刻給我一個夫君的名分。”震驚!廢物王妃和離之后,轉頭嫁給了權傾朝野的九皇叔。下堂婦?不好意思,她21世紀的外科女博士,京都第一神醫。窮酸鬼?各大藥行開遍全國,…
70.1萬字8 70228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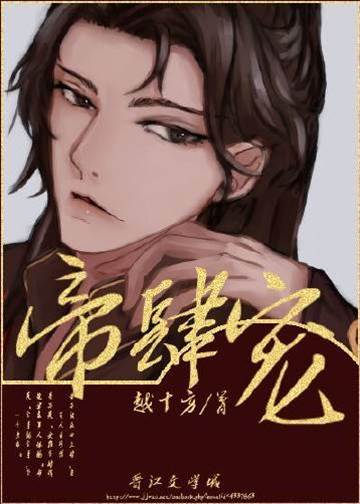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7151 -
完結296 章
恃寵為后
容晞是罪臣之女,入宮后,她將秾麗絕艷的姿容掩住,成了四皇子的近身婢女。 四皇子慕淮生得皎如玉樹,霽月清風,卻是個坐輪椅的殘廢,性情暴戾又孤僻。 宮人們怕得瑟瑟發抖,沒人敢近身伺候,容晞這個專啃硬骨頭的好脾氣便被推了出去。 一月后,四皇子讓容晞坐在了他的腿上,眾宮人驚。 六月后,四皇子的腿好了,還入東宮成了當朝太子,容晞卻死了。 慕淮面上未露悲郁之色,卻在一夜間,白了少年...
45.5萬字8 42165 -
完結149 章

摔鳳冠!剛和離攝政王就抬來聘禮
家破人亡前夕,沈玉梔匆匆出嫁,得以逃過一劫。成婚第二日,丈夫蔣成煜帶兵出征。她獨守空房三年,盼來的卻是他要納她的仇人為妾。沈玉梔心灰意冷,提出和離。蔣成煜貶低她:“你不知道吧,那夜碰你的人不是我。你帶著一個父不詳的孽子能去哪?還是識時務些,我才會給你和孩子名分。”春寒料峭,沈玉梔枯坐整個雨夜。第二日,帶著兒子離開了將軍府。全京城都等著看她的笑話時,那個冷厲矜貴、權勢滔天的攝政王霍北昀,竟然向她伸出了手!“本王府上無公婆侍奉,無兄弟姐妹,無妻妾子嗣,唯缺一位正妃。“沈小姐可願?”後來,前夫追悔莫及跪在她身後,攥著她的裙角求她回頭。霍北昀擁緊了她的腰肢,用腳碾碎他的手指:“你也配碰本王的妃。”沈玉梔不知道霍北昀等這一天等了十年。就像她不知道,在她做將軍夫人的那些年裏,這個男人是怎樣錐心蝕骨,痛不欲生過。
26.4萬字5 2300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