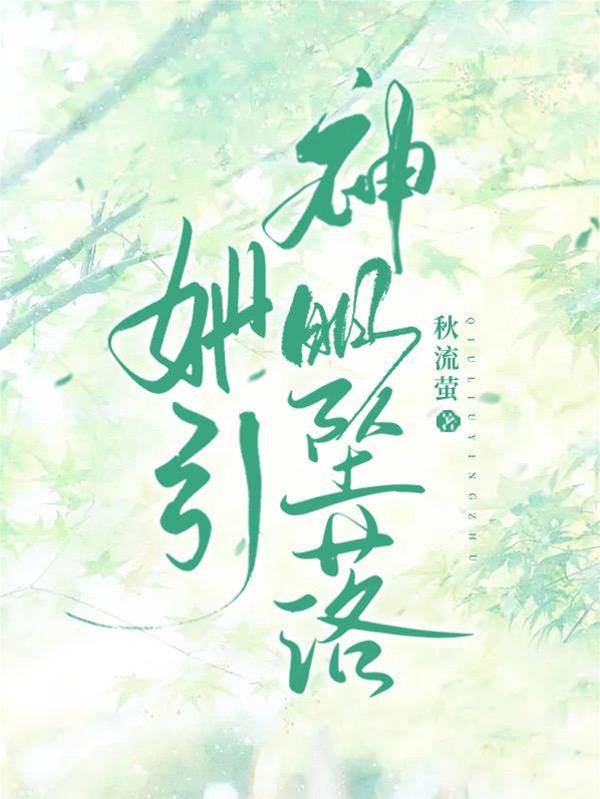《夢斷幽閣》 第259章 黃雀在后
回到家中的林子輝滿臉晦氣,氣沖沖地重重推開書房大門,夫人余氏不滿道:
“喲,你這是在跟我發脾氣呀?我還不是為你好。”
“為我好?你瞧瞧你這頭上的手上戴的,不是跟你說過了你不要這樣張揚嘛,你居然還這樣一副樣子跑進了節度使治所,這是想告訴滿天下的人,我林子輝有錢啊?你不是往火坑里帶我嘛。”
林子輝氣呼呼地一屁坐在椅子上。
余氏似乎也發覺了不妥之,忙將頭上的首飾摘了下來攥在手中,好言道:
“那阿濤過來報信的時候,我心里一急,這不是忘記了嘛。”
林子輝單手額,神郁。
余氏湊上前去,問道:“相公,他們不是只說問問話嘛,你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走到他后,討好地為他輕輕肩膀:“哎喲相公,庫房又不是你燒的,人也不是你殺,你什麼都不知道,他們能奈你何?”
林子輝喃喃道:“我就是心里不踏實啊。等阿濤來了再問問吧。”
余氏道:“相公送去的信,想必我表哥還沒收到,事急從權,相公你小心應對便是,他們沒有證據,不能怎樣的。等我哥收到信了必會給你個出謀劃策。別擔心,我去給你拿些點心來吃,咱們啊,吃飽喝足了再去對付他們,啊。”
言罷扭著走了出去。
林子輝心煩意,如坐針氈,起在房中負手踱步。
突然外面一陣碗碟墜地碎裂的聲音,隨即傳來余氏尖銳刺耳的謾罵聲。
林子輝此刻正心浮氣躁,一聽這靜剎時火冒三丈,真是心越煩,事越,他疾步沖出書房,咆哮道:
“吵死了,能不能讓我安靜一會兒?!”
于是便看見余氏掐著姚巧兒纖細的手臂從伙房門口一路將拖拽了過來,將狠狠“扔”到林子輝面前,氣急敗壞地吼道:
Advertisement
“我去廚房給相公你拿點心,誰知剛出門便一頭撞了上來,把盤子都打碎了,點心也掉地上了,我看就是故意使壞,不給相公你吃點心,定然是對相公你懷恨在心呢。”
姚巧兒一見林子輝那兇狠的幾乎要殺人的眼神,嚇的直往后退,滿眼的恐懼之,連連擺手,解釋道:“沒有,沒有,我是去廚房做事的,走快了些,不小心撞上姐姐了……”
林子輝雙眼惡狠狠地瞪著,緩緩向走去,“啪”地一記響亮的耳了過去。
“老子心里真是煩了。”
“啪!”
“怎麼會把你弄到家里來。”
“啪!”
“讓老子日日不得安寧……”
“啪!”
他每說一句就打一個耳,直打的姚巧兒的小臉紅腫變形,滿目驚恐,哭都已經哭不出來。
姚巧兒雙手抱著頭,口中連聲乞求:“老爺,別打了,巧兒再不敢了……”
余氏在一旁高聲罵道:“不敢?你還有啥不敢的?你就是個喪門星,從你來到我家,家里就不得安生,全是你造的,你這個賤人,為何勾引我相公,是不是就是故意來害我們的,啊?你這個不下蛋的母,你干脆早點死了算了,早死早投生……”
越罵林子輝心里越惱,這心里的火兒就不自覺地往頭上沖,他將滿腔郁結的煩惱化作重重一腳向姚巧兒踹去,將那弱小的子從廊下踹到了院子里。
如此他還不解氣,他沖過去一把抓住頭發將一路拖回廊下,將的腦袋一下一下往柱子上撞,“咚、咚、咚”直撞得額頭上鮮淋漓,頭暈目眩,再哭不出聲來,這才將重重扔在地上,拍了拍雙手,兀自咬牙切齒,心中恨意未消。
Advertisement
余氏幸災樂禍地看著那個躺在地上快死的人,滿眼笑意,上前挽起林子輝的手臂,撒道:
“相公別生氣了,別為這個賤人氣壞了自己子,一會兒為妻我再去做些點心來給相公吃,啊。”
二人頭也不回地進了書房。
姚巧兒側臥在地上,頭部鮮橫流,眼前金星冒。待得稍稍過一口氣,才緩緩從地上爬了起來,扶著墻壁,踉踉蹌蹌地向自己屋子走去。
廚房門前的阿秀遠遠看著,眼中滲出深深的同,但卻連過去攙扶一下也不敢,直到見姚巧兒搖搖晃晃地回了房,才悄無聲息地嘆息一聲,退進廚房。
林子輝有個兒已經十歲,如今在余氏娘家,而林子輝想生個兒子,余氏卻再未曾有孕,原本娶了姚巧兒想為自己傳宗接代,怎奈余氏兇悍,容不下姚巧兒,偏偏姚巧兒的肚子也不爭氣,至今未有一點靜,林子輝心中有氣,也就都撒在了姚巧兒上。
林家不過小門小戶,原本就只有一個丫頭一個伙計,伙計已經趕去京城送信了,丫頭阿秀不過十五六歲,平日里姚巧兒也要跟兩個仆人一樣做各種雜事,日常灑掃,買菜做飯都要做。
臥房中,姚巧兒獨自坐在梳妝臺前,看著鏡子里淋淋的自己,曾經的貌不再有,曾經那個被眾星捧月的梨園姚老板已不復存在,如今的不過是林子輝的妾室,一個任人凌辱的軀殼罷了。
三年前的這個時候,他每日去梨園看唱戲,送各種禮,生病了,他守在邊,為施針治療,他還時不時帶一些最喜歡的點心,他端正的相貌,他對自己的惜,他的每一份心思都讓不由自主地為他心,于是,在諸多追求者中,還是接了他,哪怕做他的妾室也心甘愿。
Advertisement
可是噩夢也是從那時開始,嫁給他不過短短半年時,由于大夫人的嫉恨,盡了折磨,拿當使喚丫頭一般,而他也漸漸變了,他開始什麼都聽大夫人的,對自己更是非打即罵。如今想來,他對自己的疼猶自那麼地清晰,卻已恍若隔世,的眼中沒有淚,沒有仇恨,有的只是充目的。
從桌上拿起一把剪刀,鋒利的刀尖緩緩頂住自己的咽,良久,卻沒有刺下,輕輕地,又將剪刀放在桌上,站起來,蹣跚著去了墻角邊,用手巾沾著水洗了臉……
一直等到戌時,阿濤還沒有來,林子輝在書房越發地焦躁不安, 晚飯后他終于坐不住了,告訴余氏他要去趟兵營,便匆匆離開。
不過一個時辰,他又行匆匆地趕回了,那臉比出去的時候更加難看,一把拽住余氏,將拉到了書房,閉大門。
見他神異樣,余氏不由得心中一,問道:“相公,你這是怎麼了?出了什麼事了?”
林子輝眼神慌,低聲道:“阿濤被抓了。”
“什麼?”余氏驚呼,忙手捂住自己的,低聲道:“他們怎麼發現的?”
林子輝道:“不知,聽說起初是軍需殷君瑤找阿濤對賬,阿濤不肯,殷君瑤一氣之下去柳奕之那告了他一狀,然后阿濤就被帶走了。”
余氏松了口氣,“嚇死我了,不就是被人告了一狀嘛,那應該不會有事的。”
林子輝道:“你懂什麼?要當真就是這點小事,人早該放出來了,怎麼到現在還關著?我還聽說啊,言虎搜了他的屋子。”
“搜屋子?”余氏的心又提了起來,“可是,他能有什麼好東西啊?”
林子輝急道:“你忘啦,他為我辦事,我不是會給他點意思意思嘛。”
余氏不屑地撇了撇,“那才幾錢銀子啊,總不會就為這點錢把人抓了吧。”
林子輝低聲音道:“你還記得吧,當初我給了王允一箱首飾,后來讓阿濤給我拿回來了。”
余氏點頭道:“對呀,不是在你這里嗎?”
林子輝道:“里面了一個鐲子,一珍珠項鏈。”
“什麼?”余氏怒道:“阿濤這小子居然敢咱們東西!”
林子輝神慌,沉聲道:“不行,我還是小心為上,萬一這小子把我供出來……”
余氏倒是不懼,嗤笑一聲:“他供你什麼呀?你一沒放火,二沒殺人,你怕什麼。”
“小心為上!”林子輝言罷搬了個凳子書架前,爬上去將頂部兩個上了鎖的方匣子都取了下來。
余氏問道:“相公,你又拿它做什麼?”
林子輝咬牙道:“小心為上,夫人,我要找個地方把它藏起來,你說,藏哪里合適?”
余氏雙眼滿屋子尋覓了一圈,指著墻角的柜子:“這里?”
“不行!”
“要不,藏屋里床下?”
“也不行!”
“這不行那不行,那往哪里藏啊?!”
林子輝咬牙想了片刻,說道:“你去看看外面有沒有人。”
“哦,好。”余氏輕手輕腳地走到門前,輕輕打開門,探頭向外張,扭頭低聲道:“相公,外面沒人。”
林子輝忙去找了一塊布來,將兩個匣子包裹起來,抱在懷中,打開書房門,探頭探腦,見各房都熄了燈,便沖著余氏招了招手,二人躡手躡腳走到院墻邊暗影下,將那箱子輕輕放在地上,他又去花圃中尋了一個鐵鍬來,在墻角地上開始挖土,忙活了好一陣,終于挖出一個坑,將箱子小心放進去,然后再將挖出的土重新填埋好,最后搬了一塊大石頭在上面。
待一切理停當,他夫妻二人才躡手躡腳地回了書房,將門關閉。
余氏說道:“這下就沒事了吧?”
林子輝著閃爍的燭火,眸沉而兇狠,咬牙道:“不行,阿濤必須死。”
他那蒼白的臉在燭的映下顯得尤為猙獰。
余氏道:“他如今關著呢,咱們沒法見到他啊。“
林子輝重重吐出一口氣:“等機會吧。“
他夫妻二人自以為一切做的神不知鬼不覺,殊不知,西廂房虛掩的窗中,一雙布滿的眼睛卻將這一切看的清清楚楚……
猜你喜歡
-
連載4114 章
罪妻來襲:總裁很偏執
易瑾離的未婚妻車禍身亡,淩依然被判刑三年,熬過了三年最痛苦的時光,她終於重獲自由,然而,出獄後的生活比在監獄中更加難捱,易瑾離沒想放過她,他用自己的方式折磨著她,在恨意的驅使下,兩個人糾纏不清,漸漸的產生了愛意,在她放下戒備,想要接受這份愛的時候,當年車禍的真相浮出水麵,殘酷的現實摧毀了她所有的愛。
361.9萬字8 23603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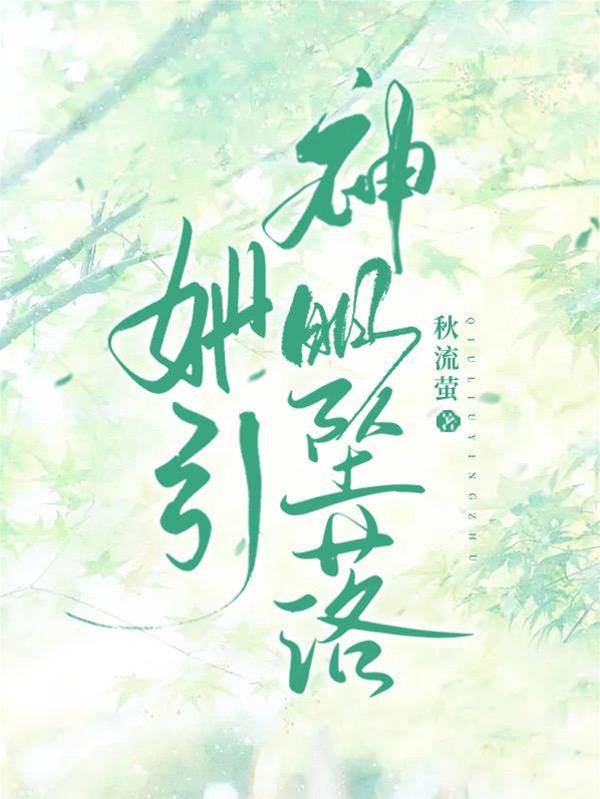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311 章

昨夜燈暖
三年前,蕭叢南被迫娶了傅燼如。人人都道,那一夜是傅燼如的手段。 於是他一氣之下遠走他鄉。傅燼如就那樣當了三年有名無實的蕭太太。 一夕鉅變,家道中落。揹負一身債務的傅燼如卻突然清醒。一廂情願的愛,低賤如野草。 在蕭叢南迴國之後。在人人都等着看她要如何巴結蕭叢南這根救命稻草的時候。 她卻乾脆利索的遞上了離婚協議書。
51.4萬字8 115868 -
完結120 章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
豪門小可憐?不,是你祖宗小說簡介:宋家那個土里土氣又蠢又笨的真千金,忽然轉性了。變得嬌軟明艷惹人憐,回眸一笑百媚生。眾人酸溜溜:空有皮囊有啥用,不過是山里長大,
22.5萬字8.46 589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