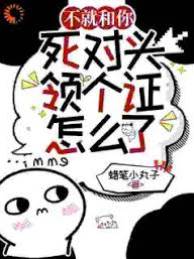《婚婚入睡》 第51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一章
六月中旬, 南城暑,下午五六點,天邊垂墜著火燒云, 荼蘼染天。
南煙那側車窗降下來, 熱風呼啦啦地往里灌,神平靜, 不急不緩地反問,“這些算是七八糟的還是算正經的?”
“不清楚。”齊聿禮說。
“那你清楚什麼?”
“你好像在生氣, ”齊聿禮眸微沉, “我惹你不開心了?”
“沒有,我沒有在生氣。”
氣溫灼熱, 空氣被太炙烤,熱風涌拂過臉,帶來揮之不去的燥意。車的冷風沒有任何作用,南煙手將車窗升上。燥熱好像順著管一路往下,鉆進的心肺里。
南煙稍頓, 好半晌,承認:“有一點兒不開心。”
齊聿禮:“我做什麼了?”
不是虛心求教的口吻,是不明所以卻又確定自己什麼都沒干的問。事實上, 齊聿禮確實什麼都沒干。
南煙想了想, 忽然道:“我做了個夢, 夢到你了。”
齊聿禮瞬間意會:“我在夢里惹你不開心了?”
“何止是惹我不開心了。”南煙半真半假地數著他的罪狀,“我夢到你才上高中, 就和班里一個同學眉來眼去。你倆在學校天天一起吃飯,你在籃球場打球, 就在邊上抱著你的服, 趁中場休息的時候給你送水。”
其實南煙也知道自己沒必要生氣, 他倆沒任何關系。可就是憋不住。
太喜歡了。
喜歡到要完蛋的地步。
原來喜歡一個人,是連他清白的過去都會吃醋。
真是要命。
完全控制不住。
聞言,齊聿禮皺了皺眉:“你覺得這像是我會做的事嗎?”
南煙:“像。”
齊聿禮眉頭褶皺更深:“你對我有什麼誤解?”
Advertisement
南煙添油加醋:“夢里后來,你和那個的還在教室……那什麼了。”含糊帶過,“這不就是你能做出來的事嗎?”
不是假的。
南煙昨晚真做了這麼一個夢。
甚至于夢境一開始,就是空曠無人的教室。原木的課桌擺放齊整,窗戶明亮幾凈,和煦,微風徐徐吹,白紗簾緩緩搖曳。
下課鈴響了許久,校園里也沒有人影。
驀地,教室門被人打開,一男一,前后走進教室。
看清了男生的臉,是齊聿禮,穿著附中襯衫校服的齊聿禮。
生的臉看不清,但潛意識覺得那是夏弦月,不是夏弦月也是別人,反正不會是南煙。他們差了五歲,齊聿禮上高一的時候,南煙還是個小學生。
要是南煙的話,那齊聿禮真的是個徹頭徹尾的大變態了。
齊聿禮和夏弦月停在課桌前。
兩個人什麼都沒說,只是一個對視,彼此便知曉對方的心意。
夢境就開始摻雜忌澤了。
然后南煙就醒了。
其實這個夢到他倆對視,快要接吻的時候就戛然而止了。但南煙醒來后,說不清是嚇的還是怕的,全冷汗。
“你出軌了。”南煙胡攪蠻纏起來,“你在我不在的時候出軌了。”
“……”
齊聿禮眉間褶皺更深。
他剛準備說話,車廂里響起短促繃的手機鈴聲。齊聿禮的手機鈴聲是手機自帶的鈴聲,一直沒換過,響起來的時候總有種催命的覺。
齊聿禮給南煙遞了一個“適可而止”、“等我接完電話再來教育你”的眼神,然后按下電話的接聽按鈕。
他沒有開免提,但手機那端的聲音清晰地響遍車廂,就連前排的司機和何銀礫都聽見了。
Advertisement
“齊三,附中后天百年校慶,咱們兄弟四個得去一個。”是霍以南的電話,“容四不是附中出來的,商二在國外,我最近有點兒忙,怎麼說,要不你過去?”
霍氏是附中最大的贊助商,每年給附中數千萬的贊助費。
附中校慶,自然要邀請贊助商出席并發言。以往這種活兒都是商從洲干,可商從洲好巧不巧,不在國。
齊聿禮想了想:“嗯,我過去。”
霍以南:“行。”
電話掛斷后。
齊聿禮一抬眸,正對上南煙水汪汪的眼,幽怨無比地盯著他。
南煙:“故地重游,舊復燃。”
齊聿禮抿了抿,耐心告罄,手,不帶任何溫地掐住的后頸,把的臉往自己上按。顧及車里還有其他人,他沒進行接下去的作,只是俯附耳,黯聲宣判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什麼:“到家后我有一萬種方式堵住你的。”
南煙掙扎。
齊聿禮空著的另一只手按住的腰,把死死地按在自己膝蓋上。埋在西裝面料里,不敢放大作也不敢大聲,嗚嗚嗷嗷的反抗著。齒呼吸間的熱意全都聚在一,他小腹一熱,險些控制不住,低聲呵斥:“別!再!信不信這會兒就讓你吃下去!”
“……唔,唔!”南煙瞬間安分了。
-
車子一停穩,南煙率先打開車門跑了出去。
任后的人怎麼喊“太太”,都沒搭理,管家困,太太平常端莊優雅的,怎麼今兒個躁躁的?
南煙不是躁。
是急躁。
別人可能是恐嚇一下,齊聿禮不是,他是說到做到的人。
南煙還在和他生悶氣中,不想往自己的里塞一些不該有的東西。
可是逃得了一時逃不了一世。
Advertisement
晚上洗完澡,二人還是得在同一張床上睡覺。
床很大,南煙占了非常小的一半,整個人幾乎是著床邊躺著了,剩下一大半的地方都給齊聿禮睡。顯而易見,要和齊聿禮這個夢中出軌的男人劃清界限。
齊聿禮向來不講道理,更何況——現在不講道理的人是南煙,不是他。
他洗完澡后,走到南煙睡的床這一邊。居高臨下地睨著。
南煙心虛地不敢看他,“你干嘛?”
齊聿禮:“說清楚。”
南煙:“說什麼?”
齊聿禮一聲冷笑:“為什麼突然來機場接機?”
南煙眨眨眼,忽然牛頭不對馬地來了一句:“你看窗外的月亮,下弦月呢,真漂亮。”話里有話。
齊聿禮甚至沒轉看,冷冷地提醒:“今天農歷初八,天上掛著的是上弦月。”
“……”
“你懂得可真多。”南煙沒想到他這麼煞風景。
“上過初中的都知道。”齊聿禮說。
“我沒上過初中。”南煙賭氣道,“我是小學生。”
齊聿禮對這胡攪蠻纏又無理取鬧的行徑向來采取一個措施,也是他當時所說的——睡、服。
南煙不太樂意:“你別我,你出軌了。”
齊聿禮邊拉開床頭的屜找到里面的塑料包裝制品,邊把死死地按在懷里讓無法彈,“現在說幾句,待會兒有你的。”
“……”
“……”
……
齊聿禮出差一個禮拜,像是要把這一個禮拜缺了的都給補回來。
南煙最后猶如條涸澤之魚,毫無招架能力。
也是到了這種時候,才是最無防備意識的乖,趴在他懷里,甕聲甕氣地說:“昨天齊月的生日宴,我遇到你以前的追求者了。”
二人都還沒去洗澡,他上有他的汗,也有的,更多的還是剛才苦苦求饒時落下的眼淚。
南煙了一口。
苦的眉頭皺。
顯得聲音更委屈了:“知道以前追求過你之前,我還覺得人好的,長得也漂亮的。我聽說還為了你考去哈佛了,家境好,學歷好,人又好……”
饒是圈赫赫有名的煙小姐,也產生了一卑微之。
“……誰?”齊聿禮一個字,瞬間秒殺所有。
南煙默了默,“夏弦月,你高中同學,你沒印象嗎?”
齊聿禮面冷淡:“確實是我高中同學,但考上哈佛了嗎?我沒印象,我出國是為了讀書的,不是為了和高中同學談的。”
這種嚴肅正經的撇清干系的模樣……
南煙后知后覺意識到,自己這醋吃的太莫名其妙了。
“如果你是因為這個和我生氣吃醋,煙兒,真的沒必要。”齊聿禮說,“我要真對有想法,我倆早就在一起了,就沒有你什麼事兒了。”
“哦。”南煙扯了扯角。
“又生氣了?”齊聿禮知的緒變化,“我說的是實話。”
“那麻煩你不要在剛做完的時候說這種掃興的話,”南煙也學著他說話的姿態,冷眸冷臉,如出一轍的高高在上,“的男人是會在這種時候調的。”
“的人也不會在這種時候提我沒什麼印象的追求者。”
“……”
“……”
一場無硝煙的斗爭,誰都沒贏,誰也都沒輸。
-
附中的百年校慶是在兩天后。
而兩天后,也是南煙的生日。
南煙不像齊月,過個生日要號召天下,恨不得把全南城名媛圈的人都喊過來替自己慶生。南煙并不熱衷過生日,也不過生日。
但生日這天天一亮,窩在齊聿禮的懷里,趁他還沒醒,就開始對他手腳。
齊聿禮被吵醒后,干脆利落地又著來了一頓。
早上九點多。
齊聿禮難得還躺在床上。
他手撥了撥南煙垂落的碎發,喑啞著嗓,戲謔:“怎麼這麼主?”
南煙聽到這話,忍不住抬踹了他一腳,“今天是什麼日子,你還記得嗎?”
齊聿禮:“附中百年校慶。”
南煙板著臉,不說話了。
齊聿禮沒再逗,清淺地勾了下角:“你生日。”他把抱在懷里,“生日禮已經送到你帽間了,除了服包以外,還有一枚鉆戒指,前陣子在蘇富比拍賣會拍到的。”
蘇富比拍賣會上的鉆都是fancy vivid purplish si1凈度的艷彩。饒是常年收貴重禮的南煙,也不由得心了一下,可沒忘記自己的主要目的:“再說吧,你又不是沒送我戒指過,我今天生日,你得滿足我一個生日愿。”
“什麼愿?”齊聿禮聲音沉啞,略沉,“除了要個小孩兒,其他都可以。”
“……”
南煙:“?”
猜你喜歡
-
完結321 章

戀著你眼紅紅
她被人下藥,一覺醒來,身邊躺著這個尊貴不可一世的男人。男人看她的眼神滿是嫌棄與恨意,她倉皇逃離。四年後,她被男人掐著脖子抵在牆上:陪酒賣笑的滋味怎麼樣?他是惡魔,一紙高價片酬協議將她給綁在身邊,受盡折磨。他為找人而來,男人態度強硬:把我的未婚妻弄丟了,你要賠給我,靳太太。 說出你的標準,我一定把人找來賠給你。”他喉嚨裏氣吞山河雲翻雲滾,最終化為一個字落地鏗鏘,你。我愛你,始終如一。
54.5萬字8 40428 -
完結706 章

快穿之做個好媽媽
現代女強人江瑛和女兒萌萌坐車時突然遇到車禍,女兒當場身亡,她悲痛欲絕時簽下一個契約,只要快穿到各個小世界中,做一個個好媽媽,挽救被壞媽媽傷害的兒女們,改變他們的命運,集齊10000個功德點以后,江瑛就可以重生,并挽救女兒的性命。于是江瑛穿越到各個世界,做起了好媽媽。各個世界更新中:懶惰至極的媽媽,重男輕女的媽媽,捆住兒子的媽媽,虛榮心太盛的媽媽......
143.5萬字8 6918 -
完結471 章

霸氣回歸,總裁嬌妻太撩人
[協議關係,複仇,追妻火葬場]洛熙玥為了擺脫前男友的控製,與前男友的小叔定下協議關係。明明就是協議關係,她卻先犯規愛上他。男人的白月光回來她上頭、她吃醋......他說:“我們之間明明就是你情我願的,你委屈什麼?”她回:“是我錯了,我改。”......從此,關上心門,請勿窺探。一次車禍曆經生死他終於覺醒直接把她寵上天好景不長男人中毒將他忘記她挺著大肚子在民政局跟他辦了離婚……一年後她霸氣回歸將男人撩撥得不要不要的......
79.5萬字8 4169 -
連載42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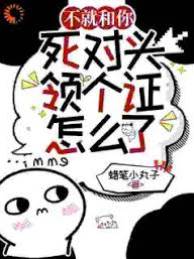
不就和你死對頭領個證,怎麼了?
第三次領證,沈嶠南又一次因為白月光失了約;民政局外,江晚撥通了一個電話:“我同意和你結婚!” 既然抓不住沈嶠南,江晚也不想委屈自己繼續等下去; 她答應了沈嶠南死對頭結婚的要求; 江晚用了一個禮拜,徹底斬斷了沈嶠南的所有; 第一天,她將所有合照燒掉; 第二天,她把名下共有的房子賣掉; 第三天,她為沈嶠南白月光騰出了位置; 第四天,她撤出了沈嶠南共有的工作室; 第五天,她剪掉了沈嶠南為自己定制的婚紗; 第六天,她不再隱忍,怒打了沈嶠南和白月光; 第七天,她終于和顧君堯領了證,從此消失在沈嶠南的眼中; 看著被死對頭擁在懷里溫柔呵護的江晚,口口聲聲嚷著江晚下賤的男人卻紅了眼眶,瘋了似的跪求原諒; 沈嶠南知道錯了,終于意識到自己愛的人是江晚; 可一切已經來不及! 江晚已經不需要他!
76.6萬字8 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