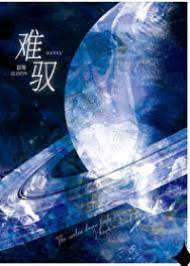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薄少追妻太上頭了》 第147章 珍貴的藥方
晚上九點半。
阮安夏拖著疲憊的形到了安寧醫院,才剛上電梯,就被人直接住了。
“夏夏!”
一道悉的聲音從旁邊傳來,隔著一些距離,立刻引起了不人的注意。
阮安夏下意識朝那邊看過去,果不其然看見了男人瘦削頎長的軀。
微微挑眉,小臉上還多了分詫異。
“你怎麼會在這。”
薄深白眨了下眼睛,聽見的話還愣了愣。
“夏夏,我怎麼不能在這啦,你難道忘記了之前我在電話里說的事?”
怔了怔,“什麼事?”
這讓薄深白到邊的話頓時收了回去。
他真是已經都說不出來了。
略微有些狹長的眸子瞇了瞇,仔細湊近看臉上的表,確定阮安夏是真的忘記了之后,才徹底的相信了。
“夏夏,上午我給你打電話的時候提到過的。七叔他生了病正在醫院住院。”
薄深白臉都快綠了,“難道你來醫院不是為了看他嗎?”
“不是。”
很明顯的道理。
阮安夏甚至直接越過他側朝旁邊走了過去。
而后再沒有回頭看一眼。
哪怕薄深白一直跟在旁邊提醒著,“就是最里頭守衛最森嚴的那個病房,等你空閑下來直接過來好不好?”
見阮安夏沒有理會他。
薄深白便簡單地說了幾句話,回頭往病房里走了。
病房里躺著的那個,現在還等著他過去復命。
Advertisement
原本薄深白還擔心著自己要怎麼代過去,現在遇到了阮安夏反而有自信心了。
“叩叩叩”敲門聲響起。
“進。”
薄云牧抬起頭,看著薄深白臉上的笑容,終于將手里的文件放了下去。
他并不說話,但眼神里的反應已格外明顯,就等著對方開口。
“嘿嘿。七叔,你猜我剛剛在走廊遇到誰啦?”
男人抬起了頭。
黑眸里著一些思考的緒,但從頭到尾都沒有開口說一個字。
薄深白笑了笑,把手里的東西放在桌上,主靠過去站在病床邊,靜靜看著他,“見到了你朝思暮想的人!”
話音落下。
薄云牧便立刻朝病房外看過去。
可房門虛掩,卻并不曾看見任何人影出現。
這番小表自然都會落在薄深白眼里,他假裝沒發現,低聲開口,“只是可惜了剛剛說還有點事要辦,沒過來。”
“現在是晚上十點。”
薄云牧嗓音冷。
言下之意,若是真要辦事,也不會這個時間點出現。
“對啊!我也是這麼想的。深更半夜的,除了來醫院探你之外,還能干啥對不對?”
空氣里的溫度好像都上升了不,這還是薄深白今天頭一次到那樣的舒適。
他很識趣地將東西放下,蓋子打開之后便往外走。
“這樣,為了避免尷尬,我呢就先回去了。七叔你好好在這里修養著。”
Advertisement
沒等薄云牧給出回答,他便已經直接離開了病房。
房門開了又關。
桌上的食散發著清香。
原本沒什麼食的薄云牧,此刻忽然對這兩碗粥有了興趣。
他拿起了勺子吃起來。
遵照醫囑,自然是要清淡為主。
而后很長時間都只是一個人在安安靜靜地食。
可就算他吃的再慢,半個小時過去,這兩碗粥也已經被吃了干凈。
而病房外依舊安靜,除了在門外候著的風颯之外,并沒有任何人經過。
意想中要出現的影,此刻并未出現在視線范圍。
薄云牧終于放下勺子,俊臉上好不容易緩下來的線條,在這一刻又變得冷起來。
而四下無人。
他低頭看了一眼手機上的時間。
晚上十點十五分。
就算是真辦什麼事,也早該辦完了。
“風颯。”
安靜的病房,薄云牧終于忍不住了人進來。
“七爺,有什麼吩咐?”
……
而在另外一邊的病房。
阮安夏抱著那個老舊的盒子走進去時,秦燕還沒有休息。
眼底甚至還有一些清清淡淡的笑容,看見過來,立刻拍了拍邊的位置。
“回來了呀。辛不辛苦?”
阮安夏如今風塵仆仆。
臉上著一些疲憊,但此刻看見秦燕氣還不錯的時候,便也松了一口氣。
轉頭將盒子放下。
“幸不辱命。就放在柜子最下面那層,還好找的。”
Advertisement
“這麼多年過去,也沒被人走就好。”秦燕出手著盒子上的銹跡,看著完好無損的鎖頭,長長松了一口氣。
阮安夏在旁邊坐下,大口大口喝水。
“看起來這麼破舊的東西,應該沒人要吧?最多被人走賣廢鐵。我們走的時候大家都知道能搬的都搬了,本來家里就窮,外公更是無長,我今天去的時候院子里的門鎖都還是好的。應該這麼多年都沒人進去過。”
秦燕的注意力都放在盒子上。
阮安夏看來回挲了許久,卻是從旁邊的柜子里拿出了一支小小的鑰匙。
折騰了好一會才打開。
“到底是什麼呀,看你還張兮兮的。”
湊過去看。
才發現里面靜靜躺著的是一個羊皮紙封。
乍一看只是很簡單的一封信件,細細瞧卻與平常的不一樣。似乎做過防水防理,這麼多年過去,也沒有損。
“夏夏,你還記不記得,當初你外公去世的時候,有幾位叔伯來過咱們家。”
“嗯嗯。說是來悼念外公的。還給了我們一筆錢。”
“他們都是你外公生前的朋友,但去找我們可不是為了悼念,而是另有所圖。”
阮安夏怔住。
“他們圖什麼?咱們家窮的都揭不開鍋。不然也不會接阮家的幫助來到市里。”
在的印象里,哪怕外公是圣手,平日里也救治了不人。
可大部分都是鄰里鄉親的,那幾年大家都困苦的,外公盡量開的都是能在山上采摘的草藥,不會跟那些無良醫生一樣,開一些高價藥品。
這也讓他行醫多年,沒什麼積蓄。
僅有的那點錢,那都花在秦燕治病上了。
而外公自己因為那次意外,早早病逝。
“你外公曾經留下了幾個方子,有的也只是常規的用藥法子,別的地方也能看到類似的。并不算突出,就像之前我給你的那兩個。”
“嗯嗯。第三個你說特別重要,是解毒的法子。”
所以哪怕當初跟七爺做了易,也不敢隨便出去這張方子。
秦燕點了點頭。
“但那還不是最重要的。”
說話間,已經將信封的那張羊皮紙拿了出來。
上面是用黑墨水筆寫著的藥方。
“這一張,才是最最重要的。而且一旦泄,我們可能會遭遇危險。”
猜你喜歡
-
完結1870 章

大佬的大佬甜妻
一次意外,她救下帝國大佬,大佬非要以身相許娶她。 眾人紛紛嘲諷:就這種鄉下來的土包子也配得上夜少?什麼?又土又丑又沒用?她反手一個大……驚世美貌、無數馬甲漸漸暴露。 慕夏隱藏身份回國,只為查清母親去世真相。 當馬甲一個個被扒,眾人驚覺:原來大佬的老婆才是真正的大佬!
169.3萬字8.33 11991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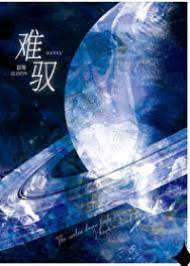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879 章

閃婚秘寵:首富大佬愛妻入骨!
為了擺脫原生家庭,她與陌生男人一紙協議閃婚了!婚后男人要同居,她說,“我們說好了各過各的。” 男人要豪車接送她,她說,“坐你車我暈車。” 面對她拒絕他一億拍來的珠寶,男人終于怒了,“不值什麼錢,看得順眼留著,不順眼去賣了!” 原以為這場婚姻各取所需,他有需要,她回應;她有麻煩,他第一時間出手,其余時間互不干涉…… 直到媒體采訪某個從未露過面的世界首富,“……聽聞封先生妻子出身不高?”鏡頭前的男人表示,“所以大家不要欺負她,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些千金富太太渣渣們看著他驚艷名流圈的老婆,一個個流淚控訴:封大首富,到底誰欺負誰啊!
163.7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