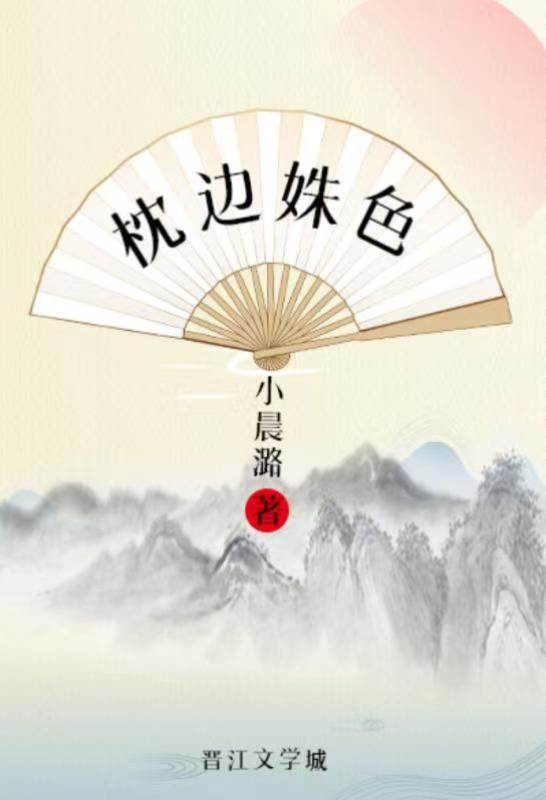《神醫毒後》 第一卷_第九十章 京都來使
夜黑風高。雲天傾關好五柳居的柴門,揹著行醫的包裹任命嘆氣,索著路去梅香園。忍不住安自己,去了梅香園就能看到耍寶的萬俟兄妹,就能看到容凌吃癟的表。還是很值得的,很值得的……一路自我安,到了梅香園門口,看到門口的兩個大紅燈籠,還是重重嘆氣: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呀。
話說,自從在五柳居見過容凌,萬俟兄妹一致認爲若是在梅香園找不到容凌,他就一定在五柳居,於是雲天傾的生活待遇一路飆升,同樣,清淨的日子一去不復返。每日和容凌一樣,要面對拿著大包小包禮品的萬俟兄妹,還要想盡方法解釋容凌的去。當然,容凌不了的時候的確在這兒,但很多時候,容凌找是爲了制的毒。本來容凌的已經好了七八分,但那晚因爲要接住從房上掉下來的,擅用力,一口真氣憋在口,雲天傾只能每晚給他鍼灸,緩解悶的癥狀。
各種原因之下,雲天傾好幾天沒給他好臉看,命令止容凌再踏五柳居一步……後來,只能每晚到梅香園去找容凌。
進梅香園,和預想中的喧鬧不同, 容凌一人獨倚在門口,顯得有些孤寂。夜悽迷,雲天傾只能從燈籠投出的暈中看到他的一個側影,側影後,是一道狹長的影子。見到來,容凌笑了一下, 像是紅塵中的萬家燈火綿綿不斷在黑夜中亮起,雲天傾的心猛烈跳一下。
“你來了?”他說。
“我不是每天都要來?”
從他旁進屋,把藥包放在桌上,打量著屋的陳設。雕花窗,屏風,榻,牆上掛著古琴,窗隴邊的香爐……這種陳設每見一次都想笑一次,不爲別的,就想看見獨屬於容凌的鬱悶表。這是的惡趣味。,明知道容凌最討厭被當人,還拿人打擊他,每每看到容凌強忍著發火的樣子,的心總是異常的好。
Advertisement
“我以爲你今天不會來。”他跟著進來,坐在榻上,給自己倒了杯茶。不急著喝,捲起袖子,放在榻上的小桌上。
茶香氤氳,雲天傾上容凌的脈搏,“還和昨天的況一樣,不用隨便用力,則一切與常人無異。”
“否則……”
深夜,二人獨坐,茶香纏繞在鼻尖,雲天傾有瞬間恍然,隨即挑眉,聲音有些飄渺,“否則,你就會昏迷,萬俟家的兄妹一定對昏迷的你很興趣,也許會一起上……”
“夠了。”容凌冷聲打斷。從的笑容中他猜出借來的意思。真不知道他扮人有什麼好笑,讓這個傻人笑了一路,到了鼎劍山莊還看他笑話。這分明就是權宜之計,有什麼奇怪的?
容凌收回手。雲天傾撇撇,心裡鬆口氣。從剛纔見到他,一切就很詭異,自己的心不自己控制地跳,好像發的小母貓。尤其容凌還倒杯茶,故意營造出曖昧的氛圍……雲天傾抖索兩下, 看他兩眼。
容凌沒發現,沉浸在自己的氣憤中,“從今天起,不許因爲我扮人發笑……算了,今天都過去了,從明天起……不行,以後,通通不能因爲我扮
人笑。反正事也快結束了,哼哼。”哼哼的意味不言而喻。
雲天傾抿看容凌法牢。容凌這般稚又真的樣子,不是第一次見,每次見到都驚喜一次,聽到後面,腦中一閃,“發生什麼事了?”頓了頓,說:“你說的快結束是很什麼意思?”
容凌出狐貍一樣的笑,細長的眼睛閃爍著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的幸福芒,端起杯子抿茶,“你不覺得萬俟兄妹今晚沒來煩我,很反常嗎?”
Advertisement
雲天傾大驚,愣住,“你,你,你,你希他們來?難道你習慣他們每天都來,偶爾一次不到你就覺得反常,那那那我呢,我也天天來,你是不是也習慣了?”
“啪。”茶杯掉了。
“雲天傾,你腦子裡都是啥東西?”
容凌說的認真,雲天傾被他唬住,腦袋,“能有啥東西?”
容凌深吸兩口氣,笑容燦爛,“今天來貴客,萬俟家的老爺子出門迎接,萬俟兄妹自然也要在迎接隊伍之中。這就是他們來不了的原因。”
“來貴客,……迎接……”雲天傾反覆咀嚼這些信息,垂下眼瞼,“也就是說,你找到突破點了。”記得那次灌醉萬俟無雙,他無意中鼎劍山莊的主要營生是鑄鐵,且震懾黑白兩道。自古以來,鹽鐵都是營,鑄劍需要大量的鐵和銅,鼎劍山莊一定和府有聯繫,再加上鼎劍山莊在黑白兩道的地位,說明和鼎劍山莊有聯繫的員職位很高。普天下,職位最高的是誰?當然是皇帝。也就是說,鼎劍山莊直接聽命與皇帝。而這次的貴客……
“明天,我們就去會會這個所謂的貴客。”燭火照著容凌的側面,安靜好燈下, 他用很淡的語氣說,雲天傾點頭,容凌又說:“燈火太亮了,你把蠟燭剪一下。”
雲天傾依言,取下蠟燭的紙罩子,拿起大剪刀剪掉蠟燭燃盡後多餘的線頭,燭火跳了一下, 雲天傾又把紙罩子罩上。
榻上的容凌目不轉睛看著雲天傾的作,只覺得燭火邊的雲天傾就像蠟燭一樣,散發著淡淡的芒,他驀地想起一句古詩,那人卻在燈火闌珊。是的,燈火闌珊,佳人靜。
Advertisement
“怎麼了?”剪完蠟燭的雲天傾看到怔愣的容凌,以爲自己做的不妥,“燈火太暗了?”
容凌眨眼,掩去所有的緒,“沒事。反正時間也早,不如手談一盤?”
雲天傾盤坐在容凌對面,看眼窗外漆黑的天,支起胳膊說:“行。”
容凌取了棋盤棋子,在小桌上擺開,“我讓你七子,不要說我欺負你。”
雲天傾執白先行,對他囂張的言語恍若未聞,笑容沖淡,“不會。”
燭淚乾,天已亮。
雲天傾放下意猶未盡,手中棋子盡數倒進棋盒,“沒想到,容小王爺是高手中的高手。”
“你也不錯。”容凌神嚴肅,“能在我手中走完整盤棋的人,屈指可數。能把棋下到這個程度,更是不多。”他想起在七裡臺的比試,爲了破陣把所有的空格都填滿。能使出這招的人,不是本就不懂下棋,就是已經到
底融環貫通以虛化實的境界。看來,他這個王妃是真的不會下棋,若是讓那個聲名赫赫的十三傑知道,他苦心孤詣擺出的棋陣被一個不會下棋的人破解,會不會再被氣吐?
“修生養,偶爾下著玩,還算說得過去吧。”雲天傾不在乎他的調笑,眉宇間一片坦然。
容凌看著黑白縱橫的凌棋盤,再次認識到雲天傾是一個徹徹底底的厚黑之人,臉皮很厚,心很黑。
鼎劍山莊招待貴客,定然有歌舞助興。
絞紗帳輕拂,薰香嫋嫋,管線幽幽。貴客李錦華裳,推開依偎在他邊的舞姬,舉起酒樽對坐在他旁邊的萬俟藝說:“李某人不過是個傳話之人,萬俟員外盛招待,真是太客氣了。”
萬俟藝連連擺手,“哪裡哪裡,李大人臨寒舍,是萬俟一族的榮幸。”飲下酒,“這是犬子萬俟無雙,奏樂之人是小萬俟唯一。讓李大人見笑了。”
萬俟無雙敬酒。李的臉笑花,“默契員外的公子小姐都是優秀的人,好福氣,好福氣呀。”
萬俟藝謙虛地說著“不敢”,揮手舞姬上前勸酒。
李左擁右抱,來者不拒。一直在他邊的舞姬趁機說:“萬俟公子年輕有爲,功當選上年度金陵第一公子,也是這一年度的最有希爲第一公子的候選人呢。”
萬俟無雙喝酒的作一滯,瞇著眼睛看說話的舞姬,舞姬只是低頭勸酒,李聞言,似是渾不在意說道:“每四年一度的金陵公子,本在京都也有所耳聞,只是本依稀記得,這競選前幾日就該結束了,怎麼還有候選人之說?”
他認識的“雲清”很有才華,他曾經一度很討厭這個人,甚至命令十三傑姬蒙不惜一切代價贏他,沒想到姬蒙戰敗,那時,他其實想殺了他。沒想到“雲清”還有個妹妹,那可是個傾國傾城的人。看在人的面上,他改變了主意,藉由和“雲清”相識的名義邀約那兄妹二人出遊,現在更是把人弄到府裡來。
這是很的事!
萬俟無雙不想任何人知道“雲清”的事,更不想人知道府中還有個“雲小姐”。這個舞姬引出“雲清”,使臣李很容易知道“雲小姐”的存在。若是李見起義,那時他還能“雲小姐”嗎?而且,這個舞姬引出“雲清”,是無意,還是有人授意?若是後者,主謀又是神馬目的?
萬俟無大腦飛轉,作仍舊謙和有禮,顯出世家公子的優雅風度,“此次金陵來了一位人,才華不再無雙之下,曾把頗負盛名的十三傑姬蒙氣得在千里臺吐暈倒。”
“還有這等人?我倒不曾聽說。不知我是否有緣見他一面。”李曾見過姬蒙,清楚那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現竟被氣得吐,一時對雲天傾產生極大興趣。
萬俟無雙微微一笑,“這位公子自稱雲清,和無雙一見如故,現在寒舍暫住。”
既然已經被人知道,瞞雲氏兄妹的蹤跡顯得可笑。常言道文人相輕,但也有人說惺惺相惜,把“雲清”捧得越高,他注意到“雲小姐”的可能就越小。就這麼辦。
(本章完)
分給朋友: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完結74 章
錯嫁皇妃帝宮沉浮:妃
一夜承歡,失去清白,她卻成了他代孕的皇妃。紅綃帳內,他不知是她,她不知是他。紅綃帳外,一碗鳩藥,墮去她腹中胎兒,她亦含笑飲下。惑君心,媚帝側,一切本非她意,一切終隨他心。
64.9萬字8 15557 -
完結568 章

爽翻天!穿到古代搬空國庫去流放
【空間 女主神醫 女強 爽文 虐渣 發家致富 全家流放逃荒,女主能力強,空間輔助】特種軍醫穿越古代,剛穿越就與曆史上的大英雄墨玖曄拜堂成親。據曆史記載,墨家滿門忠烈,然而卻因功高蓋主遭到了皇上的忌憚,新婚第二日,便是墨家滿門被抄家流放之時。了解這一段曆史的赫知冉,果斷使用空間搬空墨家財物,讓抄家的皇帝抄了個寂寞。流放前,又救了墨家滿門的性命。擔心流放路上會被餓死?這不可能,赫知冉不但空間財物足夠,她還掌握了無數賺錢的本事。一路上,八個嫂嫂視她為偶像,言聽計從。婆婆小姑默默支持,但凡有人敢說赫知冉不好,老娘撕爛你們的嘴。終於安頓下來,日子過得一天比一天紅火。墨玖曄:“媳婦兒,我們成親這麼久,還沒有洞房呢!”赫知冉:“想洞房,得看你表現。”墨玖曄:“我對天發誓,一輩子心裏隻有你一個女人,不,下輩子、下下輩子也是。”赫知冉:“你說話要算數……”
104.2萬字8.43 421630 -
完結347 章

娘娘總是體弱多病
邰家有二女,長女明豔無雙,及笄時便進宮做了娘娘 二女卻一直不曾露面 邰諳窈年少時一場大病,被父母送到外祖家休養,久居衢州 直到十八這一年,京城傳來消息,姐姐被人所害,日後於子嗣艱難 邰諳窈很快被接回京城 被遺忘十年後,她被接回京城的唯一意義,就是進宮替姐姐爭寵 人人都說邰諳窈是個傻子 笑她不過是邰家替姐姐爭寵的棋子 但無人知曉 她所做的一切,從來不是爲了姐姐 所謂替人爭寵從來都是隻是遮掩野心的擋箭牌 有人享受了前半生的家人寵愛,也該輪到其他人享受後半生的榮華富貴
52.3萬字8 52 -
完結3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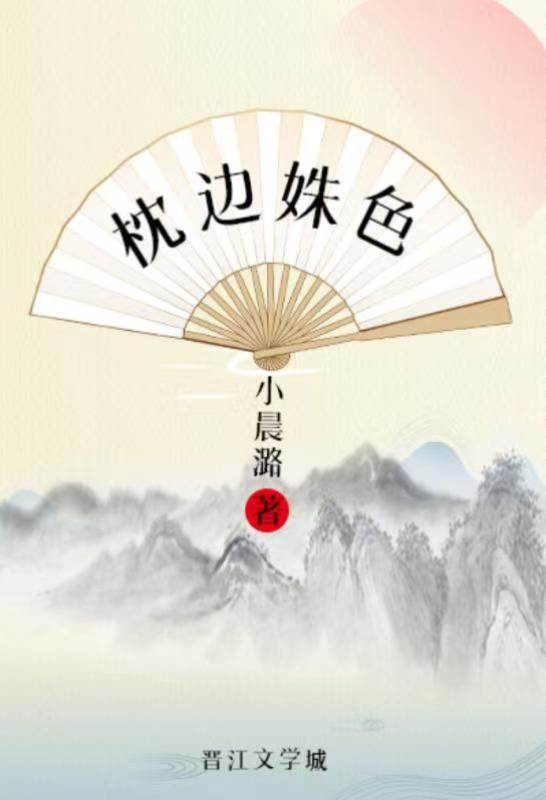
枕邊姝色(重生)
阮清川是蘇姝前世的夫君,疼她寵她,彌留之際還在爲她以後的生活做打算。 而蘇姝在他死後,終於明白這世間的艱辛困苦,體會到了他的真心。 得機遇重生歸來,卻正是她和阮清川相看的一年。她那時還看不上阮清川,嫌棄他悶,嫌棄他體弱多病……曾多次拒絕嫁給他。 再次相見。蘇姝看一眼阮清川,眼圈便紅了。 阮清川不動聲色地握緊垂在身側的右手,“我知你看不上我,亦不會強求……”一早就明白的事實,卻不死心。 蘇姝卻淚盈於睫:“是我要強求你。” 她只要一想到這一世會與阮清川擦肩而過,便什麼都顧不得了,伸手去拉他的衣袖,慌不擇言:“你願意娶我嗎?”又哽咽着保證:“我會學着乖巧懂事,不給你添麻煩……我新學了沏茶,新學了做糕點,以後會每日給你沏茶喝、給你做糕點吃。” 她急切的很,眸子澄澈又真誠。 阮清川的心突然就軟成一團,嗓音有些啞:“願意娶你的。” 娶你回來就是要捧在手心的,乖巧懂事不必,沏茶做糕點更是不必。
58.5萬字8 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