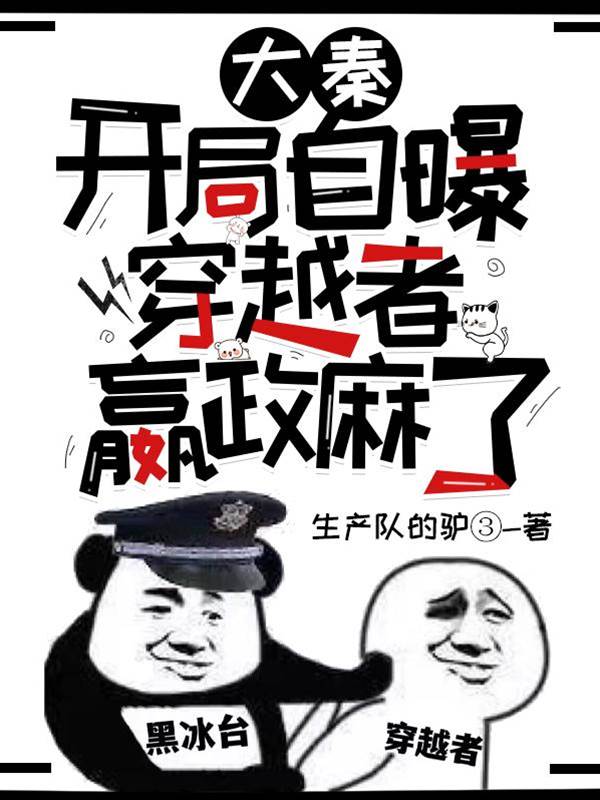《重生之大唐最強駙馬》 第五百四十一章抵死不認
「刑部?」
岑懋睜開雙眼,向房,喃喃道:「你要將我押解刑部?」
「那是自然。」房負手點頭,道:「不將史押解刑部,難道押解察院詔獄不?」
岑懋低頭沉思片刻,隨即緩緩起,湊到房面前,冷聲道:「駙馬是打算故技重施?」
「故技重施?」房眉頭微皺,掃了岑懋後的軍一眼,皺眉問:「此言何意?」
岑懋角上揚,做出了他被捕前的最後一次攻擊,「想當日蕭銳駙馬離奇慘死刑部天牢,駙馬莫非想要本得患鼠疫暴斃而亡?」
「蕭銳暴斃?!」
房星眸中閃過一抹寒芒,雙手微微攥拳,冷聲道:「蕭銳得患鼠疫人盡皆知,刑部、察院仵作皆以驗明正,史為何污衊房俊?」
岑懋輕哼一聲,慨然道:「難道刑部天牢中的耗子他姓房?!」
此言一出,房心生不快,可還沒等他出口駁斥,後的軍突然大步向前,一拳打在了岑懋的小腹之上。
「犯岑懋,再敢垢污皇家之事,立即綁縛東宮與太子殿下親審!」
聽聞軍的話兒,房繃著的神隨即鬆緩了下來。
「呼,好在軍沒有被岑懋誤導。」
對於岑懋的意圖,房瞭然於,他這樣做無非是想利用軍的耳目,將話語傳進馬監,再由馬監呈報駕親征的李世民,好上演一招「一損俱損」的戲碼。
可岑懋不知道,軍對於皇家之事想來諱莫如深,更何況房手持馬監票擬、東宮調令,軍自然會多偏向這位房駙馬一些。
岑懋半蹲在地,手捂小腹,晶瑩的汗珠兒早已佈滿了額頭,半晌這才斷斷續續的說道:「房俊!你分明就是構陷本!」
Advertisement
「是否構陷,刑部堂上自有公論!」
房不想與岑懋多費舌,冷哼一聲后,隨即對軍道:「將岑懋與其同黨押赴部堂!」
「遵命!」軍齊聲應和,隨即押著岑懋等人快步走下五樓二樓,沿著鬧市徑直朝六部所在走了去。
「岑懋!賊!」房眼岑懋等人離去的背影,恨聲道:「狗饞,時去到察院請李芳和朋三堂會審,諒你必定從實招來!」
來到刑部部堂,李芳和朋早已接到薛仁貴的通知,此刻雙雙坐在部堂正中,等待著房將岑懋押來審問。
「岑懋?察院的監察史?他怎會在五樓放火?」李芳著頜下長髯,自語道。
朋輕呷了一口涼茶,嘆聲道:「岑懋乃是長孫丞相的門生,今日恰逢國子監生員與長安試子在五樓展開對房駙馬的辯論,此舉分明借刀殺人。」
「呀!」李芳眸中閃過一抹憂慮,目掃向部堂門口,確認並無閑雜人等后,這才道:「若果真如此...牽連甚廣啊!」
朋點頭說:「若是太子殿下藉機...」
「賢侄,謹言慎行。」李芳揚手打斷朋,隨後道:「此事干係太大,不如去知會中書省?」
「中書省?三位丞相若是得知,怕是要引來山東士族與關隴門閥的較量了!」朋眼湛湛青天,慨然道。
李芳面為難之,頷首沉,「此事十分難辦啊!」
正當二人談間,房和薛仁貴袍走進部堂,眼李芳和朋,拱手道:「尚書、侍郎。」
「房侍郎。」朋和李芳起呼喚房職,隨後陸續開口道:
Advertisement
「賢侄,岑懋押來了?」
「賢弟,此事應當如何辦理?」
見二人言語虛浮,房心中暗想,「這是在詢問本宮的意見?還是將責任推在我的頭上?」
「算了!此事我既是苦主又是捉拿長,出一次頭也無不可。」
心中打定主意,房拱手道:「還請升堂三堂會審!」
「三堂會審?」李芳和朋對視一眼,臉上全都出了遲疑之。
三堂會審乃是專門審理事關重大案件的方法,像之前「蕭銳暴斃一案」李世民命魏徵、長孫無忌、馬周、蔡炳四人會審此案,又命高士廉、李孝恭、辯機和尚等人從旁觀審,為的便是公正公平,當然刑部堂上的三堂會審難比當初察院中的規模。
「賢侄,三堂會審未免有些小題大做了吧?」李芳沉思許,開口說道。
朋點頭應聲,「是啊,三堂會審岑懋...」
見二人言語閃爍,房苦笑一聲,拱手道:「既然如此,還請二位從旁觀審,房俊一人主審便是!」
「好,賢侄居刑部右侍郎,審理此案倒也合適。」見自己能事外,李芳忙不迭的點頭應允。
朋眸中閃過一抹愧,嚅囁道:「賢弟,此事...」
見朋臉有異,房搖頭道:「仁兄放心。」
三人商定決策,隨即由李芳出面,打開刑部案堂,來十幾名番子手持水火站立兩廂,而房則端居大堂公案之上,朋、李芳堂下左右而坐,薛仁貴則坐在李芳一側,行使其了刑部主事的權利。
等到案堂準備就緒,房一拍驚堂木,朗聲道:「帶人犯!」
Advertisement
自從在梅塢縣、曹州兩地歷練過後,房對於升堂問案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加之承蔡炳的「恩惠」,房駙馬的問案、唬人技巧又上了一層樓。
四名番子押著岑懋走進案堂,只見此時的岑懋早已被換上了一罪,手中帶著手肘,腳下鎖著鐐銬,樣兒十分狼狽。
「下站何人?」因為岑懋有職在,房倒沒有強迫其跪在堂下,只是居高臨下冷聲問道。
「察院監察史,岑懋,岑俊然!」岑懋字字鏗鏘,眼房毫沒有半點怯。
房微微點頭,再拍驚堂木,「既然是四品史,那就站著審吧!」
「房俊!」岑懋聽聞房的話兒,冷聲道:「你即無批票又無捕牌,怎能審理本?」
「捕牌?批票?」房側看向薛仁貴,問道:「四...薛主事,捕牌、批票可曾拿到?」
薛仁貴從袖中取出捕牌和批票,舉著讓岑懋看了一眼,朗聲道:「捕牌、批票俱已齊備!」
李芳見狀證明道:「捕牌批票乃是本親自發放,斷難有假!」
見刑部尚書都這樣說,岑懋沒了脾氣,只得站在堂下,昂然看著房,心中想著承東和長孫無忌早些得到消息,儘快來營救自己。
「岑懋,此刻你犯事在,本便不稱呼位了,直呼其名還見諒!」房聲道。
聞言,岑懋冷哼一聲,「虛假意!」
房不置可否,直正題道:「岑懋,此番五樓放火可是人指使?」
岑懋閉上雙目,抬頭面對房,心中早已打定了死不招認的念頭。
見岑懋拒絕回答,房再問道:「既然你不願招供,那本就再問你一事。先前長安城那首謠,可是出自你的筆下?」
此言一出,李芳、朋面帶震驚,就連岑懋心中也是錯愕不已,三人萬沒想到房已經知道了謠出自誰人之手的事。
「謠是出自岑懋之筆?」李芳頷首沉。
朋面帶慍,手指岑懋質問道:「犯岑懋!想你也是二甲進士出、天子門生。況且居察院史,怎能做出如此構陷皇家的詩句?」
岑懋睜開雙眼,看向朋冷笑道:「詩句?謠算是詩句?」
「本乃是兩榜進士出,怎能做如此鄙之謠?侍郎若要朋比為,還請選個高明的手段!」
此言一出,房眉頭皺,朋慍怒大起,手指岑懋同聲道:「何為朋比為?」
「侍郎的胞妹嫁與了房則,房則何許人也?你房駙馬的胞弟!」
說完,岑懋朗聲道:「房俊!殺人便刀好了!何必如此大費周章?本不服!本要去敲登聞鼓!」
猜你喜歡
-
完結971 章

明朝好丈夫
有知識、有文化、會治病、會殺人.很熱血、很邪惡,很強大,很牛叉.嬌妻如雲,手掌天下,不是很黃,但是很暴力.我是錦衣衛,我是贅婿,我是天子親軍,我是太子教父.我就是我,一個好丈夫,一個好權臣,正德一朝,因我而多姿,因我而精彩.
254.7萬字8.18 113823 -
完結247 章

強制歡寵:我的溫柔暴君
穿到書里,成了虐待過男主,最后被男主虐死的炮灰,還要得到邑界圖才能回去?夜沐表示,她沒時間玩游戲,既然被一本書弄進來了,那就弄死男主讓世界崩壞了出去!可看著面前骨瘦嶙峋,眉宇間卻滿是堅毅的小男孩,她下不去手……好吧,她被男主的王霸之氣給鎮住了!怎麼辦?養大男主,讓他去幫自己找邑界圖?這主意可以!但她養著養著,男主貌似長歪了!女主淚流滿面,說好的正直明君呢?她可以重養一遍嗎?
42.8萬字8.17 99710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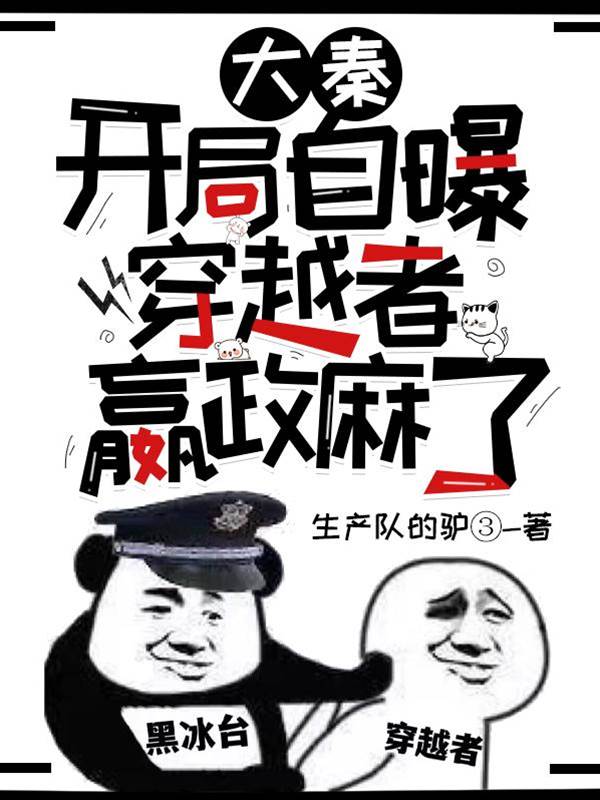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
完結118 章

七零后媽,反派崽崽買三送一
末世大佬林見月穿成七零年代小后媽人憎狗嫌還死了丈夫? 三個熊孩子張牙舞爪想趕走自己,唯一暖心小女兒快要病死 不慌,我有異能在手! 斗極品搞經商養的崽崽白白胖胖識文斷字。 多年后,新晉首富:我是我媽養大的;軍中上將:我也是我媽養大的;知名外交官:我也是! 世人都在感嘆單親家庭培育人才的不易。 只有被某生氣男人吃干抹凈的林見月暗暗叫苦,小兔崽子你們害死我了!!!
21.4萬字8 1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