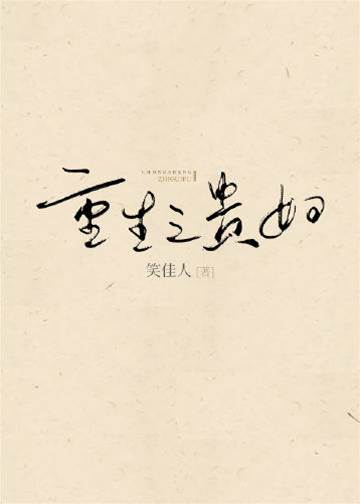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庶女毒後》 冷梅怎麼樣了
不知過了多久,只覺春風將的臉都刮疼了,才說,“好吧,你不說就算了。”說完,站起來,看他一眼,又道一句,“回去告訴你家主子,若是想監視季府,犯不著用這樣的方法,我祖母最大的牽掛就是我姑姑一家,若他們還在生,我希他們能繼續平安,而你的來意,我也不會過問。”在看來,這人選在這個敏的時間出現,冒充霍止零,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幾位皇子派進進府的探子,但是誰呢?太子?三皇子?二皇子?還是……五皇子?
若是最後一個的話,那不好意思了,要收回剛纔的話了,若是司蒼宇的人,這個妖孽般的年,就註定命損在這裡了,不會放司蒼宇的人活著離開。
霍止零端坐在石凳上,看著那道漸行漸遠的纖細背影,脣瓣揚起一道弧度,眼眸垂落,眼底掠過一淺薄的凜然。
這個季莨萋,到底以爲他是誰派來的?莫非這季府還是蜀國的政要大戶不?來之前他雖查的匆忙,但也知這季家雖是鎮國公府,但幾代下來早已名存實亡,如今空有爵位,卻無實權,是個閒纔是。可聽剛纔季莨萋所言,似乎有人盯上了季府,呵,他倒很好奇,這小娃以爲他是誰的人呢?
***
正式分權後,原本就不消停的季府頓時又起了漣漪,大夫人和二夫人因爲表姐妹關係,自然還是抱團,二老爺雖心有不悅,但眼下柳姨娘即將臨盆,比起整理家權這種一時半會兒也弄不好的事,他更專注於陪伴柳姨娘,畢竟二房這麼多年來就只有一個早夭的庶子,到現在還沒一個男丁,他是委實著急的。
而三房這邊,依舊如以前一般單一派,不過與以前不同的是,三房主攬下了照顧老夫人的活計,也自願承擔了老夫人在府中的一切開銷,往後老夫人的銀子不用從大房支付,三房原意全包,而在這種況下,或多或的,三夫人也連帶將季莨萋照顧上了。
Advertisement
所以府中的下人們漸漸發現,原本著簡樸的五小姐近些日子似乎排場越來越好了,服好看了不說,首飾也緻了,就連邊的三個丫頭也跟著水漲船高,著配件越來越跟大夫人房裡的人看齊了。
這就一人得道犬升天,看不出來這位五小姐倒是找到了好靠山,老夫人出山扶持了三夫人,三房和老夫人爲一黨,五小姐又和老夫人這麼親,而且聽說自從三夫人主擔負照顧老夫人的職責後,三夫人孃家的事也漸漸有了起,雖然田晨還是沒找到,但田家惹上的非卻給解決了,田家的生意能正常進行了,而有了田家的財力支持,三夫人倒是了這季家最有錢的一房了。
不過如今秦氏可沒空管三夫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午後,四香園裡。
大夫人一拍桌子,雙目霍冷的盯著面前的石媽媽,冷著臉道,“你說近不了是什麼意思?石媽媽,你該知道我沒什麼耐心,老爺現在天天往壽安堂走,就是去看那個小賤人,那小賤人現在仗著肚子裡有貨得意得尾都翹到天上了,再加上還有老太婆給撐腰,我若是現在不加行,難不我要看著十個月後平平安安的生下兒子,一家三口母慈子孝嗎?”
石媽媽經不住冷汗直冒,也知道原姨娘的事自己做得不夠好,但原姨娘現在天就躲在壽安堂,而老夫人又把壽安堂圍得跟銅牆鐵壁一樣,是把什麼花招都使盡了,可的人卻頻頻報來任務失敗的消息,這也沒辦法啊。
想了想,石媽媽還是道,“夫人,要不我們再等等,九個月的時間,或許還有……”
“要等到什麼時候?”大夫人氣得將手邊的茶杯揮到地上,“啪嗒”一聲,一地的碎瓷片在午後的下折出尖銳的炙,“我等不了了,天天看到老爺一回府就往那小賤人邊鑽,你知道我有多心痛嗎?你也知道我和老爺之間因爲兵部尚書一職有些小誤會,我現在急需找機會跟老爺培養,解釋清楚,可那小賤人就是算準了我著急,天天拖著老爺,專門給我使絆子,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晚解釋一天我和老爺的隔閡就越難清一天,我顧不了這麼多了,石媽媽,我要速戰速決,總之要先將原姨娘給我除掉,你放手去做,一切有我擔著。”
Advertisement
石媽媽愁眉苦臉的爲難極了,這不是誰擔著的問題,而是本沒有下手的機會啊。
這麼想著,腦子又轉了幾圈,突然想到,“夫人,既然府裡沒機會手,不如在府外吧?”
“府外?”秦氏來了興味,擡頭看著,“說來聽聽。”
石媽媽剛纔也是順這麼一說,可確實的計劃也沒有,正在這時,門外簾子突然被開,只見病弱纖的季靨畫在天梅的攙扶下,慢條斯理的走進來。
秦氏見狀,急忙起迎上去,裡嗔怪道,“你怎麼來了?誰讓你隨隨便便下牀的,你的子還沒好利索,要是落下病……”
“母親。”季靨畫拍了拍秦氏的手背,恬和的笑笑,“我的子已經好得差不多了,母親不用掛記我。”說著順勢坐到旁邊的椅子上,擡起頭問,“方纔在門口聽到母親和石媽媽在說什麼府外?什麼府外?”
秦氏嘆了口氣,秀的雙眼瞪了起來,“這些事和你沒關係,你子沒好,就不要管了,我自有分寸。”
季靨畫抿了抿脣,邊劃過一縷笑痕,淡淡的道,“母親說的莫非是七日後的釋迦尼佛誕?看母親說的,佛誕之日舉國同慶,怎能和我沒關係呢?我還想趁著那天與幾位姐妹一同到附近的寺廟裡去祈福呢。”
“佛誕?”秦氏愣了一下。
石媽媽卻一拍大,急忙道,“就是佛誕,老奴說的就是佛誕,夫人怎麼忘了,每年的釋迦尼佛誕府都要派人去寺廟祈福的,今年這任務不如就讓原姨娘去,原姨娘懷六甲,多與菩薩親近親近,來年也好爲我們季府生個小爺,夫人意下如何?”石媽媽說得冠冕堂皇,可臉上的笑卻邪惡險。
Advertisement
秦氏哪裡會聽不懂的話,眼睛瞇著思慮一下,便笑了起來,“好主意,就讓去吧。”
“母親。”季靨畫突然不悅的出聲,“母親也真是的,原姨娘帶著子,哪能去那種七八糟的地方,佛誕日寺廟門庭若市,人來人往的,若是傷著了肚裡的孩子怎麼好,還是換個人吧。”
“靨畫?”秦氏愣然的看向兒。只覺得兒是不是病糊塗了?“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季靨畫和一笑,臻首微垂,“我自然知道,這次佛誕日,兒想去。”
“你要去?爲什麼?”
“自然是爲了爲府祈禱,爲父親母親祈禱啊。”季靨畫自然而然的道,一點也不在意自己說了這種話,秦氏的表有多吃驚。
秦氏和石媽媽對視一眼,又轉回頭來,我這季靨畫的手,再的額頭。
“母親,你做什麼?”季靨畫失笑著將秦氏的手拿下來,淡笑著道,“母親不用覺得奇怪,佛誕日一年一度,這麼大喜的日子,我自然不願錯過,不止是我,還有府中幾位姐妹,聽說表哥也回來了,那就正好一起去,還有老夫人,老夫人信佛多年,想必這一盛會也是不會錯過的。”
“你……”
季靨畫繼續道,“想必那日一定很熱鬧,到時候府中就清淨了,剛好原姨娘子不適,就在府中好好歇息等我們回來吧,母親覺得可是?”說著,晶亮的瞳眸看向秦氏。
秦氏神複雜的看著兒,遲疑的點點頭,等季靨畫走了,才拉著石媽媽問,“你說靨畫是怎麼了?”
石媽媽笑道,“夫人,二小姐是說咱們將人都帶走,將府中空下來,好對原姨娘下手呢。”
“我自然知道的意思,可是爲何非要在府裡手?將原姨娘引出去手不是更乾淨利落,外頭的風險怎麼也比府裡大,原姨娘出了什麼事我們也好,但我聽靨畫剛纔說的,好像真的想去那佛誕一般,我怎麼不知道一病之後就對信佛有興趣了,我覺得有些不對。”
石媽媽聽完也點點頭,隨即道,“不如我去找天梅問問。”
秦氏沉一下,還是擺擺手,“算了,我想也是想出去走走,出了這麼大的事,總在府裡悶著心難免鬱卒,出去走走也好,剛好佛誕也是個好機會,就按二小姐說的做吧,回頭你派人去各房說一聲,表爺那你就親自去,表爺可不比得其他人,十歲就考了生,十六歲已是舉人,這等資質不是普通人有的,如今他寄居在府中,若是能將他拉到我邊來,也是個助力。”
“是,老奴這就去。”
季莨萋是在下午的時候收到四香園丫鬟的稟報的,坐在房間裡,手指挲著筆上的雕刻紋路,眼睛失焦的在滿桌的紙張上晃過,心裡想的卻是另外一件事。
小巧進來換茶,看到自己小姐皺著眉頭在發呆,不走過去問道,“小姐,可是有什麼心煩的?”
季莨萋垂垂眸,將筆擱下,慢慢的收著桌子上的紙張,緩緩道,“沒什麼,在想一些事。”說完又頓了頓,擡起頭來,“小巧,這幾日冷梅怎麼樣?”
“被關鎖了手腳關在柴房裡,小姐想到怎麼置了?”
季莨萋搖搖頭,隨即又道,“帶我去看看。”
分給朋友: 章節報錯
猜你喜歡
-
完結1931 章

女帝直播攻略
前世,薑芃姬是人類聯邦軍團上將,真正的人生贏家。 今生,她變成了普通的古代貴女,淒淒慘慘慼慼。 外有不安好心的係統,內有算計她的魑魅魍魎。 係統要她宮鬥當皇後,她偏要逐鹿天下當女帝。 圈地盤、募私兵、納賢士、建城池、打天下! 哦,最後還有睡美男—— 美男:啥?excuseme? #女帝進化日記# #未來上將在古代的諸侯爭霸之路# #直播,從一介白身到九五至尊# 問:不得不宮鬥,但又不想宮鬥怎麼辦? 答:乾死皇帝,自己當皇帝,宮鬥見鬼去吧。
353.8萬字6.1 7941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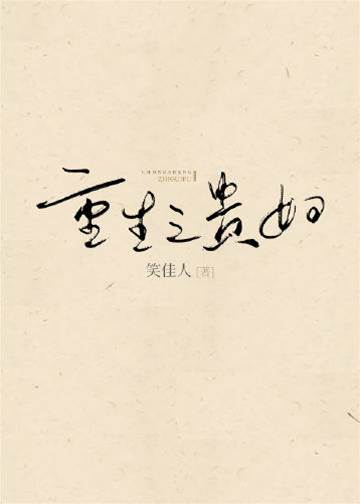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99 章

另謀高嫁,侯門主母誤惹奸臣
兵部尚書江府庶女江清月,代嫡姐出嫁,成了侯府主母。 江清月盡心盡力,卻被侯府老夫人當禮物送上了奸臣的床,為侯府掙前程…… 重生歸來,江清月大著膽子和奸臣做交易,把侯府要的東西通通截胡,打壓侯府不遺餘力。 侯府屢屢受挫,亂成一團,誰也沒想到溫婉賢淑的主母,穩坐高臺,是掌握這一切的幕後之人。 江清月成功和離,離開侯府,本想著離開這個是非之地,開始新的生活,卻被一人攔在城門外: “卿卿想去哪兒……”
33.6萬字8.17 5963 -
完結216 章

有嬌來
前世,定遠侯府滿門含冤入獄,身嬌體貴的宋五姑娘在被賣入勾欄紅院的前一晚,得那光風霽月的江世子相助,養於別院一年,只可惜宋五姑娘久病難醫,死在了求助江世子的路上。 【女主篇】 重生後的宋晏寧只想兩件事:一是怎麼保全侯府,二是怎麼拉攏江晝。 傳聞江世子不喜嬌氣的女子,被笑稱爲京都第一嬌的宋晏寧收斂脾氣,每天往跟前湊一點點,極力展現自己生活簡約質樸。 一日,宋晏寧對那清冷如霜雪的男子道:往日都是輕裝簡行,什麼茶葉點心都不曾備,可否跟大人討點茶葉? 後來,江晝意外看到:馬車裏擺着黃花梨造的軟塌,價值千金的白狐毛墊不要錢似兒的鋪在地上,寸錦寸金的雲錦做了幾個小毯被隨意的堆在後頭置物的箱子上...... 宋晏寧:...... 剛立完人設卻馬上被拆穿可如何是好? 清荷宴,宋晏寧醉酒拉住江晝,淚眼朦朧,帶着哽咽的顫意道:我信大人是爲國爲百姓正人的君子......,只想抓住幫助侯府的最後一根稻草。 江晝聞言眼底幽深,又些逾矩的用錦帕給人拭淚,看着姑娘因低頭而漏出的纖白脖頸,心裏卻比誰都清楚,他對她可稱不上君子。 世人都道江晝清風霽月,清冷剋制,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縱容和徐徐圖之......
34.9萬字8.18 105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