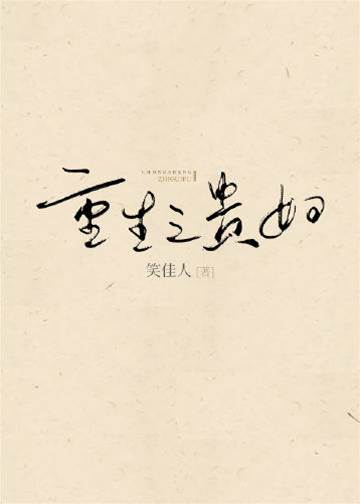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娘娘快跑您的昏君也重生了》 1417:番外:即將塵埃落定
自己沒憋住,不小心把自己的事兒給抖出來了。
時沉有些尷尬的撇開了頭:「我什麼都沒說。」
手腕倏地被贏紂抓住,時沉痛的皺著眉頭,抬眸對上了他不敢置信的神:
「你再說一遍,贏塵是你的什麼?」
「……」見他這模樣,心知自己是瞞不住的,時沉也不再瞞,回自己的手:
「你剛才竟然聽見了,還問我做什麼?」
贏紂狠戾的瞇起眼睛:「可你是怎麼知道的?是誰告訴你的嗎?」
「我——」
話已說出口,時沉斟酌一番。
有些事已經與從前不同,贏紂與之間這時候只怕是沒有太多的。
不能說出來。
「我只是想起來了,那時我在婚房外面遇到的事。」
手上的力道愈發重了:「來這一套,當日的事你絕對不可能記得!說!到底是誰?」
時沉跟自己的解釋又被瓦解,頭疼的翻了個白眼。
怎麼這傢伙這麼難纏?
贏紂看著的眼睛,相良久,他神微變。
「難不你也……」
「對!」
不想啰嗦,時沉坦然的看著他:
「托你的福,我也活了。」
贏紂瞳孔,愈發震驚:
「你怎麼會?」
時沉撇過頭不再看他。
贏紂接連追問:「是誰把你殺死的?是贏塵嗎?你怎麼可能死?!」
子被劇烈的搖晃了兩下,時沉眉心鎖,閉上雙眼:
「我是自殺。」
贏紂愣住。
「你自殺?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時沉雲淡風輕的說。
贏紂眼中卻起了笑意:「你自殺是不是想跟我殉?」
時沉滿臉問號,一掌朝他拍過去:
「你別臭不要臉,誰要跟你殉啊?像你這樣的人死了,我都是要放竹鞭慶祝的!」
贏紂輕笑一聲:
「還在說慌,你的生命不可能這麼短,縱然是贏塵不認,還有曲長笙,你還有你自己的生活,你活得會比誰都好。」
Advertisement
「……」時沉沉默了。
在他眼裏到底是怎樣一個狼心狗肺的東西?
眼睜睜的看著他死了,死在自己的前。
還能獨活不。
不過自己上了年紀,對於那些之事也不過分糾結,也不過份在意。
對於這段早就於下下輩子的糾葛,時沉避開不談:
「既然事已經發生了,也沒有辦法再避免,我也不能再多說什麼,只有一件事,贏塵絕對不能在贏灝的手中,他並非真心孩子,如何能夠帶好他。」
贏紂聞言,眉心鎖,他面上也有些許不願,但猶豫了片刻依然,面不改的說。
「我相信他能夠帶好。」
時沉就煩他這種生了卻不願意養的勁兒,怒火沖頭:
「你相信我還不相信呢,你又不能預知未來!我的孩子,難道我還不能管了不!?」
贏紂眸一沉:
「那不僅僅是你的,同時也是我的!如果你敢做出任何耽誤他前程的事,我不能保證我會對你做出什麼!」
「……」
氣氛僵住了。
時沉沉默的看了他半晌:
「你還真是一點都沒變,一樣的狼心狗肺。」
贏紂聞言卻是笑了,垂眸:
「對於我來說,江山是比兒長更重要的東西。」
時沉心頭一痛像是被誰陡然抓住了心口,想笑卻又笑不出來,轉過頭不看他,聲音卻微微起了抖:
「那我倒是要問你一個問題。」
他朝來。
時沉眸沉沉:「上一輩子我們兩個人之間是你滅了安樂國,而這一輩子你故意避開這件事。把功頭全部讓給了贏灝。
你後悔嗎?」
贏紂頓了頓,垂下眸子,沒有看:
「我沒有後悔。」
「不。」
時沉搖了搖頭:
「你後悔了。」
贏紂倏然抬眸朝去,眼中有被人破心思的窘迫,忽而又垂下眸,將自己的思緒掩飾的很好:
Advertisement
「我的一切都是為了贏塵,為了我們的孩子。」
「你為的是你的孩子。」
時沉聲音放得很輕,卻像是一把彎刀輕的截斷了他的話,將贏紂餘下所有的話都吞進了肚子裏。
時沉見他再度啞然,無奈的搖了搖頭:
「你從來沒有顧及過我的,一門心思的把贏塵打造一個殺人機,一個暴君。」
贏紂卻像是被到了逆鱗一樣,立即否認:
「他並不是暴君,贏國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安居樂業,國家繁榮昌盛,這是最好的徵兆,證明我當初的選擇沒有錯。」
時沉愣住了。
看著坐在自己前理直氣壯的男人,不知為何就酸了鼻子。
可能是一種心酸在作祟。
一個只會為了自己的兒子選擇皇位,而不會為了自己的選擇的人。
低下了頭:
「你知道我為什麼討厭你嗎?」
贏紂毫不猶豫:「我知道。我對你做了那麼多過分的事,你恨我都是應當的。」
時沉垂眸一笑:
「那我恨不得此時此刻就殺了你!」
笑的很好看,贏紂很見在自己面前這般笑過,他深深的看了一眼,最後說道:
「沉,當初我覺得我們有得選,我覺得只要我死了,重新回到過去,或許一切會不一樣,但當我發現我在改變未來的時候,也同時在改變贏塵的未來之時。
我才明白過來,有些事是不能夠做選擇的了。」
時沉靜靜的聽著,他的聲音很嘶啞,是在一開始毫無猶豫的選擇保護的時候所的傷。
而此時此刻在一開始被承擔的傷害,彷彿在這時候又悉數的奉還回來了。
贏紂抬眸:
「我今天選擇與你在一起,選擇保住安樂國,選擇繼承皇位。
贏塵就是另一個人,他不一定會為那樣一個能夠獨當一面的皇帝,不一定會跟曲長笙在一起。」
Advertisement
時沉攥住了拳頭,這種明知道命運如何想要改變卻又不能改變的,不甘,將包裹,讓過氣了。
「說到底我作為父王,是欠他的。」
贏紂輕輕說:
「而同時,在這與他相的五年之間,我也發現,我錯過了太多他最好的時,我已經很滿足了。」
時沉越聽越覺得可笑:
「是啊,你作為一個爹滿足了,那我呢?
我生養的孩子不認我,被人待足足幾年,上落得一病,我作為一個娘,在之前就沒有盡到養育他的責任,難道在這輩子也要眼睜睜的看著他苦嗎!?」
馬車驟然停下來,似乎聽到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爭吵。
而馬車一停,似乎就隨了贏紂的願:
「我這就下車了。」
時沉深吸一口氣,攥了拳沒理他。
「我阻擋不了你想什麼。」
贏紂著:「但是我要提醒你,你如果膽敢做任何要改變人生未來的事,我就不會對你客氣。」
時沉嗤笑一聲:「還沒有如喝,你就急著威脅我。」
贏紂起下車,冷漠的道:
「這是提醒。」
「對了。」
腳步一頓,贏紂復而又朝看來:
「我是想過好好的保護你,跟你在一起。」
「可是你與我之間註定不會像是他們那樣,能落到一個圓圓滿滿的團圓結局。」
他的聲音過分理智,理智得不夾帶一。
時沉攥了拳,額角青筋暴起,沒有說話。
車簾被人掀開,站在車門的人已經下了馬車。
趕車的車夫,有些顧忌的,掀開車簾朝看來,看到著難看的臉,猶豫著要不要開口。
時沉足足癮了好一會兒,見車夫言又止,緩緩閉上眼睛:
「走吧。」
「可是那位公子他已經。」
「不用管他。」
時沉眉心鎖:「我與他再無關係,如何就如何吧。」
-
睿王府。
贏灝憤憤的轉過,縱然上帶傷,也毫不影響他氣勢洶洶:
「贏紂竟然被人擄走了,可有線索留下來?」
贏灝府上的屬下稟告:「說是一個年,他帶了很多人,這個年的特點就是,聲音沙啞,而且劍基準基本上一件一條命,不過樣子和服沒有看清。」
「年……」贏灝細細斟酌一番,眼前一亮:
「難道是那個傢伙?」
門忽然被人推開,時沉姌大步流星的走了過來:
「就是那個沉!」
贏灝偏頭,看到時沉姌有些驚訝:「妃怎麼來了。」
「我是來給你看樣東西的。」
時沉姌打了個響指,後的侍在捧了一堆畫軸,時沉姌隨便選其中一幅將其打開:
「你來看看,這畫像上面畫著的,是個什麼東西。」
贏灝定睛一看,臉大變。
畫像上面掛著的紅子,這眉眼,他這輩子也忘不了:
「時沉?」
「是啊。」時沉姌冷著臉將畫軸放到了婢的手中,都沒有必要取消其他幾副展開來看:
「在搜查的時候我已經看過了,這裏面全部都是時沉那個人,不知道咱們這瑾王爺,留著時沉的畫像這麼多做什麼。」
時沉姌像是到了什麼污穢之,死勁的了自己的手。
「我看這件事沒那麼簡單,瞧著贏紂這樣子怕是喜歡我妹妹多時了。」
「你的意思是他喜歡時沉?」
贏灝卻不太相信:「無稽之談,就算是他再怎麼不近也絕對不會喜歡煽的呀,他們兩個人之間又沒有太多的糾葛。」
時沉姌見他這般篤定,不大高興的懟了他一下:
「誰跟你說他們兩個沒糾葛的,嫁給你那一年裏,你就能夠保證這時沉有沒有跟別的男人眉來眼去?」
這話倒是問著了贏灝,可是他腦子裏想一想贏紂那不近的樣子,完全聯想不到他竟然心裏都藏著這麼一個人,而且這個人還是他的前任王妃?
「我還是不相信。」
「你不相信是吧?」時沉姌怒其不爭的瞪了他一眼:
「我給你看證據。」
不由分說的一把抓住了贏灝的胳膊,帶著他離開了房間,徑直的朝最後面的一個間柴房裏頭去。
還未等進到房間里,房間就傳來了小孩子的哭聲。
隨即尖銳暴怒的聲音傳來:
「哭什麼哭?你這個掃把星!當我們睿王的小柿子,你就等著清福去吧,天天在這哭!你哭一次,我就打你一次!!」
他們在門口能聽到每次鞭子落在上的清脆之聲,孩子的嗚咽聲卻是再也聽不見了。
想想裏面是何等景,贏灝就覺得頭疼,並不想進去:
「你帶我來這裏做什麼?」
時沉姌雙手抱懷:
「你不是想要證據嗎?我思來想去,一晚上終於知道這最要的證據是什麼了。」
說著,猛的踹開了門。
拿著鞭子正舉手要打孩子的胖嬤嬤手一頓回頭朝他們看來,在看到他們的那一瞬間,臉上猙獰的瞬間變得笑意盈盈。
贏灝微不可察的皺了皺眉頭,沉眸看著在牆角,陷自閉的贏塵。
真是因為夏日,上只著了一層薄薄的衫。
衫已經髒了,甚至還被打了一個個的口子,上被得紫青鞭痕目驚心。
贏灝作為一個皇叔,到底是有些於心不忍的:
「怎麼就給打這樣子了?要是給打死了,你能賠罪嗎?」
胖嬤嬤一聽這話趕認錯:「奴婢該死,奴婢該死,奴婢下手不知輕重。」
贏灝哼了一聲:「不許這麼打他,要是再讓本王看到他上有一傷痕,我就拿你試問!」
「你兇什麼兇?」時沉姌不樂意了:
「這麼嬤嬤這般打,是我囑咐的,跟你有什麼關係?」
贏灝眼中閃過一抹不悅:「那你說你找我來這兒做什麼。」
「你不是想要證據嗎?」
時沉姌走到角落,要在角落的贏塵的頭強迫的給抬起來。
小孩子面無,臉上有一塊一塊的青紫,角還滲出了點點,被強迫的抬頭,他本虛弱的目中陡然增添了一抹怨恨。
惡狠狠的瞪著,恨不得將吞到肚子裏。
「看到了嗎?」時沉姌勾起角:
「你仔細瞧瞧,看他長得像誰?」
贏塵時有幾分像贏紂的,剩下那幾分是隨娘。
猜你喜歡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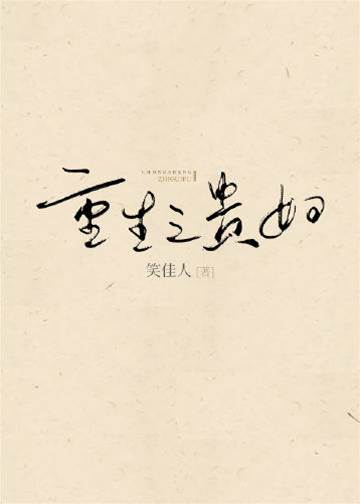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828 章

我是旺夫命
一朝穿越,鐘璃不幸變成了莫家村聞名內外的寡婦,家徒四壁一地雞毛也就罷了,婆婆惡毒小姑子狠心嫂子算計也能忍,可是誰要是敢欺負我男人,那絕對是忍無可忍!我男人是傻子?鐘璃怒起:這叫大智若愚!他除了長得好看一無是處?鐘璃冷笑:有本事你也那麼長。鐘…
170.9萬字8 233467 -
完結149 章

開封府美食探案錄
開封府來了位擅長食療的女大夫,煎炒烹炸蒸煮涮,跌打損傷病倒癱,飯到病除!眾人狂喜:“家人再也不用擔心我的身體!”但聞香識人,分辨痕跡……大夫您究竟還有多少驚喜是我們不知道的?新晉大夫馬冰表示:“一切為了生存。”而軍巡使謝鈺卻發現,隨著對方的…
45.8萬字8 13472 -
完結930 章

毒醫狂妃:誤惹腹黑九王爺
傳聞,相府嫡長女容貌盡毀,淪為廢材。 當眾人看見一襲黑色裙裳,面貌精緻、氣勢輕狂的女子出現時——這叫毀容?那她們這張臉,豈不是丑得不用要了?身為煉藥師,一次還晉陞好幾階,你管這叫廢材?那他們是什麼,廢人???某日,俊美如神邸的男人執起女子的手,墨眸掃向眾人,語氣清冷又寵溺:「本王的王妃秉性嬌弱,各位多擔著些」 眾人想起先前同時吊打幾個實力高深的老祖的女子——真是神特麼的秉性嬌弱!
153.2萬字8 334465 -
完結371 章

惑君
嫡姐嫁到衛國公府,一連三年無所出,鬱郁成疾。 庶出的阿縈低眉順眼,隨着幾位嫡出的姊妹入府爲嫡姐侍疾。 嫡姐溫柔可親,勸說阿縈給丈夫做妾,姊妹共侍一夫,並許以重利。 爲了弟弟前程,阿縈咬牙應了。 哪知夜裏飲下嫡姐賞的果子酒,卻倒在床上神志不清,渾身似火燒灼。 恍惚間瞧見高大俊朗的姐夫負手立於床榻邊,神色淡漠而譏諷地看着她,擡手揮落了帳子。 …… 當晚阿縈便做了個夢。 夢中嫡姐面善心毒,將親妹妹送上了丈夫的床榻——大周朝最年輕的權臣衛國公來借腹生子,在嫡姐的哄騙與脅迫下,阿縈答應幫她生下國公府世子來固寵。 不久之後她果真成功懷有身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嫡姐抱着懷中的男娃終於露出了猙獰的真面目。 可憐的阿縈孩子被奪,鬱鬱而終,衛國公卻很快又納美妾,不光鬥倒了嫡姐被扶正,還圖謀要將她的一雙寶貝兒女養廢…… 倏然自夢中驚醒,一切不該發生的都已發生了,看着身邊沉睡着的成熟俊美的男人,阿縈面色慘白。 不甘心就這般不明不白地死去,待男人穿好衣衫漠然離去時,阿縈一咬牙,柔若無骨的小手勾住了男人的衣帶。 “姐夫……” 嗓音沙啞綿軟,梨花帶雨地小聲嗚咽,“你,你別走,阿縈怕。” 後來嫡姐飲鴆自盡,嫡母罪行昭彰天下,已成爲衛國公夫人的阿縈再也不必刻意討好誰,哄好了剛出生的兒子哄女兒。 形單影隻的丈夫立在軒窗下看着母慈子孝的三人,幽幽嘆道:“阿縈,今夜你還要趕我走嗎?”
61.6萬字8 10053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