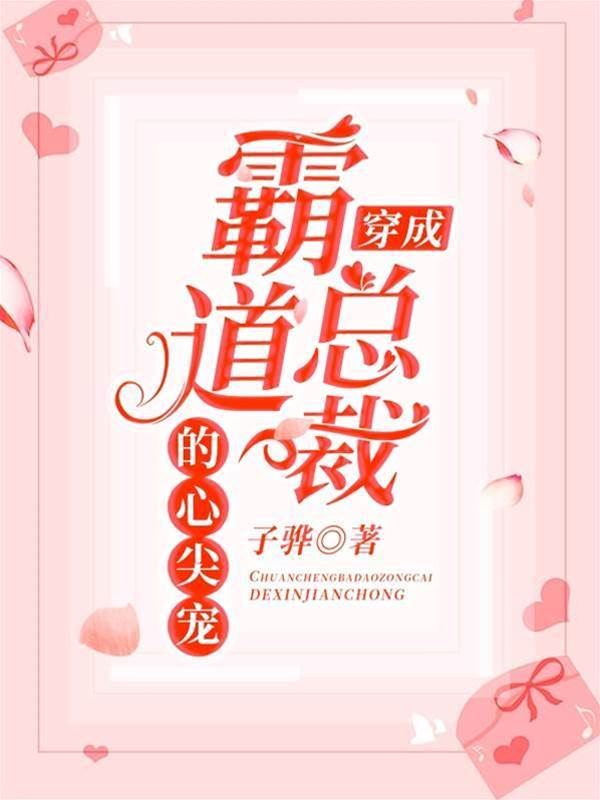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權寵天下:盛寵毒醫小嬌妃》 第94章 宴席驚變
阮桃一時并沒有發現什麼端倪,因為茹雪坐得端端正正,手上的作也是一不茍。
但阮桃偏偏就能從那曲調中聽出一按耐不住的狂躁來。
心底里莫名的預令阮桃有幾分焦慮,故而將更多的力灌注在了場中央的茹雪上,不再關注其他地方。
一曲終了,那茹雪站起來向在場的人行禮,卻不知為何悄悄地走近了匈奴使團中的耶律楚。
一直看著茹雪的阮桃自然發現了的小作。
只是還未來得及開口提醒的時候,茹雪便一個飛撲進了耶律楚的懷中。
看得出來,耶律楚對這個突然接近自己的子有極強的戒心。
在看到茹雪倒過去的瞬間,他便用手握了隨攜帶的長刀的刀柄之上。
只是接下來的場景卻讓在在座的眾人都大跌眼鏡。
只見那茹雪像是被去了骨頭似的,驀然倒在了耶律楚的懷中。
這一下令在場的諸位都猝不及防地呆住了。
不僅是作為事件中心的耶律楚,就連遠在座上的阮桃與玦都是一副驚訝的表。
期間,阮桃還特地向玦使了一個疑問的眼神,玦則向著輕輕搖了搖頭。
阮桃扶額,一時間不知該如何解決這突發狀況。
想也知道,據玦的格,必然是不會使這種低端的人計的。
那麼這令在場不論是自己人還是對方都大為驚訝的行為,便是茹雪私自決定的了。
只是如此做,又有什麼樣目的在其中呢?
溫香玉在懷的耶律楚,卻并沒有接這人的投懷送抱,而是像是極其嫌棄似的一把將茹雪扶正,甚至有些抗拒地推了開來。
“離我遠點兒。”耶律楚皺著眉頭看著茹雪,仿佛不是一位千百的大人兒,而是剛從臭水里飛出來的蒼蠅似的。
Advertisement
然而茹雪臉上可人的表卻沒有毫的變化,反倒是沒臉沒皮地了上去:“難道您不喜歡奴家這樣的嗎?”
耶律楚眼底的嫌棄仿佛就快要溢出來了一樣,毫不憐香惜玉地一把將茹雪推倒在地。
“敬的玦王殿下,若是要使人計,也得看是什麼人來。倘若是那不起眼的小飛蛾,就不要裝作是麗的蝴蝶了。”
這一番話說得毫不客氣,似乎一下便認定了是玦授意這茹雪前去勾引他的。
而玦卻沒有什麼表示,只是冷冷地瞥了地上的茹雪一眼,想必已經在心底想好了如何懲治這膽大妄為的子。
只是那被推倒在地上的茹雪卻依舊沒有反應,他甚至像是失去了痛一樣,依舊呆呆地坐在那兒。
耶律楚似乎察覺到了不對勁,一副強忍著惡心的模樣,湊近過去看了一眼茹雪的正臉。
接著,在場的諸位都發現了一十分詭異的地方。
那便是這茹雪方才進來時瞳孔是正常的黑。
而現在,瞳孔的正在慢慢帶上一抹紅,甚至有向純粹的發展的趨勢。
從阮桃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這茹雪眼睛的改變的同時,整個人也變得更為呆滯起來,像是一個沒有生命的傀儡。
這極為詭異的一幕,令本有著竊竊私語的談聲的大廳變得極為安靜起來。
阮桃著那雙赤的眼睛,不過瞬息便似乎想到了什麼,的瞳孔驀然放大。
幾乎在瞬息之間,阮桃便強地拉著玦起,退到了距離茹雪極遠的一個被柱子遮掩的角落。
“離遠一點!這是苗疆的!”
阮桃的語速極快,但幾乎在話音落下的那一瞬間,大廳中央的茹雪便轉過頭,用那雙赤的眼眸直勾勾的向了阮桃。
Advertisement
阮桃幾乎可以到那雙眼眸中滿是嗜的味道,但還未來得及有什麼深刻的驗,茹雪那姣好的臉龐,便驀地起了變化。
茹雪的宛如一個膨脹的球,迅速地鼓了起來。
本來那些匈奴使者們還一個個都對這話沒有太大的反應,但此刻見茹雪這幅詭異的模樣,皆是齊齊倒退了幾步。
而距離最近的耶律楚甚至已經三步并作兩步,往廳外跑去。
或許是冥冥之中的直覺指引,又或許是因為相信座上的阮桃。
耶律楚幾乎沒有毫猶豫地便開始遠離那看著便極為危險的茹雪。
事實證明他的預是正確的,因為在他才邁出幾步的時候,茹雪就毫不猶豫地朝他追了過去。
隨著茹雪的步伐,每朝前踏一步,的變異程度也回隨之多一分。
阮桃與玦雖然安全地待在柱子后面,卻仍舊十分焦急。
這耶律楚的死活雖然與他們無關,但耶律楚卻不能死在王府。
阮桃通過茹雪紅的眸子判斷,這茹雪上怕是被他人中了能控制神智的蠱毒。
而這眼眸的恰好與上一次追殺阮桃與玦的那個使用苗疆的刺客一致。
這便說明,無論是自愿或是被迫,茹雪都可能是要通過同歸于盡的方式拉著耶律楚一起死。
眼看著茹雪一副隨時都要炸裂開來的模樣,臉上已經凸起了青筋。
這般危急的時刻下,阮桃卻是漸漸冷靜下來。
合上雙眼,拼命回想著在那本古書上所記載的東西。
這種蠱毒似乎是一種可以控人心智的蠱毒,不過其控制力度卻并沒有達到完全違背宿主意愿的程度。
這蠱毒只會探詢被蠱所侵蝕的宿主的心愿,通過引的方式來達自己的目的。
Advertisement
也就是說,茹雪的心其實也是想讓耶律楚死在自己手上的。
其原因大抵是為了向玦表達忠心,亦或是與常年和國小打小鬧爭斗不休的匈奴有什麼夙怨。
而這所謂的苗疆,在那本古書上卻一點兒有用的容都沒有。
古書上只含糊地提到過有這等,卻并沒有說過破解之法。
阮桃再次睜開眼。看著茹雪逐漸脹大的軀變得越來越猙獰,心底忽然浮現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想法。
接著便由隨攜帶的荷包中掏出了自己的一整套銀針。
雖然由于穿著正統的朝服,阮桃將荷包藏在了極為的衫中,拿出來時有些困難,但由于況急,便顧不得那麼多了。
阮桃飛速地解下兩個扣子,將荷包拿出來,又飛速地系上,其中的過程大抵就只有玦注意到了。
接著阮桃一邊一手著銀針,一邊注視著距離已經有了不小的一段距離的茹雪。
據方才的猜測來看,這苗疆的,要做的是激發的“氣”,然后再將這些“氣”,通過一個從膨脹到釋放的過程,將它的能量盡數傾泄出來。
茹雪看來只是一件沒有力的普通人,故而這一凝聚“氣”的這個過程需要一段時間。
而上次那位前來追殺阮桃與玦的刺客卻是一位修為高深的家高手。
故而那位刺客從凝氣到釋放,就只用了一瞬間的功夫。
這也是他為何能猝不及防地讓阮桃與玦跌落懸崖的原因。
而阮桃現在要做的事,便是下一場賭注。
賭的便是刺中了茹雪上用于封泄勁的幾個道之后,能夠讓停止凝聚“氣”的這一個階段,從而阻止使用苗疆與耶律楚同歸于盡。
只是阮桃很快便發現現在與茹雪離得距離有些過于遠了,再加上如雪現在上膨脹得厲害。
若是不靠近茹雪就不能確地刺到茹雪上的位。
阮桃咬了咬牙,朝著茹雪的方向行進了些。
只是不消片刻,便被玦一把抓住了手臂。
“你要做什麼?”
阮桃回頭看了一眼他的眼睛,卻執著地試圖將他的手拉開來。
“妾必須阻止茹雪,如果今天和耶律楚一起死在這里,等待我們的將是無窮的后患。”
然而玦卻不依不饒,手上使得勁兒越發大了。
“他們是否死在這兒,本王今后的麻煩都不會。”
玦的聲音罕見地有了幾分微不可察的抖。
“而你,給本王活下去。”
阮桃看著他的手,一時間竟有些失神。
在如此重要的關頭分心,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事。
之前無論在多麼危急的時刻,阮桃都是一樣鎮靜自如。
很多時候,甚至連無量道人也說阮桃看似對邊的人都有有義,實際上最是無。
而這無,卻主要是提現阮桃對自己的態度上。
或許是因為從小的經歷,阮桃一向是一個對自己狠得下心來的人。
從跟著無量道人學醫開始,阮桃便直接用自己的手來試針。
那一出神化的醫便大多是從自己上實驗得來的。
在此期間,曾因為下針失誤而遭遇種種后癥,也曾因為試驗一種新藥而瀕臨死亡。
但阮桃終究足夠努力,也擁有常人所難以企及的天賦,故而“桃夭”所在江湖上取得的名聲,也都是靠自己攢回來的。
“對不起,這一次,我不能聽你的話。”
阮桃輕聲說著,出口的卻是拒絕的話語。
猜你喜歡
-
完結328 章

鬼王撩帳:人家好怕怕
意外身亡,魂穿異世,這都不算什麼。可是,偽善繼母,心機庶妹,剛一過來就遭遇毀容退婚,她招誰惹誰了?作為醫學世家的唯一傳人,竟然也會落入這步田地。說她囂張跋扈,那就跋扈給你看。你們都想做好人,那麼惡人就由她來當。繼母,死開!庶妹,滾邊!至於那傳說中喜好男風的鬼王……瑪德,到底是誰亂傳瞎話?這哪裡是喜好男風,興趣明顯是女好麼!某鬼王:“王妃錯了,本王的喜好無關男女,隻是喜好你……”
54萬字8 30742 -
完結81 章

天生撩人
梅幼舒生得嫵媚動人,在旁人眼中:心術不正+狐貍精+禍水+勾勾搭搭=不要碧蓮! 然而事實上,梅幼舒膽子極小,只想努力做個守禮清白的庶女,希望可以被嫡母分派一個好人家去過活一世。有一日君楚瑾(偷)看到她白嫩嫩的腳,最終認定了這位美豔動人的小姑娘果然如傳聞中那般品性不堪,並且冷臉上門將她納為了妾室。 梅幼舒驚恐狀(聲若蚊吟):「求求你……我不要你負責。」 君楚瑾內心os:欲迎還拒?果然是個高段位的小妖精。梅幼舒:QAQ 婚後每天都被夫君當做黑心x做作x惡毒白蓮花疼愛,梅幼舒表示:我TM是真的聖母白蓮花啊! 精短版本:小嬌花默默過著婚前被一群人欺負,婚後被一個人欺負日子,只是不知不覺那些曾經欺負過她的人,都漸漸地匍匐在她腳旁被迫要仰視著她,然而幾乎所有人都在心底等待著一句話的應驗—— 以色侍君王,色衰而愛弛! 瑟瑟發抖小兔嘰vs衣冠楚楚大惡狼 其他作品:無
25.8萬字8.25 26644 -
完結37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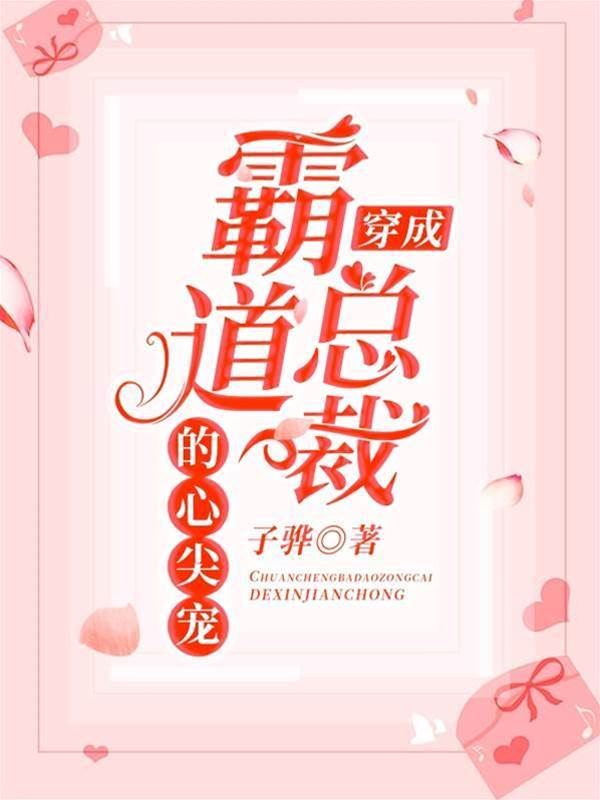
穿成霸道總裁的心尖寵
金尊玉貴的小公主一朝醒來發現自己穿越了? 身旁竟然躺著一個粗獷的野漢子?怎會被人捉奸在床? 丈夫英俊瀟灑,他怎會看得上這種胡子拉碴的臭男人? “老公,聽我解釋。” “離婚。” 程珍兒撲進男人的懷抱里,緊緊地環住他的腰,“老公,你這麼優秀,人家怎會看得上別人呢?” “老公,你的心跳得好快啊!” 男人一臉陰鷙,“離婚。” 此后,厲家那個懦弱成性、膽膽怯怯的少夫人不見了蹤影,變成了時而賣萌撒嬌時而任性善良的程珍兒。 冷若冰霜的霸道總裁好像變了一個人,不分場合的對她又摟又抱。 “老公,注意場合。” “不要!” 厲騰瀾送上深情一吻…
34.6萬字8 23781 -
完結112 章

太子妃嬌寵日常
姑母是皇後,父親是當朝權臣,哥哥是手握重兵的大將軍,一副妥妥的炮灰標配,他們還一心想把自己送上太子的床! 一朝穿成胸大無腦的內定太子妃,柳吟隻覺得壓力很大。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太子殿下極其厭惡柳家嫡女,避如蛇蠍,直到一次宮宴,眾人卻看到如神袛般的太子殿下給那柳家嫡女提裙擺!!! —— 月黑風高夜,男人攬著嬌小的人兒眸光一暗,“你給孤下藥?” 柳吟一臉羞紅:“我不是!我沒
31.9萬字8 32371 -
完結218 章

愛你甘願為妃
一碗落胎藥,她看著他平靜飲下,卻不曾想,他親手殺死了他們的孩子,依然不肯放過她,他說她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33萬字8.18 10132 -
完結191 章

新婚夜,瘋批太子奪我入宮
【強取豪奪+追妻火葬場+瘋狗男主】十六歲前,姜容音是嫡公主,受萬人敬仰,貴不可攀。十六歲后,姜容音是姜昀的掌中嬌雀,逃脫不了。世人稱贊太子殿下清風霽月,君子如珩
34.6萬字8 38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