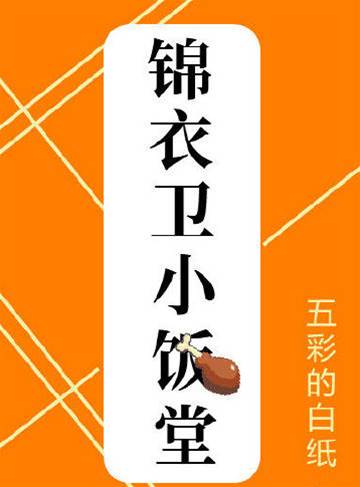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穿書后我推倒了暴躁男二》 第294回:真相還套著真相
“知道秦穆是怎麼當上西祁大汗的麼?”
這一刻的曹岫面目猙獰,早失去了高高在上的那份雍容和典雅。仿佛多年積累下的怨恨與冤屈,如堤壩上被豁開的口子一樣,洶涌迸出。
隋目不轉睛地睇向,一種前所未有的驚怖慢慢爬滿心田。
他本以為要和曹氏一族周旋許久,才能探得最終的真相。顯然是他推斷錯了,曹岫早就準備妥當,一直都在等,等待有個人跳出來扯下當年謎底的面紗。
“是拜你那好兄弟裴彬所賜啊。他在暗中贈予秦穆大量金銀珠寶,支持秦穆回到西祁爭奪王位。為的就是要讓秦穆打回北黎,好借他的手消滅我們曹氏的力量。”
“先帝絕不會那麼做!”隋嘶聲力竭地喝道。
曹岫一步步走到隋面前,仰頭看著這個高大威猛的男子,不值一哂地道:“哀家也以為裴彬很弱,他連一只貓都不敢殺死啊!哪能有那麼狠的心腸?可事實不容置疑,就是他一手把北黎推到阿毗地獄的深淵里。”
屋外倏然刮起勁風,在這酷夏時節里,增添幾分詭異之。堂屋案幾上的燈燭嗶嗶啵啵地作響,那暖黃的火苗在燈罩虛虛搖擺。
“起初按照裴彬計劃進展的都很順利,漠州淪陷,涼州、邕州岌岌可危。北黎朝中無將可調,西祁的攻勢太猛、太強悍。偏這時候你隋站了出來,披掛上陣誓要把西祁打回大漠里去。”
隋始終不得解的迷逐漸清晰起來,曹岫就是要這樣將他擊垮。以為雙可以重新站立行走就是重生了?非要讓他的信仰和堅持再次崩塌。摧毀一個人的方法有很多,這樣與隋對峙,遠比殺了他更有快。
Advertisement
然而曹岫不知道隋早就經歷了比這還要痛苦的打擊,在他還沒有站起來以前,他就被東野老國主凌澈強行告知,他里流淌的是東野人的。
不管曹岫對他說的這些是真是假,隋都不可能再像當初那樣歇斯底里地崩潰。但習慣了演戲的他,還是配合起曹岫,他目呆滯,間艱難地。
隋沒再像最初那樣急于反駁曹岫,他裝出手無足措的模樣,像是本不知該作何反應。
曹岫乘勝追擊,繼續強勁有力地說:“你是武中奇才,天生就是做將軍的料。雖然前期打得很吃力,中期又被兵力、軍糧等因素阻撓,但后期反擊時打得足夠大快人心,要知道漠州鐵騎的神話是靠西北百姓們自發頌揚開來的。”
“所以我打了先帝的計劃?”
“當然!裴彬和秦穆有盟約,裴彬把狼進來,再想送出去談何容易?你殺了多西祁士兵,秦穆損失多麼慘重?要不是裴彬下令要你別再繼續往大漠深里追攆,西祁都快被你打滅國了。”
曹岫不不慢地敘述著,又走回八仙桌旁,在事先準備好的小箱籠里取出一沓書信。這些正是秦穆和裴彬當年暗通款曲的信件往來。曹岫手里不僅著這些證據,而且在這條線上為裴彬差使的所有人的證據都收集得明明白白。
故意擺滿一桌面,一張一張地遞給隋,如凌遲般折磨著他的神經。曹岫所掌控的證據,恰恰就是許有德給他的卷宗里敘述模糊、疑竇重重的地方。
證詞、畫押、書信、銀票存……事無巨細一一俱全。看來當年曹岫調查這些下了不功夫。就在隋在陣前浴戰之際,他們這些人竟在背后作著這些勾當。
Advertisement
“西祁敗了,秦穆要裴彬給他一個代。裴彬不獻出你的命,秦穆就要揭他的老底兒。他害怕極了,北黎因為這場戰爭死去多條命?要是秦穆公之于眾,他就會被天下之人唾罵死,北黎皇室還拿什麼征服臣民?”
隋徹底明白過來,這才是裴彬把他拱手送出去的真正原因。他利用曹氏一族對隋的忌憚,讓世人都以為是曹太后派人索取隋的命,實則幕后黑手卻是裴彬。
“哀家承認,當年我是收買了你邊的副將,想讓他們在你的飯食和戰馬上做手腳。可你的那些將士們衷心,即便接到旨意也做不出背叛你的事,只象征地放了一點劑量,企圖蒙混過關。”
“我福大命大并沒有死,而當時的種種疑云讓你產生了懷疑?”隋順著曹岫的思路追問下去。
“真正讓你戰馬發狂的是笛聲。”曹岫又在那小箱籠里取出一支形狀古怪的短笛。
隋拿在手中掂了掂,很快判斷出這是西祁那邊的產。一點劑量的麻藥已讓他的不聽使喚,戰馬再被這種短笛所控制,不翻下懸崖才怪!
“馭笛的是西祁人,但你的回京路線確是被軍中之人出去的。不用猜了,不是你死去的那些副將,裴彬怎會找他們潛伏在你邊?那人預料到裴彬要殺他,才調頭來求哀家,跟哀家道出實。是我沒能保護好他……”
“先帝在朝堂上哪有這麼多勢力?有誰能幫助他完這些事?”
“問得好。”曹岫贊許地點點頭,“是老清王啊。你是老清王放在裴彬邊的一顆棋子,可惜你這顆棋子太不好用了,曾經的你不懂世故,不會圓,又太能打仗,他們都畏懼你!”
Advertisement
“你調查清楚這背后的一切,所以殺了裴彬。”隋放下手中麻麻的證據,問道。
“裴彬必須死!”曹岫大義凜然地呵道,“裴、彬、必、須、死!他得給北黎死去的將士和百姓們一個代!他那一條命本抵不過北黎千上萬無辜條命。哀家真恨不得親手殺了他,這樣心腸的畜生不配坐在龍椅寶座上!”
曹岫如此大方的承認,還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背叛國家和百姓的人沒有資格當皇帝。
這麼多年真的恨錯了人?曹氏一族從萬惡不赦的形象里搖一變,竟為忍辱負重、鞠躬盡瘁的楷模?
隋啼笑皆非,繞了這麼一大圈,得到的結果卻教人更加絕!
“哀家知道,自打你回到雒都就一直在追查當年之事,肅王府那幾個老東西在背后搞得那些勾當,以為哀家不清楚麼?”
“所以太后對現在的今上還是不滿意?”
“滿不滿意他也是當今的北黎皇帝,他重你不過是想利用你,他以為倚重宦就能大事?歷朝歷代就沒聽說有靠宦打下江山的。”
“可他是皇帝。”
“他能給你什麼呢?那區區三年的侯爵封賞?他什麼都給不了你,只能讓你去都督府里掛著閑職。今日哀家與你推心置腹,就看你能不能摒棄前嫌,與哀家站在一起了?”
“我一介武夫,不值得太后和今上如此重視。”
曹岫肆意大笑,說:“哀家讓你回漠州去,重振漠州鐵騎雄風,替哀家守好北黎的西大門。漠、涼、邕三州守備軍皆由你來統領,另……”頓了頓,“哀家封你為北黎王朝開國以來的第一個異姓王,你覺得如何?”
這個條件的確人,跟著曹家遠比跟著臭未干的劍璽帝要好的多。隋不聲地勾起角,沉聲道:“看來秦穆這幾年臥薪嘗膽養的不錯,宇文戟鎮不住他們了吧?”
“總得打好提前量,你也不希北黎重陷煉獄吧?”曹岫自信滿滿地道,“功名利祿哀家都能給你,這不好麼?”
“這回就不怕臣功高蓋主了?卸磨殺驢又不是一次兩次。”
“此一時彼一時,沒有絕對的朋友,也沒有絕對的敵人,只有絕對的利益。你與哀家共同坐擁這北黎江山,隋,莫在猶豫了。”
隋給了曹岫一個模棱兩可的答案,以今夜遭打擊太大為由,讓曹岫給他時間好好考慮一番。
曹岫放走隋,曹宗遠和曹宗道才從室里走出來。
“要不是西北太缺將領,何故要這麼低三下四地求他!宇文戟太不統,黃時越和傅青野在雒都待得早沒了爪牙,我也不能放顧白去西北啊,就他這麼一個有真本事的,得留下來保護咱們。”曹宗遠朝門外方向狠狠啐道。
曹宗道謹小慎微地收起好那些證據,道:“這些東西還是保留好比較保險,太后累壞了吧?臣這就差人備轎回宮。”
曹岫坐在玫瑰倚上單手支頤,疲憊地說:“多年未曾回家,已然冒了大不韙,干脆今夜在閨房留宿。”
時間早過三更,隋和郭林快速穿梭在無人的街巷里。就在馬上要回到侯府庭院中時,他們對面突然出現兩個黑人。能在這里堵住隋的也只有梅若風的人了。
黑人引著隋去往許有德宅邸方向,不遠傳來更夫的喊聲:“天干燥,小心火燭……”
他知道府中的染定在擔心自己,肯定在一遍遍地數著梆子聲。
“見過曹太后了?”
許有德在室里面見隋,梅若風則沒有跟進來,而是在屋外守候著。
隋坐到許有德對面,無奈地笑了笑:“許公公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些幕,但你沒有正面告訴我。”
“證據不在我手,由曹家人親自告訴你才更有說服力。恨麼?怨麼?想報仇麼?”
猜你喜歡
-
完結54 章
日日思君不見君
蕭逸塵是殺伐果決的當朝太子,司馬月是風華絕代的傾世太子妃,她輔他一步步登上至尊之位。他榮登大寶之日,她等來的卻不是封後的聖旨,而是滿門抄斬的厄運……
5.3萬字8 18603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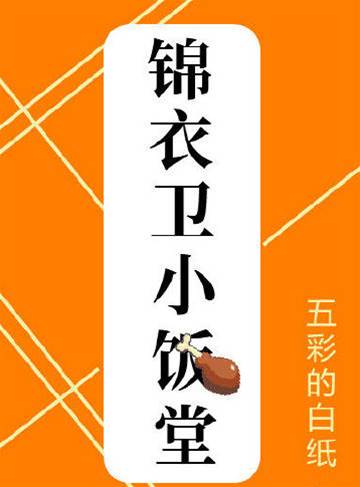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25 39928 -
完結420 章
廢柴要逆天:邪王追妻路漫漫
前世,她助他步步為營,終登九五之尊寶座,他卻因她家族功高蓋主,滅她一族全門,絲毫不念舊情;今生,她要親手從他手裏,將他欠自己的全部奪過來,讓他斷子絕孫! 只是,為什麼始終有個腹黑男人一直繞在她身邊?看她虐渣,他從旁指點,有人欺負她,他遞上刀子,讓她百倍還回去。 男強女強的碰撞,追逐與被追逐的好戲,誰會笑到最後?
112.4萬字8 10085 -
完結223 章

替姐姐嫁給病弱反派沖喜後
《真假千金》一書中,女配是被抱錯的假千金。 爲了報答養父母的恩情, 代替真千金嫁給受重傷將死的靖遠候陸霽沖喜。 穿成假千金的蘇桃心情複雜地看着榻上昏迷不醒的男人,想起書中他也沒多久可活,且她也無處可去,便安心照顧起陸霽,算是做件好事。 結果誰能想到,陸霽竟然醒過來了,還張口就喊她娘子! ———— 靖遠候陸霽心狠手辣,惡名昭昭,見他昏迷不醒,世人皆拍手稱快,就等着他嚥氣。 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昏迷後的他竟然附身在一塊玉佩上,雖口不能言,卻能看見周圍發生的事。 於是他看着那個沖喜嫁進來的小姑娘每天幫他擦洗身子,幫他上藥,給他喂水。 當衆人把他拉到院外,等着他嚥氣的時候,是她哭紅着眼睛把他帶回去,對着昏迷的他說:“走,跟我回家。” 醒後的陸霽逐漸強大,成爲大齊權傾天下的靖遠候,可他始終忘不了她穿着紅嫁衣進門時的模樣,還有那句“走,跟我回家”。 這句話,他記了一輩子。
31.7萬字5 18644 -
連載713 章

玄學丑妃:滿朝文武跪求我算卦
玄學大佬云清清,一朝穿越,竟成了被退婚的丑女小可憐。她反手就撕了跟渣男太子的婚書,嫁給了權傾朝野卻眼瞎腿殘的攝政王。全帝京都覺得攝政王妃又丑又廢,然而……皇后故意刁難,她直接一杯熱茶潑皇后臉上。“皇后娘娘還要罰我嗎?”皇后:“……潑得好,再潑一杯!”老國公怒斥云清清蠱惑攝政王,禍亂朝綱。云清清:“你祖墳炸了。”所有人都說這下攝政王也保不住她。哪知國公爺老淚縱橫:“我代表祖宗八輩感謝你!”全帝京都說她長得太丑,還騙婚攝政王。大婚當日,全場目瞪口呆。某王爺笑得妖孽:“本王只跟清清一生一世一雙人!”云清清:“…王爺,戲太足了。”
123.9萬字8 11457 -
完結81 章

侯府在逃小妾
宋吟一朝穿至大令朝,被原身父母賣給人牙子,幾經轉手,成爲高牆中的瘦馬。 碧玉年華之時,她出落得玲瓏有致、杏眼含情。 某夜,京中貴客駕臨,宋吟與衆女於席上獻藝。她瞥見下首坐着一位華服少年,眉目如畫,神情冷淡,實乃仙品也。 宋吟斗膽,主動迎了上去。 * 少年生性倨傲,吃軟不吃硬。 宋吟使出渾身解數,撒嬌獻媚,只盼他銷了自己的奴籍,而後早些歸京。 至於她,從此獨享宅院,快意人生。 豈料分別前夜,酒意作祟,少年堪稱繾綣道:“我乃永安府的小侯爺,你可願隨我一同上京。” 豁…… 宋吟額角滴下冷汗。 * 後來,盛怒的小侯爺抓到身着粗劣布衣、白淨小臉上畫一對粗眉的“已逝”愛妾。 黑眸中陰戾洶涌,冷冷道:“還跑嗎。” 宋吟仰頭,溼漉漉的杏眼迎上他的目光,如願在衛辭眼中見到一絲動容,遂壯着膽子道:“還跑……吧?”
24萬字8 40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