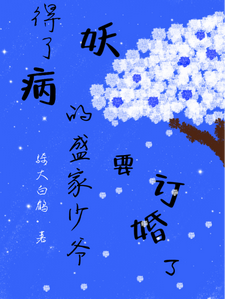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十一年夏至》 第7章 07
夏漓掛了電話,看向此刻已經抬起了頭的晏斯時,“……抱歉,沒注意到這里有人。是不是打擾到你了?”
晏斯時向投來的一眼分外疏淡,“沒有。”
夏漓頓時覺得惴然,是不是演技太拙劣,已被他看穿自己是個變態跟蹤狂。
沒法多想,著頭皮說:“哦……正好,你的外套。”
卸下書包,從中拿出那清洗晾曬,疊得整齊的運外套。
走近,遞過去,頓了一下——
年兩只手臂搭在膝蓋上,而手里著的,竟然是一包香煙。
“……謝謝你的服。”
晏斯時手接過,“不用。”
“還有這個……”夏漓從自己背包側面口袋里出耳機和打火機,解釋道,“服我洗過了,洗之前拿出來的……”
晏斯時手,從手掌里抓起耳機和打火機。
他手指竟比那枚銀的打火機還要涼,那瞬間到了的掌心,像是被什麼輕輕地啄了一下。
Advertisement
“謝謝。”晏斯時說。
夏漓頃刻間無法出聲,手垂落下去,悄悄住了手指,不知是想將那一下的抹去,還是長久留存。
晏斯時將耳機往校服外套口袋里隨意一塞,打火機拿在手里,從煙盒里出一支,低頭銜住。
“嚓”的一聲,打火機噴出小朵火苗。
他拿手掌攏了一下,那一霎的暖焰照在他冷白的臉上,垂眼瞬間,像裁開一段黑夜,薄長睫投下明顯的影。
夏漓父親的那些朋友都是人,見多了吞云吐霧的老煙槍。
因此一眼看出,晏斯時點煙和煙的作都還很生疏,明顯是個剛學會不久,且應該并沒有嘗試過多次的新手。
所以,他其實真真切切是個優等生。
連做起“壞事”來,用矯的話形容,都有種墮落的破碎。
晏斯時修長的手指夾著煙,抬眼,清淡地瞥一眼,“會告訴老師嗎。”
Advertisement
仿佛他只是隨口一問。
告訴不告訴的,他并不在意,這樣的好學生,又是學校的財神爺,老師知知道了又能拿他怎樣。
如同飲下徹夜涼風,嚨竟不自覺地一梗。
不會,會變共犯。
“這里平時經常有約會,老師也會時不時過來巡查。我知道有個地方……”出聲,好似又有些聽不見自己的聲音,“鐘樓的四樓,是個堆放桌椅的空教室,基本沒人去,適合需要安靜的時候,一個人待著。”
作為廣播臺臺長,經常出鐘樓。
那是偶然發現的基地。
如果他需要的話,樂意分。
晏斯時看向,臉上浮現淡淡的訝,片刻后說:“謝謝。”
夏漓沉默了一霎,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場在放電影,你不去看嗎?”
“不去了。”
“……那我先回場了。”
Advertisement
晏斯時點了一下頭。
夏漓不再打擾,轉離開。
將要拐彎時,回頭看了一眼,只能看見黑暗里一點如似漂浮的紅火星。
回到班里,林清曉也已經回來了。
“你去哪兒了?老莊剛剛來查崗,我說你上廁所去了。”林清曉湊過來低聲問。
“隨便去逛了一下。”
“我跟你講我剛剛嚇死了。”林清曉小聲吐槽,“教導主任剛才領著幾個紀律組的滿學校巡查,我差點被逮住……”
夏漓手臂撐著前方同學的座椅靠背,將額頭靠在了手臂上。
林清曉聲音一頓,關切地湊過來,“怎麼了?”
“……沒事。有點胃痛。可能是得。”輕聲說。
剛剛的事,仿佛榨干了所有的勇氣與力氣。
猜你喜歡
-
完結459 章

百無禁忌,她是第一百零一
十年前。溫知夏是安靜寡淡的乖乖女,顧平生是放蕩不羈帶著痞笑的校霸。 溫知夏一酒瓶爆頭了小巷內想要對她施暴的流氓,讓顧平生驚嘆、驚艷,原來小書呆也有脾氣。 青春年少,好像全世界都知道顧平生愛溫知夏,情深難抑。他為她喝過最烈的酒,淋過最大的雨,發過最熾烈的誓言,給過她最纏綿的吻。 顧平生用濃情蜜意偷走了少女最乾凈的一顆心。十年後。大雪紛飛的傍晚。 瘦弱的溫知夏看著車前跟另一個女人擁吻的顧平生,手中的化驗單無聲的飄落在地上,被雪花掩埋。 顧平生許是認定了、賴定了,事事順著他的溫知夏,這輩子都不會離開他。 他好像是忘記了,當初是誰求著哄著溫知夏愛他。她疼到了極致,為了保命,便是要將名為 “顧平生”的這塊腐肉剜去,即使傷痕累累,即使鮮血淋淋。後來——溫知夏在門口看到靠著墻吸煙的男人,他的身旁帶著一個紅著眼眶可憐巴巴的奶娃娃:“媽媽,團子好睏~~”溫知夏皺眉:“?!”青霧色的煙霧將男人的神情遮蓋,他耍起無賴:“看什麼?親子鑒定在這裡,你兒子,也是我兒子,負責吧。”
123萬字7.73 47352 -
完結54 章

心動指令
北城大學的百年校慶上,跟隨父母出席校慶的宋幼意一眼看到站在領獎臺上的白襯衣少年,襯衣洗得干凈發白,白凈精致的側臉微帶溫和笑意,細邊眼鏡泛著微光。旁人竊竊私語,談起這個金融系的天才少年賀憬,都夸一句努力,接連跳級考進名校,兼職賺生活費的同時,…
14.9萬字8 23535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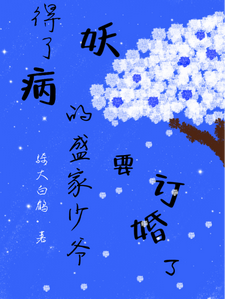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