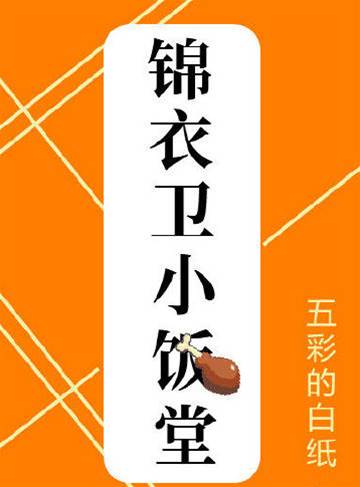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權臣一心要娶我》 第一百三十九章 比試
「南疆王,世人都知你南疆擅長奇門,你這怕是有點欺負人了。」這時候,有人言語說道。
在場的文不敢說話,威武將軍可不是善茬,他心中沒有那麼多顧慮,想到什麼就說。
老皇帝聽威武將軍這麼說,心中不由好!可面子上還是要裝模作樣的教訓一下。
「威武將軍。」
老皇帝故作不悅的開口,「南疆王是客,既然是客人,自然要照顧好客人的心意,我們北悠雖然不擅長奇門,但是陪南疆王娛樂一下,也不是不可。」
這話說得就很有技巧了,要知道客隨主便,偏偏南疆王自作主張,反客為主,這就是說他不要臉了。
再者,又說明了北悠不擅長這些,你們南疆就是欺負人。偏偏我們北悠有大國之風範,不介意陪你玩玩罷了。
這般,就是輸了,也不會丟了面子。
南疆王暗罵北悠皇是個老狐貍,但是他卻不以為意,畢竟這些不過是拋磚引玉,他的目的也不在此。
有了這麼一個臺階,這比試自然就應下了。
這一切,蘇惜都看在眼裏,更何況,蘇沐月那眼神,也太過明顯了。
這局若是輸了,怕是后招就等著了。
蘇惜前世雖然沒進過宮,但也一直都在為自己的命擔憂,除了努力活下去之外,並沒有什麼別的空閑的時間關心別的事。
可是,這畢竟涉及到家國大事,馬虎不得。更何況,約間覺察到,此事與有關。
回頭將青枝喚上前來,低聲吩咐幾句,後者取了的腰牌應下之後,便悄然離開了泰安殿。
蘇惜的心中也有些忐忑,雖然知道沐棋擅長奇門遁甲之,可究竟會到什麼程度,還未可知。
Advertisement
沒辦法,先死馬當活馬醫吧,
北悠皇帝與眾位員不同,他們可以在默不作聲地在心裏罵南疆王小人,可他卻不能,甚至還必須得將此事妥善理好,不能落了北悠國的面子。
心裏搜尋了一圈沒有找到合適的應戰人選,北悠皇帝有些急了,試探著開口問道:「北悠倒是不怎麼擅長這奇門遁甲之,畢竟邊疆有諸位驍勇善戰的將軍鎮守足以。若是比試的話,不知南疆王可有人選?」
他也算是同南疆王學了幾分,提前說了自己這邊沒有那種奇人異士。不過說就說吧,偏偏還帶了幾分傲氣,說是自己手底下的武將實力足夠,並不需要什麼花里胡哨的東西來作為輔佐。
若是聰明一些的人,聽出他這話里的幾分嘲諷,這時候應該說幾句場面話把氣氛扭轉過來。畢竟這還是在別人的地盤上,太過囂張了的確不好。
可偏偏那南疆王像是聽不懂北悠皇帝字裏行間的意思一樣,當然若是在乎臉面,也不會做出這般事來。
只見南疆王臉上的隨著他的笑容一抖一抖的,兒沒有收話的意思不說,甚至還真順著對方方才的話煞有介事地點了人。
「本王在永安侯府也住了兩天了,覺得墨世子學識不錯,聽說還是北悠今年的新科狀元。不如就由他來和我這侍從比試如何?」
堂堂一個侯府世子跑去和一個侍從比試,無疑是自降份,哪怕就算贏了也算不得什麼面的事。
這事不管別人怎麼說,蘇惜的眉頭便先皺起來了,果然,事還是繞到了的頭上。
看著蘇沐月得意的笑容,蘇惜就知道,這事跑不了的搬弄是非。
Advertisement
北悠員雖不至於人人八面玲瓏,但心思敏捷程度也遠超常人。這般簡單的問題,他們自然也已經看出來了。
還更別說,這墨玄瑾只是今年的文科狀元,有再大的本事落到這實戰裏面,也不過算是紙上談兵,更何況奇門遁甲之與學識毫無關係,到時候還落個北悠堂堂的狀元還不如他們南疆一個侍從的名聲。
一時間,眾人議論紛紛,甚至還有幾個老臣已經準備不顧臉面地起向皇帝進言了。
「陛下,墨世子能力不錯,但畢竟從未接過這些東西,請三思啊!」
此話一出,另外幾個膽大的老臣自然也跟著開了口。
顧及著還有外人在場,他們倒也沒把話說得有多難聽,最多也只是在圍繞著墨玄瑾為文科狀元,更是堂堂侯府世子,怎會接這些常人不的事等等。反正說來說去,都在明裏暗裏地指責南疆王故意挑人不懷好意。
但人家本來就是不懷好意的啊。
倒是沈方舟對墨玄瑾很是支持,「眾位大臣這話不對,墨世子的才學我等都看在眼裏,你們怎麼可以如此打擊呢。」
聽完這話,蘇惜眸一暗,沈方舟這時候還不忘了捧殺,果然心機。
南疆王趁機十分大方地開口了:「本王也不過是聽說墨世子是京中同齡人中最為出的,這才想著藉著這次比試見識一下北悠年輕一輩的學識能力罷了。諸位怎麼比我還對墨世子沒有信心呢?」
那幾個老臣聞言,臉都漲了豬肝,險些就要一口氣上不來。
得,換人也不行,眼下這是不得不應戰了。
北悠皇帝心中有些擔憂,把目放到了這個新進朝堂的年輕人上,試圖用眼神詢問他對此事有幾分把握。
Advertisement
哪怕是心裏其實本沒抱幾分贏的希,但有個底子放在心裏,總比明知要輸還把心懸在半空等著要好。
然而墨玄瑾卻並沒有第一時間回過去。準確地說,他知道北悠皇帝已經看過來了,也知道他的意思,但他並不想在這時候回答他。
因為方才他看到對面小姑娘的作了,若是他沒有猜錯的話,那個沐棋的姑娘今日似乎也跟著進了宮。在這時候讓青枝出去,莫不是有了主意,要去將人找來?
真是娶了一個好賢助啊。
墨玄瑾心中並不著急,繼續裝聾作啞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喝酒,簡直就像此刻眾人議論紛紛的對象不是他一樣。
北悠皇帝沒有得到回應,又不好一直拖著不回答,只能打算先把比試答應下來。
若是他知道墨玄瑾此時心中還在誇他老婆,怕是要被氣死。
南疆王看見北悠人磨唧唧的,便是開口說道,「左右不過是一場比試罷了,怎麼樣都可以,本王自然沒什麼意見。」
南疆王話說得客氣,但他先前那樣喧囂奪主的態度可不是這麼回事。
可是越是這般,北悠那邊就更是張。南疆王敢說這樣的大話,只能說明他勝券在握了,本都不在乎。
北悠國人更是氣極,若是比武,他們此時也是這個態度。
蘇沐月坐在他的旁,輕紗之下角高高揚起。對於現在的場景,特別滿意。
從沒想過有一天,這北悠朝堂竟然能被玩弄於鼓掌之中。
倒要看看,等蘇惜同一樣到了南疆王的床榻之上,還會不會再有那麼多人爭先恐後地為舍心掏肺!就是要侮辱,讓把自己過的屈辱,都要上一遍,甚至承百倍千倍的痛苦。
更何況如今才是南疆王的王妃,哪怕那是個頭大耳的老男人又如何,手裏有權,他又聽的,能藉著他的威風在南疆說得上話就行。到了那個時候,要蘇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只是這樣想著,蘇沐月彷彿就已經看到了不知夢到過多遍的場景,心中狂喜。若非這裏場合不對,只怕都要站起來仰天大笑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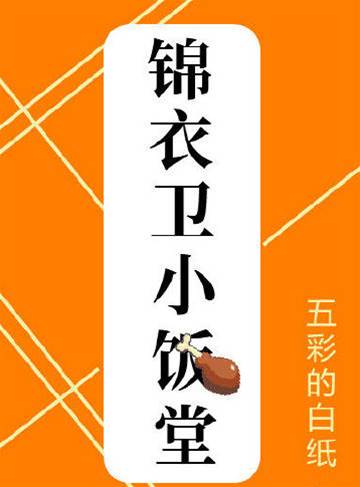
錦衣衛小飯堂(美食)
自從董舒甜到錦衣衛小飯堂后,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指揮使最近吃了什麼#錦衣衛1:“我看到夜嶼大人吃烤鴨了,皮脆肉嫩,油滋滋的,嚼起來嘎吱響!”錦衣衛2:“我看到夜嶼大人吃麻婆豆腐了,一勺澆在米飯上,嘖嘖,鮮嫩香滑,滋溜一下就吞了!”錦衣衛3:…
77.3萬字8.25 39928 -
完結151 章

嬌靨
一朝變故,帝臺有名的怯美人趙枝枝,從宰相家不受寵的庶女成了東宮里的小小姬妾——無名無份,只作“曉事”之用。傳聞新太子性情暴戾,喜怒無常,堪比修羅煉獄里的惡鬼。又說新太子厭惡美人,最恨絕色,以手刃傾城佳人為樂。趙枝枝聽后,嚇得半死,哭著同自己新結交的東宮“姐妹”托付遺言:“我…我若死了…能不能請你每年祭一碗櫻桃酥給我?”太子穿著彩衣娛親后的裙袍,黑沉沉的眼緊盯趙枝枝,半晌,他聲音沉啞道:“放心,你死不了。”*趙枝枝侍寢當夜,太子沒來,來了一百碗櫻桃酥。太子處理公務深夜歸宮,想起侍寢之事:“人睡下了嗎?”內侍:“回殿下的話,趙姑娘吃了一夜的櫻桃酥,這會子還在吃呢。”太子皺眉,罵了句:“真是個蠢貨。”半個時辰后,內侍前去寢殿查看,驚訝發現殿內多出一人。太子云鬢鳳釵,坐在小姑娘身側,替她揩拭嘴角:“吃不完也沒事,殿下不會怪罪你。”小姑娘低垂淚汪汪的眼,打著嗝細聲道:“你又不是殿下,你怎知他不會怪罪我?”*人人皆道趙枝枝膽小如鼠軟弱可欺,直至那日宮宴,東宮之主匍匐她身前,替她揉腳提靴,紅著眼咬牙切齒:“你若再不理孤,孤今日便離宮出走。”趙枝枝別開臉:“哼。”*文名嬌靨=女主趙枝枝眼中的男主,面美心黑暴躁太子爺。本文又名《心高氣傲狗男人每日在線卑微求愛》《孤這麼好她怎麼可以不喜歡孤》暴躁帝王VS哭包美人,小學雞談戀愛,1V1,口是心非真香吶。
53.6萬字8 33236 -
完結491 章

王妃又不讓王爺上榻了
重生前,她的世界只有沈風宸一人,為他忤逆父親,棄三千將士於不顧,毅然決然回京助他奪太子位,就在她滿心幸福等憐愛時,卻等來了一杯毒酒……重生后,她虐渣男,踢渣女,醫毒無雙,名動天下,每天都在轟動帝都的路上……「王爺召集我們是有什麼大事要商量嗎?」 「莫非又有戰事?」 某王爺坐在高位上,面容嚴肅,一本正經道:「諸位,本王今日有一事請教」 王爺竟然有事請教他們?「王爺請講」 「諸位平常在家是如何上自家夫人榻的」 後來,帝都上到八十老人,下到三歲孩童,都知道那個殺伐果斷的晉王總是上不了晉王妃的榻。
90.4萬字8 25310 -
完結546 章
攝政王你又被挖墻角了
【1v1+醫妃+養成+女強爽文】 他是權傾朝野的攝政王,她是葉家頭腦蠢笨的傻女,更是醫毒雙絕的鬼醫聖手。 渣爹奪盡她的家產,後娘欺她似狗,庶姐們欺淩辱駡,渣男悔婚利用,無妨,她一手醫毒術,打遍天下無敵手。 白蓮花陷害,一把毒藥變傻子。 後娘下毒,叫她毀容。 渣男踩著她上位,一根銀針叫他斷子絕孫。 人後撕天撕地撕空氣,人前可憐兮兮小白兔:“皇叔,我手手疼......” 男人眸光乍冷:“誰欺負了本王的愛妃? “ 被打得痛哭流涕的眾人:攝政王,您老人家可睜睜眼吧!!
50.8萬字8 41164 -
完結102 章

表妹慫且甜
徐靜書天生一個大寫的慫。 讀書時怕被人知自己寄居在信王府,每日披星戴月出入京郊書院;考卷從來隻答半張,怕學業出眾要遭人排擠,掐算著同窗的水準力爭中游; 出仕後御前彈劾百官有理有據,下朝時卻恨不能團成個球滾得瘋快;上官強調八百遍「沒人敢打御史臺的人」,她休沐時還是不敢獨自出門。 她最膽大包天的瞬間,大概就是十五歲那年,以猛兔撲虎之姿親上了眼盲的信王世子趙澈……還死不認帳。 徐靜書:不是我,我沒親,你瞎說! 趙澈:表妹休得狡辯,當初的口感,與此刻分明是一樣的。 史上最慫「官員風紀糾察員」X眼盲心明嗜甜王府世子,1V1,HE,慫甜味小甜餅。女主大事不慫,男主眼睛會好。 其他作品:《公子病》、《金玉為糖,拐個醋王》、《一枝紅杏紙上春》
36.1萬字8.18 11187 -
完結266 章

重生后嫁給廢太子
重生後,餘清窈選擇嫁給被圈禁的廢太子。 無人看好這樁婚事,就連她那曾經的心上人也來奚落她,篤定她一定會受不了禁苑的清苦,也不會被廢太子所喜愛。 她毫不在意,更不會改變主意。 上一世她爲心上人費盡心思拉攏家族、料理後院,到頭來卻換來背叛,降妻爲妾的恥辱還沒過去多久,她又因爲一場刺殺而慘死野地。 這輩子她不願意再勞心勞力,爲人做嫁衣。 廢太子雖復起無望,但是對她有求必應。餘清窈也十分知足。 起初,李策本想餘清窈過不了幾日就會嚷着要離開。大婚那日,他答應過她有求必應,就是包含了此事。 誰知她只要一碟白玉酥。 看着她明眸如水,巧笑嫣然的樣子,李策默默壓下了心底那些話,只輕輕道:“好。” 後來他成功復起,回到了東宮。 友人好奇:你從前消極度日,誰勸你也不肯爭取,如今又是爲何突然就轉了性子? 李策凝視園子裏身穿鬱金裙的少女,脣邊是無奈又寵溺的淺笑:“在禁苑,有些東西不容易弄到。” 知道李策寵妻,友人正會心一笑,卻又聽他語氣一變,森寒低語: “更何況……還有個人,孤不想看見他再出現了。” 友人心中一驚,他還是頭一回看見一向溫和的李策眼裏流露出冷意。 可見那人多次去禁苑‘打擾’太子妃一事,終歸觸到了太子的逆鱗!
41.8萬字8.18 436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