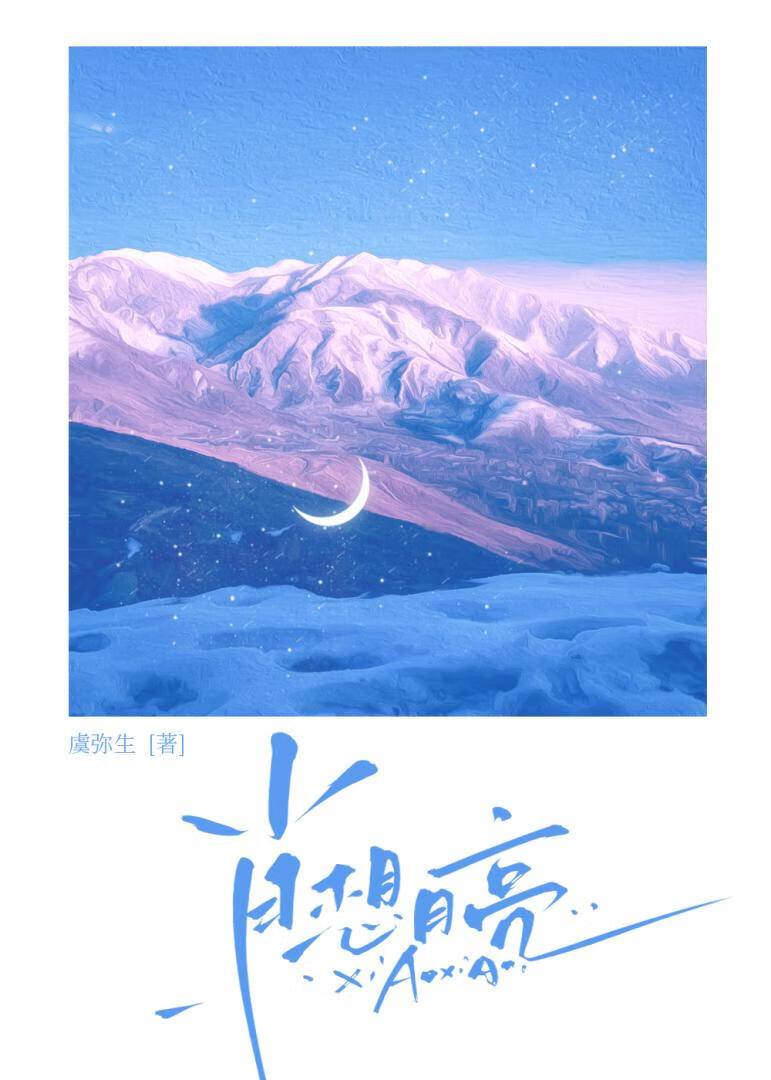《莫少逼婚,新妻難招架》 第341章 你不會太難受
「時笙,」季予南喊,聲音啞得很,一雙眸子很亮,很灼人。下顎上長出的淺淺鬍渣弄得很,他只是吻,一次比一次重,一次比一次深,似乎要將整個拆骨腹。
時笙被他的樣子嚇住了,雖然他的手規規矩矩的撐在的側,瓣也始終只在脖子上方,但約覺得這次和之前的不一樣。
「季予南,你先起來。」
這種覺讓心慌,開始不控制的掙扎。
就在這張床上,季予南和慕清歡滾到了一起,想想也覺得怪噁心人的。
季予南似乎被推得難,聲音更啞了,綳著的背脊似乎隨時都可能斷掉,「我沒有和慕清歡上過床。」
這事是下飛機時凱文跟他說的。
季予南第一次覺得這人怎麼這麼蠢,蠢得讓他恨不得狠狠的咬幾口,而他也真的這麼做了,啟,在時笙的上狠狠咬了一下,直到疼得眼裏冒出淚才鬆口,又用舌尖安的在被咬的破了皮的地方了。
時笙擰著眉別過頭,上還火辣辣的疼,「是,我看到慕清歡和一頭豬躺在床上。」
頭頂上方響起男人的笑聲。
他又低頭吻,這次比之前用力,「沒做,給我下了安眠藥,你他媽當我是什麼?昏迷不醒了還得起來?」
他又開始渾了,炙熱滾燙的吻極侵犯,他的手沿著人的腰線下,落在子的扣子上,卻不急著解開,似乎存了心要。
時笙綳著,努力下心裏那一的,人到了這個年紀多多會有生理反應,何況正在的這個男人還是喜歡的,但攔在他們前方的有太多未知,做不到心無旁騖的投。
所以,拒絕。
Advertisement
「你先起來。」人的嗓音因為繃而顯得戰慄。
「起不來,」季予南將臉埋在他的脖子裏,氣息紊的不樣,「就想著你,再一。」
時笙臉頰滾燙,也不知是被他氣的,還是惱的,「你……」
著的男人突然撐起了子,卻沒有完全離開,時笙聽見屜被拉開,繃的開始掙扎,帶著急促的音,「季予南,我不想。」
就算要做,也等見了傅亦,把事問清楚了呀。
下一秒,撐在他口的手被人握住,過頭頂。
男人看的目冷冷淡淡的,那灼熱被抑的很深,一點苗頭都見不著,「你是不想做,還是不想和我做?」
氣氛僵凝。
兩個人子又都是不服的,季予南菲薄的抿一條倔強的直線,時笙氣的口發疼,聚集著怒氣,「人要對對方有覺才會有慾,你以為全都跟你這種生長在腦子裏的人一個樣?環燕瘦都不挑。」
季予南著一張臉,神經簡直要綳得斷掉。
他這種?
生長在腦子裏?
「呵。」
男人一聲冷笑,又一次俯下子……
卻不是意料中的親吻,時笙只聽見『咔嚓』兩聲,手腕上一涼,雙手已經被他用東西銬住了。
掙了掙,才反應過來是手銬,不過還沒完,在時笙質問之前,季予南徹底翻從上下來,按住的雙膝,連胡踢蹬的雙腳一併銬住了。
輕鬆的不像是在錮一個全力掙扎的年人,更像是逗弄一隻小仔。
時笙躺在床上,手和腳都被束住,作僵像是一條待宰的魚,見季予南起整了整服要走,怒目瞪著他,「季予南,你幹什麼?給我解開。」
怎麼也沒想到剛才還蟲上腦恨不得將拆骨腹的男人瞬間變了態度。
Advertisement
居然拿手銬將拷了。
正常況下,他拉開屜拿的不應該是避孕套嗎?
媽的,腦子有病,做的事都別出心裁。
季予南就站在床邊,冷冷的瞧著,「拷著安心。」
時笙:「……」
臥槽你大爺的。
等想好要說什麼話時,季予南已經朝門口走了,那句到嚨口的冷嘲變了惱怒的斥責,「季予南你這個混蛋,你給我回來。」
回應的是一聲震耳聾的關門聲。
季予南面無表的下樓,口的襯衫還有些褶皺。
他上樓之前吩咐過不用準備晚餐,所以傭人都在打掃衛生,見他這麼快開門下來,有些忐忑的問:「季,有什麼吩咐嗎?」
們都剛來,多他的子不了解,只覺得過分沉。
「恩,」他應了一聲,薄間噙著極冷的笑,「做好後送上去給太太,親自喂吃下。」
他要趕回公司一趟,去中國這趟走的匆忙,公司的事也沒有接,雖不至於,但有幾件事必須要他去理。
他走到玄關,又吩咐道:「做中餐。」
傭人覺得這吩咐太過奇怪,但還是恭敬的應下了。
難道不該是看著吃下去?
一個好手好腳的年人,還需要人喂?
但等端著做好的菜小心翼翼的推開那扇門,就知道季予南為什麼這麼吩咐了。
「太太。」
躺在床上的了,手和腳都被束縛著,沒辦法有太大作,甚至坐起來都很費力。
克伊走過去扶了一把,手到幾乎只剩下皮包骨頭的手腕,忍不住輕了力道。
太太太瘦了。
都怕用力太猛將的手給折了。
時笙靠著床頭,「季予南呢?」
用手背蹭了蹭額頭那被頭髮弄得的地方,用手銬拷著還能輕微活,比用繩子綁著覺要好,這讓的臉稍微好些。
Advertisement
「季出去了,他臨走前吩咐給您做晚餐,要親自看著您吃。」
時笙還真了,即便是頭等艙,飛機餐也不見得有多好,再加上後面有些不舒服,被季予南著吃了兩口,後來就沒了。
「放著吧,我等一會兒吃。」
時笙這樣,吃飯肯定問題,總不能在個外人面前像個孩子一樣,將飯撒的到都是吧。
克伊已經拿了碗筷,夾了一筷菜遞到邊,「爺吩咐我親自喂您吃。」
時笙看著那鮮翠的菜葉以及嫻的握筷子姿勢:「你會做中國菜?」
「招聘第一條就寫著要會中國菜,我本來以為是季吃,但這些天他從來沒吩咐過,也就今天太太回來了,他才讓我做中國菜。」
時笙心裏掠過幾分別樣的緒,季予南很吃中國菜,而且也吃不習慣,時笙只要自己在家做,一般都做中國菜。
也沒矯,就著克伊的手吃了飯。
「謝謝,味道很好。」
克伊鬆了口氣,笑道:「太太您先休息吧,我就在門口候著,有什麼吩咐直接我就行了。」
時笙睡不著,讓克伊將的手機拿過來,撥了季予南的電話。
……
彼時,季予南正在公司開會,整個會議室的氣氛劍拔弩張,靜得一針掉在地上都能聽見。
這幾天季予南不在公司,旗下地方分廠主管虧空公款,剋扣工人工資,弄得集罷工,被吵得沸沸揚揚,導致這幾天季氏票跌落,董事會借題發揮,有幾個早就見不慣他的人在中間挑事,非要讓他為此時給個代。
季予南本就心不好,臉更是沉的不行,冰冷灼灼的視線掃過下面心思各異的人……
這群人,無非想自己獨攬大權,偏偏又被他著,不甘心而已。
他嘲諷的勾了下角,啟,還未說話,正巧手機響了……
季予南低頭看了一眼,屏幕上顯示——時笙。
「看不慣就滾。」
五個字擲地有聲,一旁的傅隨安咽了咽唾沫,還好,下留了,沒讓這群人直接去死。
他拿著電話起,推開會議室的門走了出去,留下一群人面面相覷。
這會還開不開?
季總拿著電話,一句吩咐都沒有就出去了,到底什麼意思?
「什麼事?」
男人心不好,眼睛裏是森森的寒意,他低頭點了支煙,靠著牆,一副神倦怠不願說話的樣子。
會議室里的竊竊私語聲清晰的傳他的耳中,更是惹人煩躁。
這般爾虞我詐,他早已經習慣了,只是最近越發的覺得煩了,疲於應付。
一支煙很快了一半。
時笙問:「你打算什麼時候放了我?」
總不能拷著一輩子吧。
季予南角噙著笑,眼睛微微瞇起,慵懶的道:「等你乖的時候。」
時笙氣得咬牙,手銬越掙扎越,手腕上有一磨得通紅泛著殷紅的,「怎樣才算乖?」
「你覺得呢?」季予南彎,那燥意因為幾句輕描淡寫的話就散了一半,再聽裏面的爭論也不覺得煩了。
會議室的門沒關,傅隨安見季予南許久沒進來,抬頭去看——
淡漠的男人穿著一剪裁合的西裝,眉眼英俊,抿起的瓣彎起並不明顯的弧度,像是在笑。
這段時間季予南的脾氣一直晴不定,弄的整個公司的人都惶惶不安,生怕了地雷。
所以,乍然見到他這般溫耐心打電話的模樣,傅隨安還是看得有幾分出了神。
察覺到的目,季予南看過來,轉瞬間,又是一副優雅疏離的淡漠樣。
他很快轉開視線往會議室里走,對電話那頭的時笙道:「還有兩個小時,等我回去,無聊可以看會兒電影或是睡覺。」
。
猜你喜歡
-
完結897 章

上司是隱婚老公
寧熙嫁了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兩年後她進公司實習,總裁是她的隱婚老公。人前,他們假裝不熟。人後,兩人極致纏綿。白月光回國,他提出離婚,她藏好孕肚簽下離婚協議瀟灑的離開,他發瘋似的全世界找。五年後,她牽著帥氣兒子回國。男人將她抵在角落,紅著眼眶乞求道:“老婆,求求你看看我。”
85.2萬字8.46 450366 -
完結226 章

假千金逆襲,千億老公高攀不起
我以爲我只要乖順聽話,就能守住這場婚姻,直到那女孩出現。 他眼底愛意流淌,看她時像看易碎品,完全無視我的難堪和酸澀。 青梅竹馬不敵天降意中人。 我讓出江太太的位置,遠走他鄉。 可久別重逢,他卻紅了眼眶,握住我肩膀:孩子是我的嗎? 我笑笑甩開他的手:你認錯人了。 以爲是場死火,未料仍有餘燼。
40.3萬字8.18 24215 -
完結2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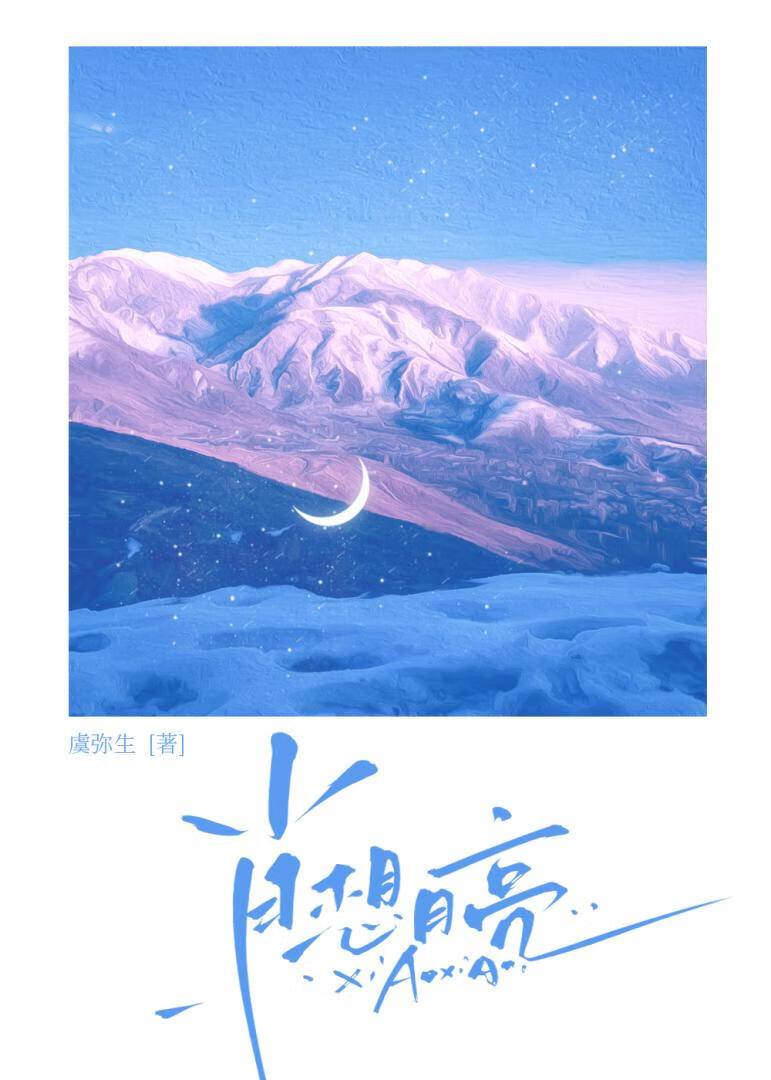
肖想月亮
林應緹第一次見江席月是在養父母的倉庫裏。 少年清俊矜貴,穿着白襯衫,雙手被反捆在身後,額前黑髮微微濡溼。 他看向自己。嗓音清冷,“你是這家的小孩?” 林應緹點頭,“我不能放你走。” 聞言,少年只是笑。 當時年紀尚小的她還看不懂江席月看向自己的的淡漠眼神叫做憐憫。 但是那時的林應緹,沒來由的,討厭那樣的眼神。 —— 被親生父母找回的第九年,林應緹跟隨父母從縣城搬到了大城市,轉學到了國際高中。 也是在這裏,她見到了江席月。 男生臉上含笑,溫柔清俊,穿着白襯衫,代表學生會在主席臺下發言。 林應緹在下面望着他,發現他和小時候一樣,是遙望不可及的存在。 所以林應緹按部就班的上課學習努力考大學。她看着他被學校裏最漂亮的女生追求,看着他被國外名牌大學提前錄取,看着他他無數次和自己擦肩而過。 自始至終林應緹都很清醒,甘願當個沉默的旁觀者。 如果這份喜歡會讓她變得狼狽,那她寧願一輩子埋藏於心。 —— 很多年後的高中同學婚禮上,林應緹和好友坐在臺下,看着江席月作爲伴郎,和當初的校花伴娘站在一起。 好友感慨:“他們還挺般配。” 林應緹看了一會,也贊同點頭:“確實般配。” 婚宴結束,林應緹和江席月在婚禮後臺相遇。 林應緹冷靜輕聲道:“你不要在臺上一直看着我,會被發現的。” 江席月身上帶着淡淡酒氣,眼神卻是清明無比,只見他懶洋洋地將下巴搭在林應緹肩上。 “抱歉老婆,下次注意。”
33萬字8 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