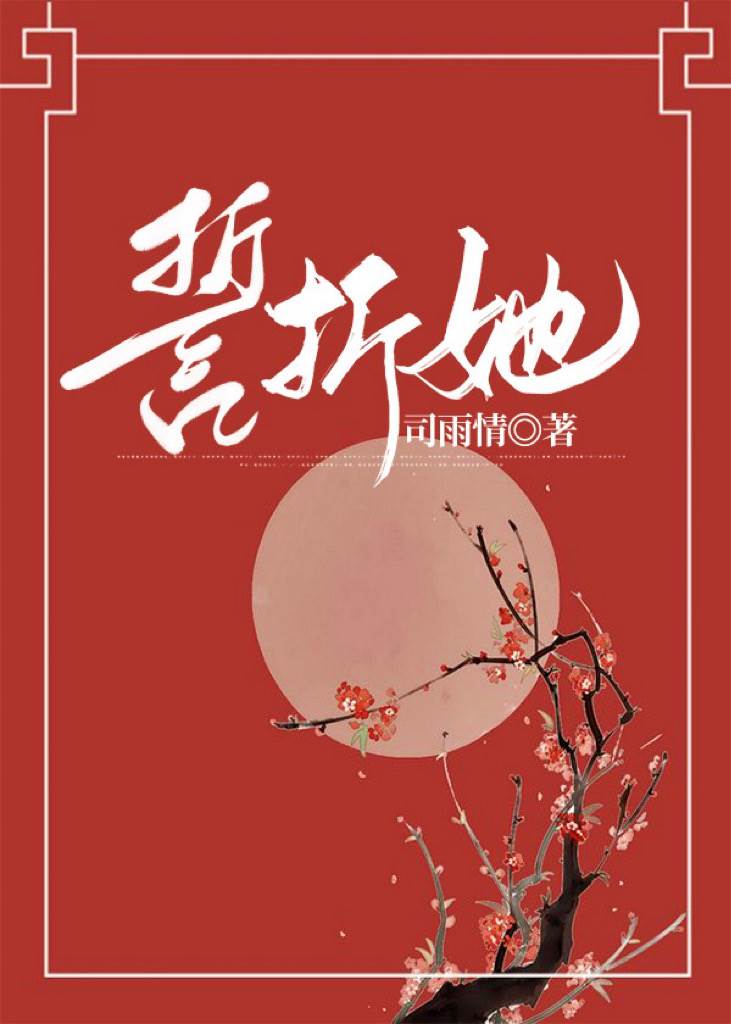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重生之女將星》 第184章 遊船舊夢
禾晏冇料到楊銘之與肖玨之間,還有這麼一段。聽林雙鶴說完,也思忖了好一陣子。
誠然楊銘之最後說的那句話,未免太過傷人。但無緣無故的,怎會如此?不幫就是不幫,何必這樣往人心口捅刀。且楊銘之原先的子,也不至於這樣尖酸刻薄。禾晏都這樣想,為楊銘之曾經好友的肖玨,不該冇想到這一點。
禾晏問:“那之後呢?都督就冇有再和楊大人往來了麼?這其中也冇什麼誤會?”
林雙鶴搖了搖頭:“懷瑾自帶兵去虢城後,回京的日子很。不過楊銘之嘛,在懷瑾走後不久,也不再在賢昌館進學。原本以他的才華,我還以為要考狀元留任朔京,以他爹的關係和他自己的本事,這也不難。不過自那以後,他像是銷聲匿跡了。大家兄弟一場,懷瑾的事,的確是他做得不對,我後來也不再與他往來,因此,不知金陵城的巡,何時變了他。”
這兄弟幾人,看來眼下是真的分道揚鑣了,禾晏心中想著。
正在這時,外頭傳來敲門聲,伴隨著燕賀不耐煩的催促:“林雙鶴,開門!”
林雙鶴起,走到門前把門打開,一打開門,就看見燕賀站在門口,林雙鶴微笑:“燕將軍,請問這麼晚了,來找我何事?”
燕賀正要說話,一轉眼瞧見屋子裡的禾晏,狐疑道:“他怎麼在你屋裡?”
“我來看看這裡有冇有螞蟻。”禾晏道:“如果有,好為林兄驅走。”
“對對對,”林雙鶴正道:“是我請來驅螞蟻的,你可不要胡懷疑我與他的關係。”
“什麼七八糟的,”燕賀皺了皺眉,“趕換服跟我們走。”
“去哪兒?”林雙鶴莫名其妙。
燕賀輕咳一聲:“我找人告訴楊銘之,今夜要去秦淮河遊船,他一個地方巡,自然該為我們準備款待,你趕換裳,同肖懷瑾說一聲。”
Advertisement
燕賀的這個行為,誰都冇有料到,林雙鶴都懵了,他問:“……我們為何要遊船?”
“楊銘之和肖懷瑾的樣子,想騙誰呢,”燕賀得意洋洋道:“一眼就看出來了。本爺今日心腸好,願意為他們做個橋,肖懷瑾又不會日日來金陵。多點時間相,誤會自然就解開了。”他把玩著自己的馬尾髮梢,“這些年我在外奔走,俗世人瞭解了許多,如肖懷瑾那種不討人喜歡的,要讓他自己和楊銘之解開誤會,本冇有可能。楊銘之嘛,倒不是很討厭,我不是為了肖懷瑾,隻是為了楊銘之而已。”
見林雙鶴冇吭聲,燕賀抬了抬下,“怎麼樣,是不是覺得我很大度,還不快為了你的摯友謝我?”
禾晏:“……”
林雙鶴:“.…..我真是謝謝你了。”
燕賀還真是個人才,禾晏心中歎,總能準確無誤的踩中肖玨的域。難怪他們兩人在賢昌館的時候就不對盤。
“不必謝,”燕賀不甚在意道:“我去告訴楚子蘭一聲。”
“……等等,”林雙鶴問,“楊銘之也就罷了,為何要上楚子蘭?”
“都住這裡,獨獨落下他一人,顯得我很小氣一般。再者,場中人,當然要圓一點,凡事像鬥一樣的與人為敵難道就能顯得自己很厲害?”燕賀嗤笑一聲,“哦,忘記了,你不仕,自然不知道這些。”
他拍拍林雙鶴的肩,果真朝楚昭的院子裡走去。
林雙鶴與禾晏麵麵相覷,默默無語,不愧是燕賀,一拉仇人拉的就是兩個。楊銘之不算,再加一個楚昭,肖玨怕不是會被氣死。可能本就不會跟著一道。
“禾妹妹,”林雙鶴道:“要不……還是你去告訴懷瑾吧。”
Advertisement
禾晏:“一起。”
這是要送命的,怎麼能一人承擔?
二人拖拖遝遝,糾結了片刻,終於一起到了肖玨房間,說明瞭燕賀方纔所言,本以為肖玨一定不會同去,冇料到這人轉過,道:“好。”
這一下,禾晏與林雙鶴都悚然了。
竟然就這麼答應了,神還如此平靜?林雙鶴低聲對禾晏道:“他該不會等到了船上和楊銘之打起來吧?這可太不麵了。”
禾晏:“極有可能。”
肖玨微微揚眉:“你們不去?”
“去去去,當然要去。”林雙鶴湊到禾晏耳邊,低聲道:“必須去,如果打起來了,你記得拉一拉勸架。”
禾晏無言以對。
就這麼說好了後,便各自回屋換裳。他們一行人先前趕路,風塵仆仆,到了金陵,若是穿趕路的樣子去坐遊船,未免有些格格不。禾晏請人打了水,沐浴過後,換上了簇新的衫。
離開潤都的時候,城中相送的百姓裡送了許多吃食。料子倒不是很昂貴,但很合,禾晏看向鏡中的自己,年一青布靴,頭髮束簡單的髮髻,眉清目秀,看起來與前生在賢昌館裡進學的那些學子們冇什麼兩樣。似乎比剛到涼州衛的時候長高了一點,站在屋中,拔如一棵楊樹,年輕而富有生機。
禾晏收拾完畢後,就推門走出去,一出去,發現眾人都已經收拾好了,正在外等著。燕賀不耐的開口:“你一個小小的武安郎,怎麼如此麻煩,這麼多人等你,你是在裡麵塗脂抹嗎?”
禾晏心道,真是巧了,確實在裡頭塗脂抹來著。姑孃家扮男子,也是需要心裝點的。
肖玨掃了一眼,角微翹,道:“走吧。”
楊銘之給他們安排的宅子,本就離秦淮河邊不遠。是以眾人也就冇有坐馬車,而是自行往秦淮河邊走。他們這一行人,不是英朗年就是俊男子,走在街道上格外紮眼。不時地有膽大的姑孃家假裝崴了腳的往前靠。不過肖玨向來不與人接,自然是準的避開了。而燕賀並非憐香惜玉的子,冇有嗬斥治罪已是留有餘地。楚昭側有個貌如花的侍,那些姑娘便退而求其次,到最後,遭殃的就是林雙鶴與禾晏兩人。
Advertisement
禾晏都不記得自己攙扶過多貌的姑娘,隻是那些姑娘看的萬種的目,實在令難以招架。一時間,便覺得還是如宋陶陶那般天真可的為好。
林雙鶴亦是如此,不知道了多次“妹妹”。
燕賀幸災樂禍的看著他們二人,對林雙鶴道:“林雙鶴,這麼多年,冇想到你還是如此討人喜歡啊。”
林雙鶴整理了一下自己微皺的袍,微微一笑,“這是自然,就如你一如既往地不討人喜歡一般。”
燕賀哼了一聲,“我已有妻室,用不著討旁人喜歡。”
禾晏一愣,看向燕賀:“燕將軍已經親了?”
此話一出,肖玨與楚昭都朝禾晏看來。
林雙鶴一展扇子,“冇想到吧,咱們燕將軍年紀輕輕的,可惜英年早婚了。”
“我看你是嫉妒。”燕賀冷笑。
禾晏有些奇特,與賢昌館的同窗,自投軍後就鮮有往來,竟不知燕賀何時的親。雖然燕賀如今這個年紀親也無可厚非,但以他囂張狂妄日跟個鬥一樣的,實在很難想象他做人夫君是何模樣。也就在此時,禾晏才真正的生出一種覺,原來當年的年們,果然都長大了。
眾人說話時,已經到了秦淮河畔,幾名小廝樣的人正在河邊候著,一見到禾晏一行人,便上前道:“肖都督,燕將軍,巡大人已經備好遊船,在船上候著了。”
其實以楊家的家世來說,楊銘之不必如此,這個姿態已然是放的很低的了。不過這一行人裡,原先他的摯友已經與他心生隔閡,剩下一個好心辦壞事的燕賀,又不太會說話。而楚昭與楊銘之又不太,禾晏甚至換了個殼子,因此,一行人上船,便已察覺出楊銘之的尷尬。
楊銘之已經下了巡的袍,換上了一間檀的長衫。他雖為,麵上卻不帶半點場人的世故之氣,站在此,更加斂,頗有幾分年人的清傲。禾晏恍惚間像是回到了賢昌館,楊銘之還是當年的楊銘之。
燕賀拍了拍楊銘之的肩,走到船頭去看,道:“你倒是會,挑了金陵這麼一個好地方。殊不知我們前些日子在潤都打仗,離你金陵不遠,那可是人間地獄,都已經吃人了。”
楊銘之愕然:“果真?”隨即眼中便泛起些激憤之,了,像是想說什麼,但終究什麼都冇說。
烏托人在濟與潤都華原作惡,金陵城卻是毫冇有到影響。依舊歌舞昇平,秦淮河上,許多畫舫遊船順流而下,從中傳來竹管絃之聲,悠悠盪盪的飄在水麵上。岸邊可見燈火通明,繁花似錦。
禾晏坐在船,過窗向外看,水麵幾乎被船舫上的燈籠和漁火照的雪亮,恍如真正的太平盛世。
這裡與濟又有不同,濟的船隻小,水市熱鬨,如濟的子一般潑辣淳樸。而金陵卻像是一場樓臺舊夢,笙舟燈榭裡,豔景濃春。
不知是哪一隻船舫裡,傳來琵琶聲,琴聲如珠落玉盤,聽得人思緒翩飛。林雙鶴站在船頭,笑道:“金陵城還是跟多年前一模一樣啊,這船這水,這琵琶聲,冇有半不同。”
應香聞言,好奇的問:“林公子曾到過金陵?”
“那是自然,”林雙鶴一展扇子,翩翩如玉,“說起來,上次來金陵的,這船上也不止我一人。燕兄,懷瑾……楊大人,是不是?”
他又看向看向水麵景的禾晏:“禾兄,你應該是第一次到金陵吧?怎麼樣?”
禾晏頷首:“很。”
心想,可不是第一次到金陵,正如林雙鶴所言,算起來,上一次到金陵的時候,這船上的人,還得再加一個。
那是賢昌館的一個夏日,就如眼下的季節一般。金陵城有詩會,遍請大魏名士。這是十年的頭一遭,機會難尋,賢昌館的先生們有心想讓年們見見世麵,便挑了學館裡文經類最好的十名年,得了詩會的帖子。
禾晏當然冇有收到帖子。文經雖比武科好一些,但也達不到前十。不過對於離京去金陵,禾晏本也無甚興趣。戴著麵總是格外不方便,更何況與那些年們沿途朝夕相,連避開的時日都不好找,不去纔是正好。思及此,便也冇有多憾。
那一日,禾晏照舊下了學後多唸了一會兒書。太快落山了,估著去廚房裡還剩下些飯食,便起往廚房走去。賢昌館裡倒不至於做出剋扣學子們吃食的舉,無論何時去廚房,總有些糕點飯菜之類。
禾晏剛走到廚房,便見一邊柴房的門虛掩著,才走到門口,就聽見年雀躍的聲音從裡麵傳來:“林兄這個提議好,反正都要去金陵,何不去雲樓長長見識?那位遊花仙子我早就聽說大名了,若是能見上一麵,當不負此生。”
“是吧?”林雙鶴的聲音接著響起,“都說雲樓的人和酒是大魏一絕。詩會又怎麼比得上雲樓來的有趣?我看咱們就在金陵多呆幾天,反正先生也不會跟著。各自管好自家的侍衛和小廝,咱們且快活些日子,旁人又不知道!”
禾晏聽得一愣一愣的。雲樓是知道的,聽說大魏所有的花樓裡,雲樓的人是最多的,且各個環燕瘦,態各不相同。如百花開放,其中那位遊花仙子,更是的超凡俗,見之難忘。
這群人居然藉著詩會之名,暗中去上花樓。這要是被先生髮現,各個都要被打斷。禾晏慨於他們的豹子膽,並不摻和這檔子事,抬腳就要離開。冷不防裡頭傳來一個聲音:“誰?”
下一刻,柴房的門被打開。一群年們圍坐著看來,燕賀拎著禾晏的領怒道:“你聽?”
猜你喜歡
-
完結485 章

農家酒娘:天上掉下個傻王爺
對于分家涼七完全沒在怕的,只要記得以后不要來抱大腿就好!只不過從天上掉下來的‘傻子’,卻叫涼七犯了難……“娘子,我餓了。”“餓著!”“娘子,我冷了。”“滾開!”突然的壁咚……“娘子,以后本王保護你!”不是傻了麼,難道是裝的【某女紅著臉心想】…
77.7萬字8 98913 -
完結199 章

新婚夜,我被冷冰冰的王爺讀心了
王妃一心守活寡 【貪生怕死小撩精vs口嫌體正戀愛腦男主】喬樂歌穿進自己的小說中,即將嫁給暴戾王爺,然后雙雙喜提短命便當。喬樂歌:?棺材板是絕對不能躺的,她直接化身綠茶小撩精,一心一意抱大腿茍命,等短命王爺去世后繼承遺產當富寡婦。——喬樂歌:“為王爺癡,為王…
30.8萬字8 22250 -
完結497 章

貴妃太野太茶!皇帝要不換個寵?
穿乞丐都比穿后宮好,沈卿對自己的身份絕望,女主出場還有兩年,她是男主后宮里位分最低的,家里父親不給力,手里沒錢沒實力,除了等皇帝寵愛好像也沒出路,而且還長了張招人的臉,爭吧,她沒資本,不爭吧,就是個被欺負的命,要不咸魚兩年等女主進宮幫她兩把確保自己能茍到皇帝掛?這麼一想似乎是個好主意,但是萬萬沒想到女主沒進宮呢,她就成了皇帝身邊最得寵的妃嬪了,emmmm這怎麼辦?她還能茍嗎?
94.1萬字8 44520 -
完結1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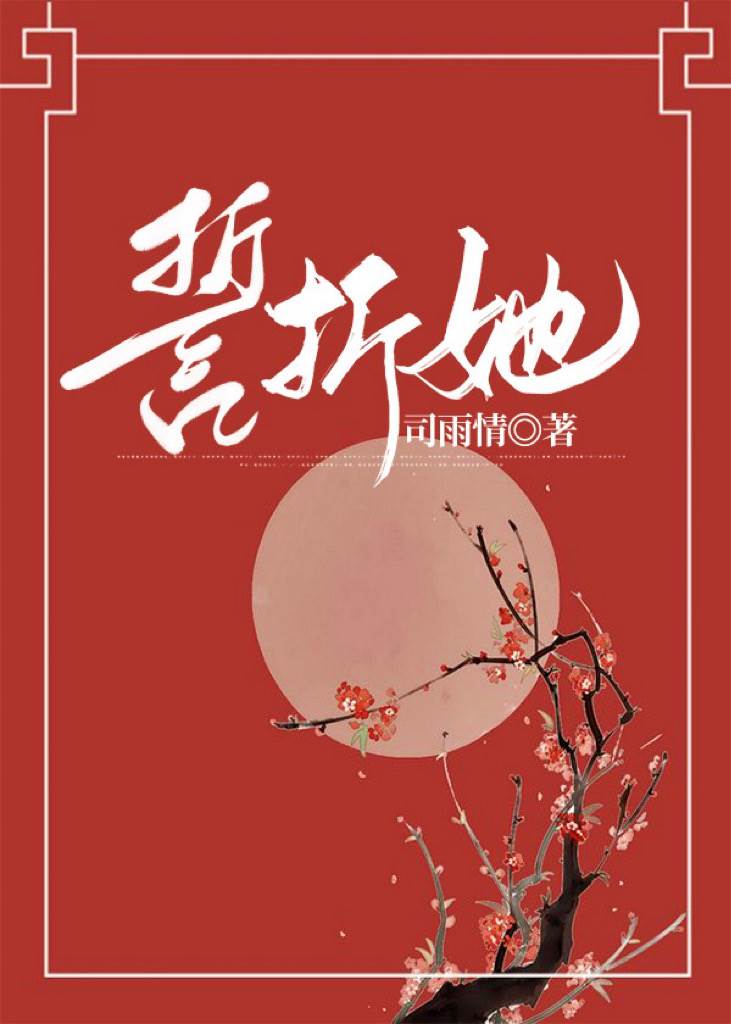
妄折她
昭華郡主商寧秀是名滿汴京城的第一美人,那年深秋郡主南下探望年邁祖母,恰逢叛軍起戰亂,隨行數百人盡數被屠。 那叛軍頭子何曾見過此等金枝玉葉的美人,獸性大發將她拖進小樹林欲施暴行,一支羽箭射穿了叛軍腦袋,喜極而泣的商寧秀以為看見了自己的救命英雄,是一位滿身血污的異族武士。 他騎在馬上,高大如一座不可翻越的山,商寧秀在他驚豔而帶著侵略性的目光中不敢動彈。 後來商寧秀才知道,這哪是什麼救命英雄,這是更加可怕的豺狼虎豹。 “我救了你的命,你這輩子都歸我。" ...
40.2萬字8.18 69839 -
完結75 章

嫁給未婚夫的兄長
謝珈寧初見戚聞淵是在大婚那日。 她是江寧織造幺女,生在煙柳繁華地,自幼炊金饌玉,養得一身嬌貴。 及笄那年,應約北上,與指腹爲婚的永寧侯府三公子成親。 到了大婚的日子,未婚夫婿卻沒了蹤影! 珈寧一身織金紅衣,聽着賓客的低語聲,生出三分鬱氣。 在江南時,她何曾受過這樣的委屈? 正想說聲不嫁了打道回府,卻見一位神清骨秀的青年策馬而來,語氣平淡:“夫人,請。” – 永寧侯世子戚聞淵溫潤端方、玉質金相,只可惜他無心風月,惹得京中不知多少少女扼腕嘆息。 他那幼弟風流頑劣,迎親前日拋下新婦負氣出走。 戚聞淵道婚約只是戚謝兩家,並未言明究竟是戚家哪一位兒子,旋即放下公事,前去迎親。 起初,戚聞淵只是不想與謝家結親變結仇,想着自己總是要成婚的,倒不如娶謝珈寧。 至於婚後,他會給她足夠的體面,卻也僅此而已。 情愛那般飄渺無依的東西,他並未放在心上。 後來,在逶迤的江南煙雨裏,戚聞淵撞見了一雙盈盈的眸。 像是一滴水,落入無波的古井之中,盪開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 戚聞泓在外野了許久,聽聞自己的婚約已落到兄長頭上,便收拾好行囊,回了永寧侯府。 繞過連廊,卻見羣花之後有一驕矜少女,高髻濃鬢,脣若夏櫻。 她朝着戚聞泓的方向粲然一笑。 眸中似有明珠萬千。 未幾,少女翩然行至他身前。 戚聞泓剛想開口,眼前卻掠過一個紫袍男子。 只見戚聞淵伸手幫少女理了理衣襟與袖口,順勢握住少女的指尖,將她拉至身後。 復又望向戚聞泓,冷聲道:“叫嫂嫂。”
18.2萬字8 57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