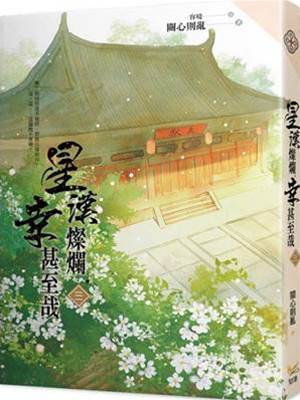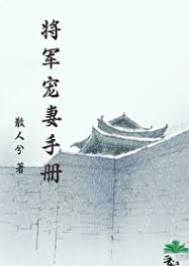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將門嬌嬌一睜眼,偏執王爺來搶親》 第81章 要怪就怪你家殿下
次日一早,謝昭昭辰時不到就起了,用完早膳,又去苗先生那小院。
藥把苗先生的藥箱拿出來。
里面有好幾套針。
謝昭昭不確定拿哪個,索把藥箱直接帶著,免得去到妙善堂苗先生再說拿的不對又得耽擱時間。
出門的時候,天都灰蒙蒙的。
守在角門那里的老伯打著哈欠,只覺一陣香風飄過,猛然一個激靈。
等反應過來的時候,就看到一抹倩影帶著兩個婢停在門邊,等候底下人備車。
“七小姐?”老伯詫異:“這麼早您干什麼去?”
“有事。”謝昭昭朝老伯微笑,“要出去一趟。”
“哦,哦。”老伯點了點頭,暗自嘀咕,這七小姐幾個月來都是除非必要,否則就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今日這麼早出門還有事?
也不知道是干什麼去。
紅霞將馬車趕來,謝昭昭直接上車,便吩咐往妙善堂那邊去。
妙善堂是鬧市之中一醫堂,就在雙魚巷巷尾,謝昭昭昨晚就讓紅袖去打聽清楚了。
馬車搖搖晃晃。
謝昭昭在車坐的端正,手指輕輕點著苗老頭的藥箱,琢磨著他跑去是找了什麼藥材?
而且回來了也不回府,竟然約在外面給解毒。
Advertisement
也不知道葫蘆里賣的什麼藥。
隨著馬車搖晃,車窗簾子忽高忽低。
謝昭昭看著街道上出來討生活的百姓,眉心輕輕蹙著,心底稍微有些浮躁不安。
這老頭,最好是這次別耍花樣,否則被這般吊著的時間太久,真的不知道發作起來會做出什麼事。
一刻鐘過些,馬車停下,外面傳來紅袖的聲音:“小姐,妙善堂到了。”
“嗯。”
謝昭昭應了一聲,提著苗先生的藥箱下了馬車。
因為時辰還早,妙善堂雖然開了門,里面卻沒有病人來看病,只有個兩個伙計在整理藥柜,一個掌柜在柜臺后面撥拉算盤。
邊上有賣早點的攤子,倒是坐了兩三個腳夫。
謝昭昭進到妙善堂。
那掌柜抬頭瞧了一眼,趕從柜臺走出迎上來,“七小姐來了,快里面請。”
謝昭昭蹙了蹙眉。
確定自己是沒見過這個人的,但這人卻一眼認出,難道是苗老頭代的?
掌柜的在前面走,一邊說道:“苗先生在后面院子呢,這會兒估著已經起了,小的帶您過去。”
謝昭昭抿了抿,只得帶著紅袖跟上去。
主仆二人穿過后堂,進了后院。
但掌柜的沒在后院停留,而是過去將門打開,還回頭恭敬地對謝昭昭說:“苗先生在那邊院子,還請小姐隨我來。”
Advertisement
謝昭昭狐疑地跟過去。
出了后院門便是一條窄巷。
對面白墻青瓦,不知是哪戶富貴人家的宅院,恰巧正對著妙善堂的后院角門也開著一扇小門。
謝昭昭站在窄巷,沒,“這是去哪?”
“苗先生在這院。”掌柜地回,“小姐別怕,小人不是壞人。”
“壞人從不把‘我是壞人’幾個字寫在臉上。”謝昭昭淡淡道:“你去苗先生出來見我。”
“這……”
掌柜的見謝昭昭不信,便說:“那您稍等,小的去請。”
話落,掌柜的提著袍擺進了那小門,往去了。
開門關門的間隙,謝昭昭看到那院子回廊九曲,紅花綠葉,景致很是不錯。
苗老頭按說沒道理有這樣的宅子。
這麼裝神弄鬼的,難道是云祁?
謝昭昭仔細打量了下面前的窄巷,又琢磨了一下雙魚巷和云祁那座定西王府所在的街面。
還沒琢磨徹,那院子里便傳出苗先生罵罵咧咧的聲音:“真是個臭丫頭,你來你過來就行了,你哪兒那麼多事兒?”
謝昭昭抬眸看去。
只見苗先生穿著一襲青灰裳,發髻有些凌,臉也很是難看。
一副剛被人從被窩里挖出來的樣子。
“跟老夫走!”苗先生一揮手,轉往里,“快點兒的。”
Advertisement
謝昭昭問:“這是哪兒?”
“總之不會把你賣掉!”苗先生沒好氣地說:“進來進來。”
謝昭昭默默片刻,大致猜到了什麼,便提著藥箱跟了進去。
一路轉到一雅致安靜的院落。
苗先生指了指西廂的屋子,“去把藥箱放下吧,坐著等我老頭子一會兒。”
“好。”
謝昭昭到西廂去。
那里有兩個藥柜,屋藥香濃重,靠窗的桌子上還有些瓶瓶罐罐,和切碎沒整理的藥材。
謝昭昭把藥箱放好,挽起袖子將那些藥渣分類。
剛分完,苗先生便進來了,“呦,還手做了點兒事呢,勤快!”
“順手而已。”謝昭昭問,“現在可以解筋散了嗎?”
“當然。”
苗先生把桌上的一個青花瓷藥罐打開,取出一粒黃褐藥丸,“你吃了,然后躺到那椅上去。”
“上次不是直接針灸,沒說要吃藥。”
謝昭昭有些狐疑,“怎麼過了幾天這解法都不一樣了?”
“你以為老夫想要這麼麻煩?”
苗先生一邊翻著藥箱找針囊,一邊沒好氣道:“還不是要怪你家殿下……”
“他知道解筋散針灸,位會有刺痛,可能不好,便著老夫做點兒準備。”
“這不,老夫便沒日沒夜做了這丹藥,服下這丹藥,一點都不會損傷經脈不會刺痛,還能養氣。”
“吃吧,吃下去睡一覺,等你醒了,你的功外功便恢復了。”
謝昭昭:“……”
沒想到這中間還有這番波折。
在苗先生的催促下,謝昭昭將那黃褐的藥丸吃下,躺到椅上去。
沒過一會兒,果然頭暈目眩,困意襲來,漸漸地就沉睡過去,什麼也不知道了。
苗先生著針走過去,執起謝昭昭的手扎針,一邊嘀咕,“這年輕人就是會玩,下藥的人是他,如今解筋散瞻前顧后還是他。”
“那麼怕人疼,下藥的時候早干嘛去了?”
“就知道折騰我老頭子。”
要不是為了那下落不明的兒,苗先生哪里會云祁驅使。
分明一個混賬東西。
這幾句話,苗先生在心里罵完,認真地給謝昭昭扎針去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0 章

糖寵
裴瓊很擅長甜言蜜語,哄得家里的祖母、爹娘和哥哥們都最疼她。 太子殿下最冷清的一個人,也被她花言巧語哄地五迷三道的,違抗父命也要娶她。 可傳聞里千嬌萬寵的太子妃,平日里連顆糖都要數著吃。裴瓊看著自己小盒子里寥寥無幾的幾塊糖,可憐巴巴地算這個月還剩幾天,她要怎麼吃才能撐到月底。 夜色幽深,鴛鴦交頸。汗光珠點點,發亂綠松松。 裴瓊眼睫上掛著淚珠兒,轉過身去不理人。 太子冷著一張臉哄:糖糖乖,不哭了,明日讓給做荔枝糖水吃好不好? 【食用指南】 1.互寵 2.真的甜,不甜不要錢 3.架空文,一切都是為了撒糖,請勿考據
24萬字8.18 8266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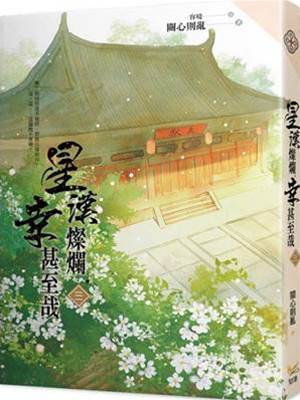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406 章

深宮劫:美婢難寵
沉默的承受著帝主給予的所有恩寵,她已無力去挽留清白,任由他在芙蓉帳下的狂妄。他是主,她是婢。從來只有他想的,沒有她能拒絕的。皇帝大婚,她卻要成為皇后新婢。
76.2萬字8 6169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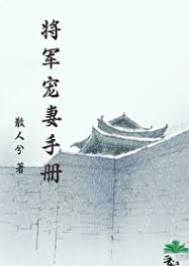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