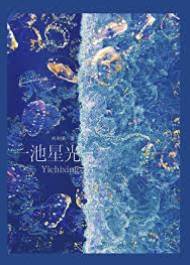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乖寵》 第85章 他錯了
唐民德握住門把手,打算開門進去。
往下按。
門卻沒開。
從裏頭反鎖了。
“湘湘?”
“湘湘!”
唐民德一麵喊,一麵扭門把手。屋沒人回應,門也打不開。
他慌了。
他怕沈湘做什麽傻事!
“先生……”
“你馬上去拿備用鑰匙把門打開!”唐民德將手裏的餐盤給了後的傭人,吩咐了一句之後就下了樓。
前往樓梯間搭乘室電梯上二樓。
電梯抵達主臥客廳。
唐民德立馬跑了出來,他環視一圈,跟著跑去臥室,就看見人躺在床上。
他箭步衝上前,彎下腰正準備放緩嗓音跟說話的時候,卻發覺人耳畔並不是他悉的。男人眸了下去,一把將被子掀開——
傭人嚇得要命。
連滾帶爬地從床上下來,跌坐在旁邊的地毯上,不敢抬頭:“……先生,是夫人要我這麽做的。”
“湘湘去哪裏了!”
“夫人……”傭人脖子,聲音都在抖,“夫人上午要我和一起出門,說是去商場買點日用品。讓我穿著的服回來,我、我也不知道夫人去哪裏了……”
唐民德麵鐵青。
垂在側的兩隻手,手臂的青筋凸顯。
在餘瞥見床頭櫃的東西那刻,男人所有的戾氣忽然被幹,整個人都遲鈍了。
他盯著那看了許久。
邁開沉重的步子走到那,低頭看向上麵擺著的三件品。
一個藍的小盒子、一枚老舊的士銀戒指、一封泛黃了的信。
Advertisement
他先拿起盒子。
打開。
裏麵躺著一隻西裝袖扣,是送給他結婚二十年紀念日的禮。可惜那天晚上他接到人的電話,說樂樂病重進醫院,沒來得及和一起吃飯。
也失信沒陪去麓山看日出。
再見已是三天後,他氣衝衝地回到別墅,拽著去醫院輸。雖然沒真的要的,但他也當著的麵,說了句‘樂樂的命更重要’的氣話。
說完他就後悔了。
唐民德又拿起那枚老舊的銀戒指,這是二十年前他們領證的時候,他送的。
那時窮。
還沒有錢。
買不起昂貴的鑽戒,隻能買一對普通銀子對戒。
但是不嫌棄,戴在手上還非常開心,說就喜歡銀戒指。
後來兩人富有了,躋為榕城上流圈子的人,他給買了很多珠寶戒指,但還是二十年如一日戴著這枚。
這戒指表麵有斷層。
應該是斷了。
但又找人去銜接,雖然工藝很好,但斷掉的戒指也無法恢複到最原始的樣子,還是有斷掉的痕跡。
唐民德最後拾起那封泛黃的信紙。
這張紙他更悉。
意氣風發的年,懷揣著最純粹的,寫了一封書,虔誠地遞給自己心的孩。
紙張的字跡已經模糊,但還能依稀看清最後一行字:“沈湘同學,做我朋友吧!”
這行字底下還有一個娟秀的字,沈湘的字:“好。”
此刻。
這個‘好’字被劃掉了。
墨水是新的,唐民德手,指腹按上去,蹭掉了一些藍墨。
Advertisement
別墅裏所有的東西都沒有帶走。
就帶走了那箱設計稿,以及‘DX品牌離唐氏企業’的合同書。立唐氏企業後畫的服裝稿都沒要,是覺得:
因為有了這家上市公司,所以他變了。
“湘湘——”
唐民德跪了下去,手裏還地攥著那枚戒指、那張信紙。
他錯了。
不該覺得兩人在一起多年日子平淡,所以就放縱自己跟外邊的人廝混。以為不會發現,以為會信任他,以為會永遠在自己邊。
為了讓自己更加心安理得。
他隻挑那些與湘湘長得相似的人,好像這樣良心就能過得去一點,不會那麽愧疚。
他不該背信承諾。
明明說過不在乎子嗣,終生不孕,那他們就無後而終。可是,當那個人拿著彩超單給他,看見彩超裏已經型的孩子,他搖了。
如果說,以前他玩人,還能有被原諒的餘地。
這個孩子的降生,就是他和沈湘之間無法越的鴻,無聲宣告他們三十幾年的關係破裂碎。
-
那晚之後,唐民德瘋狂在榕城找沈湘。
用了能的一切。
可就是找不到人。
海陸空三通樞紐都沒有離開榕城的痕跡,可就是找不到。就像人間蒸發了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直到第五天的上午。
他收到一封匿名的簡訊,對方話語簡潔:“三一大道568號咖啡館,我告訴你沈湘在哪。”
男人幾乎是收到信息的同一時刻就起離開。
Advertisement
外套都沒穿。
汽車飛馳在街道上,不要命地往咖啡館趕。二十分鍾的路程,不出十分鍾就趕到了。
唐民德推開咖啡館的門,左右環視,就看見坐在偏僻角落的喻唯一。
兩人對視。
人眼神澄澈,朝他無害地搖了一下手,示意這邊。
在來的路上,準確來說是在找沈湘的這五天裏,他就猜到是喻唯一。正因為猜到,唐民德才會如此擔心。
擔心對沈湘下手。
喻唯一藏得好。
這種人才是最毒的蛇,忍蟄伏的時間過長,積怨太深,心理早就已經扭曲了。會為了報仇不計一切代價,也會眼睛不眨地殺人。
跟年齡無關。
二十歲也能是一把冷的利刃。
唐民德快步走上前,到跟前,手撐在麵前的桌子上,“你把湘湘弄哪去了!”
喻唯一把牛兌進咖啡裏,用勺子攪拌。
瞥了眼視線裏男人青筋暴起的手,然後收回視線,語調輕快:“一個暗的地方,不給飯,好可憐。”
“喻唯一!”
“唐總,坐。”
喻唯一抬頭,近距離看他,才看見男人眼下厚重的眼圈。
神憔悴得不行。
這五天他連公司稅稅的事都不管了,隻一心發瘋地找沈湘。
唐民德不想坐,卻不得不坐。
他怕傷害沈湘。
男人拉開椅子,在對麵坐下,“喻小姐,湘湘是無辜的,請你不要害。”
喻唯一將調好的咖啡推到他麵前,“我的做法取決於你的態度。”
唐民德知道說的是什麽。
“當年車禍的事是我去辦的,剎車失靈導致車輛在倫敦大橋撞上橋墩。站得越高被人盯得越,要怪隻能怪你父母識人不清!”
喻唯一無聲冷笑。
兇手都是一個德行,總是害者有罪論,將自己滔天的罪惡歸咎在害人上。
拿出一個牛皮紙袋扔到唐民德麵前。
裏頭的照片了出來,畫麵中有他兒子樂樂。男人皺眉,手拿了起來。
一張一張往後看。
越看,唐民德臉越難看,神態越痛苦。
樂樂病重不是湘湘下的手!
他錯怪湘湘了!
看著他愈發痛苦的臉,喻唯一學他:“隻能怪你識人不清。”
猜你喜歡
-
完結500 章

陌路婚途
結婚四年,老公卻從來不碰她。 她酒後,卻是一個不小心上了個了不得的人物。 隻是這個男人,居然說要幫她征服她的老公? excuse me? 先生你冷靜一點,我是有夫之婦! “沒事,先睡了再說。”
89.4萬字8 73159 -
完結2312 章

有孕出逃:千億總裁追妻成狂
夏時是個不被豪門接受的弱聽聾女,出生便被母親拋棄。結婚三年,她的丈夫從來沒有承認過她這個陸太太。他的朋友叫她“小聾子”,人人都可以嘲笑、侮辱;他的母親說:“你一個殘障的女人,就該好好待在家裏。”直到那一天他的白月光回國,當著她的麵宣誓主權:“南沉有說過愛你嗎?以前他經常對我說,可我總嫌棄他幼稚。我這次回來,就是為了追回他。”夏時默默地聽著,回想著自己這三年和陸南沉在一起的日子,才驚覺發現,她錯了!結婚三年,夏時愛了陸南沉十二年,結果卻深情錯付。種種一切,讓夏時不堪重負。“陸先生,這些年,耽誤你了。”“我們離婚吧。”可他卻把她關在家裏。“你想走,除非我死!”
207.6萬字8.33 330489 -
完結380 章

插翅難逃之督軍請自重
她,是為姐姐替罪的女犯。他,是殺伐果決、令人生畏的督軍。相遇的那一刻起,兩人命運便交織在了一起。顧崇錦從來沒想過,一個女人竟然成為了他最大的弱點。而偏偏那個女人,卻一心隻想逃離他。宋沐笙也沒有料到,一心隻想保護姐姐的她,早已成為了男人的獵物。他近乎瘋狂,讓她痛苦不堪。為了留住她,他不顧一切,甚至故意讓她懷上了他的孩子,可誰知她居然帶著孩子一起失蹤......她以為她是恨他的,可見到他一身軍裝被血染紅時,她的心幾乎要痛到無法跳動。那一刻她意識到,她已經陷阱這個男人精心為她編織的網裏,再也出不來......
64.9萬字8.18 8586 -
完結8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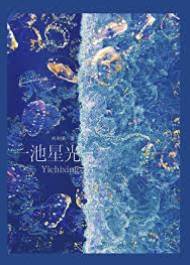
一池星光
夏星曉給閨蜜發微信,刪刪減減躊躇好久,終於眼一閉按下發送鍵。 食人星星【不小心和前任睡了,需要負責嗎?】 閨蜜秒回【時硯池???那我是不是要叫你總裁夫人了?看了那個熱搜,我就知道你們兩個有貓膩】 原因無它,著名財經主播夏星曉一臉疏淡地準備結束採訪時,被MUSE總裁點了名。 時硯池儀態翩然地攔住攝像小哥關機的動作,扶了扶金絲鏡框道,“哦?夏記者問我情感狀況?” 夏星曉:…… 時硯池坦蕩轉向直播鏡頭,嘴角微翹:“已經有女朋友了,和女朋友感情穩定。” MUSE總裁時硯池回國第一天,就霸佔了財經和娛樂兩榜的頭條。 【網友1】嗚嗚嗚時總有女朋友了,我失戀了。 【網友2】我猜這倆人肯定有貓膩,我還從沒見過夏主播這種表情。 【網友3】知情人匿名爆料,倆人高中就在一起過。 不扒不知道,越扒越精彩。 海城高中的那年往事,斷斷續續被拼湊出一段無疾而終的初戀。 夏星曉懶得理會紛擾八卦,把手機擲回包裏,冷眼看面前矜貴高傲的男人:“有女朋友的人,還要來這裏報道嗎” 時硯池眸底深沉,從身後緊緊地箍住了她,埋在她的肩膀輕聲呢喃。 “女朋友睡了我,還不給我名分,我只能再賣賣力氣。” 夏星曉一時臉熱,彷彿時間輪轉回幾年前。 玉蘭花下,時硯池一雙桃花眼似笑非笑,滿臉怨懟。 “我條件這麼好,還沒有女朋友,像話嗎?”
29.5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