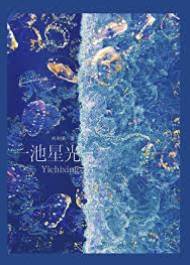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和霸道總裁離婚後發現自己懷孕了》 第9章 把他當成擺設?
那晚之後,靳寒淵就沒再出現過。
陸安然從一開始的擔驚怕,後來見靳寒淵再沒有其他擾的舉,也逐漸安心下來。
時間飛逝。
轉眼和白珊珊那位學長約定見麵的時間。
陸安然起了個大早,今天除了那位春風的老師,還約了個人。
陸安然小的時候有個朋友,王靜。
王靜是陸家廚師王叔的兒,比大兩歲,小的時候由於袁敏的原因,陸家上下沒有人對們母有好臉,並且時常背地裏待和苛責。
王叔一家是個例外。
不僅會對陸安然嗬護,私下還會給做些好吃的,讓不至於挨。
和王靜就是那時候好上的。
後來回了範茵鎮後,和王靜就了聯係,但是時不時還會有消息往來。
回到T市後,也第一時間和王靜說了。
二人約好今天一起吃個晚飯。
陸安然櫥裏的服飾千篇一律,牛仔和基礎款襯衫是最常見的搭配,但想到今天和春風的老師見麵,也算半個麵試了,為自己挑了一件略顯職業的襯樣式及膝,青春靚麗又不失溫雅。
出門的時候遇見阿荷,看到眼底裏的驚豔,陸安然有些不好意思,但是對自己這打扮還是滿意的。
隨後徑自出了門。
和不自己的男人結婚有一點好,那就是互不幹涉自由。
至於現在遭的冷眼。
並不太放在心上。
打小是苦過來的,靳寒淵至今為止對的把戲,和小時候過的並沒有什麽區別,無非是被排斥,被冷眼相待。
Advertisement
早就已經明白,人生苦短,不能浪費時間在不自己的人上。
對而言,母親的才是第一位。
挎起包,朝著山下走去。
靳寒淵昨晚在書房加班到很晚。
等他醒來的時候,陸安然已經離開有一會兒了。
陳管家為他端來早餐,報告說陸家小姐一大早就出了門,好像還刻意打扮了一番,不知道去哪兒了。
他皺了皺眉。
冷峻的五有些沉,出不悅。
這人是真把這裏當自己家了。
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把他當擺設?
正打算發脾氣的時候,手機鈴聲不合時宜的響了起來。
“寒淵,今晚7點來帝豪會所給我撐撐場子唄。”
唐元印紈絝子弟的聲音響起在電話另一頭:
“城東那塊項目不是要開始競拍了嗎,對方項目總拽的很,約了好幾次都不鬆口。
聽說這人老婆是你們靳氏集團的一個小供應商,公司最大項目就是你們家的訂單,所以你要是來啊,他肯定得給我賣個麵子。”
“不去。”
靳寒淵拒絕的幹脆冷漠。
“別啊,咱還是不是兄弟啊。”
聞言,靳寒淵沉默了會兒,繼續道:“幫你可以,好呢?”
“我就知道請你這尊佛貴的很!”
唐元印氣的跳腳,但卻隻能無可奈何的開口:“隻要你幫我,拿下項目後分靳氏5%的利潤。”
“8%。”
唐元印心裏罵了這個人千萬遍,最後咬咬牙:“。”
靳寒淵滿意的掛了電話。
“陳叔,我出去一趟。”
靳寒淵起邁步,可到了門口忽然想起了什麽,轉頭對著陳管家淡漠開口:
Advertisement
“陸家那丫頭回來後,你教點規矩,這是靳家,容不得這麽隨意的來來去去。”
“好的爺。”
陳管家彎腰垂首,恭順的問了句:“爺,您要司機嗎?”
“不用,我自己開。”
靳寒淵走車庫,從眾多豪車中選了一輛頂配法拉利。
他坐車中,鬆開襯衫的第一顆紐扣,出人的鎖骨,不羈中張揚著貴氣。
引擎發,轟鳴聲震耳聾,隨後揚長而去。
和瀟灑的靳寒淵不同,陸安然走到山下的時候,已經得不行了。
雖然日常都有鍛煉,這上千級階梯走下來,真的累得夠嗆。
覺得自己可能還要買個小電驢,不然以後真的上班了,通勤時間長不說,到學校可能都要沒半條命,如果是打車的話,本太高,也承不住。
陸安然下山後在路邊找了個早餐店,隨意的買了個飯團當午餐,囫圇吃了後,掐著點出發。
到咖啡廳時,方文鶴已經在那兒等了。
方文鶴大學時期和白珊珊同在一個文藝社團,現在是春風中學地金牌理老師。今日來這裏回見,確實是給了白珊珊麵子。
他先前也打探了一下陸安然地況,覺得不過是小鎮小老師,所以對這次會麵並沒有太高期。
“您好,我是陸安然。”
陸安然按照指定地位置來到桌前,對著麵前地人手禮貌問候。
“方文鶴。”
方文鶴站起,手到地指尖,輕微握了握後,笑著回了自己的名字。
二人客氣且禮貌。
Advertisement
隻是在抬眼時,方文鶴打量了下麵前的孩,有些驚豔。
今日隻穿了簡單常服。看起來著簡單,不是什麽大牌流,但整齊有質。
孩年紀很輕,有著一稚,但那清麗的麵容帶著一抹溫和的笑,像是淺夏的清風,讓人覺得親和可。
清麗之餘,上還帶著些許貴氣。
想起白珊珊和自己提過的的履曆,方文鶴兀自覺得有些訝然,一位小鎮姑娘竟然能有這樣的氣質。
但這抹驚豔轉瞬即逝。
“不好意思,我來晚了,您等久了。”
陸安然有些抱歉的說道。
“你推門的時候三點整,我坐下來的時候兩點二十九,隻差了零星幾秒。所以你沒有來晚,我也不算來早。”
方文鶴半開玩笑,緩和氣氛。
陸安然聞言也有些忍俊不:“方老師不愧是教理科的,數字敏很好。”
“陸老師也不愧是教語文的,誇人很有一套。”
二人相視一眼,都笑了。
方文鶴長得也很出眾,雖然沒有靳寒淵那般清貴,但五卻也幹淨齊整,有著鄰家大哥哥地親和。
二人是坐著,就是一副風景畫。
陸安然沒想到方文鶴這麽風趣,放下了些許張的緒,也稍微鬆弛了一些。
“方老師……”
剛想開口,就被方文鶴打斷了話茬。
“我名字就好。”
方文鶴看出了地張,試圖想讓放鬆一些,開口溫笑道。
“好……您我安然就行。”
“好的安然,既然已經認識,就不用客氣了。再用“您”這個稱呼,我可是要生氣了。”
方文鶴故意板起了臉。
陸安然笑著點了點頭。
不得不說,方文鶴給人的覺很好,斯斯文文,讓人忍不住放下戒備心。
“喝點什麽嗎?”
方文鶴不急著進主題,看著麵前地孩禮貌問道。
“果就好。”
“不喝咖啡嗎?”
“我不太喜歡,喝了夜裏要失眠的。”
“好。”方文鶴禮貌應了,隨後來服務生,點了一杯番石榴。
服務生將茶飲送上,二人對坐半晌後,陸安然有些忐忑地開了口:
“文鶴,珊珊應該和你說了我的況。”
“是的,說了。其實我好奇,珊珊說你在範茵中學教的不錯,而且也是編製,怎麽突然選擇辭職,春風再好也不過是個私立貴族中學,和製還是有區別的。”
猜你喜歡
-
完結500 章

陌路婚途
結婚四年,老公卻從來不碰她。 她酒後,卻是一個不小心上了個了不得的人物。 隻是這個男人,居然說要幫她征服她的老公? excuse me? 先生你冷靜一點,我是有夫之婦! “沒事,先睡了再說。”
89.4萬字8 73159 -
完結2312 章

有孕出逃:千億總裁追妻成狂
夏時是個不被豪門接受的弱聽聾女,出生便被母親拋棄。結婚三年,她的丈夫從來沒有承認過她這個陸太太。他的朋友叫她“小聾子”,人人都可以嘲笑、侮辱;他的母親說:“你一個殘障的女人,就該好好待在家裏。”直到那一天他的白月光回國,當著她的麵宣誓主權:“南沉有說過愛你嗎?以前他經常對我說,可我總嫌棄他幼稚。我這次回來,就是為了追回他。”夏時默默地聽著,回想著自己這三年和陸南沉在一起的日子,才驚覺發現,她錯了!結婚三年,夏時愛了陸南沉十二年,結果卻深情錯付。種種一切,讓夏時不堪重負。“陸先生,這些年,耽誤你了。”“我們離婚吧。”可他卻把她關在家裏。“你想走,除非我死!”
207.6萬字8.33 330489 -
完結380 章

插翅難逃之督軍請自重
她,是為姐姐替罪的女犯。他,是殺伐果決、令人生畏的督軍。相遇的那一刻起,兩人命運便交織在了一起。顧崇錦從來沒想過,一個女人竟然成為了他最大的弱點。而偏偏那個女人,卻一心隻想逃離他。宋沐笙也沒有料到,一心隻想保護姐姐的她,早已成為了男人的獵物。他近乎瘋狂,讓她痛苦不堪。為了留住她,他不顧一切,甚至故意讓她懷上了他的孩子,可誰知她居然帶著孩子一起失蹤......她以為她是恨他的,可見到他一身軍裝被血染紅時,她的心幾乎要痛到無法跳動。那一刻她意識到,她已經陷阱這個男人精心為她編織的網裏,再也出不來......
64.9萬字8.18 8586 -
完結8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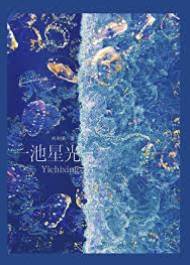
一池星光
夏星曉給閨蜜發微信,刪刪減減躊躇好久,終於眼一閉按下發送鍵。 食人星星【不小心和前任睡了,需要負責嗎?】 閨蜜秒回【時硯池???那我是不是要叫你總裁夫人了?看了那個熱搜,我就知道你們兩個有貓膩】 原因無它,著名財經主播夏星曉一臉疏淡地準備結束採訪時,被MUSE總裁點了名。 時硯池儀態翩然地攔住攝像小哥關機的動作,扶了扶金絲鏡框道,“哦?夏記者問我情感狀況?” 夏星曉:…… 時硯池坦蕩轉向直播鏡頭,嘴角微翹:“已經有女朋友了,和女朋友感情穩定。” MUSE總裁時硯池回國第一天,就霸佔了財經和娛樂兩榜的頭條。 【網友1】嗚嗚嗚時總有女朋友了,我失戀了。 【網友2】我猜這倆人肯定有貓膩,我還從沒見過夏主播這種表情。 【網友3】知情人匿名爆料,倆人高中就在一起過。 不扒不知道,越扒越精彩。 海城高中的那年往事,斷斷續續被拼湊出一段無疾而終的初戀。 夏星曉懶得理會紛擾八卦,把手機擲回包裏,冷眼看面前矜貴高傲的男人:“有女朋友的人,還要來這裏報道嗎” 時硯池眸底深沉,從身後緊緊地箍住了她,埋在她的肩膀輕聲呢喃。 “女朋友睡了我,還不給我名分,我只能再賣賣力氣。” 夏星曉一時臉熱,彷彿時間輪轉回幾年前。 玉蘭花下,時硯池一雙桃花眼似笑非笑,滿臉怨懟。 “我條件這麼好,還沒有女朋友,像話嗎?”
29.5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