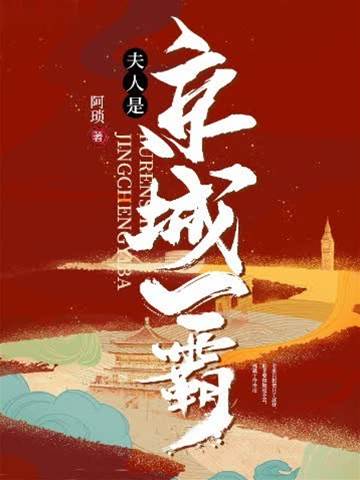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替身王妃帶球跑路了》 第34章 顧家往事
聽陸長洲這樣問,穆清葭有些錯愕。
抬眸朝他,片刻后笑了:“哪兒能呢,我如今是曜王妃,錦玉食,出都有車馬隨從,怎會不好?”
“自上回金麟池邊匆匆一見,至今已逾半年,我瞧你比從前瘦了許多。”陸長洲嘆了口氣,關心道,“幾次托我母親前去王府拜見,也總說沒見到你的面。送過去的東西可收到了嗎?背痛的病可有調理好?”
“都收到了。”穆清葭點頭,聲應話,“勞你和嬸嬸記掛。我一切都好,嬸嬸年紀大了,日后不必往王府跑,如若有事,派人來知應一聲便是。”
陸長洲又嘆了一聲,對著穆清葭溫善又自矜的笑容,到底沒再多問。
他也知道,一皇家深似海,但憑穆清葭再聰慧,要權衡偌大的王府后宅也不是易事,更何況還沒有母家可以庇佑。說自己過得好,又能有多好?如果真能事事順心,何至于他的母親去了幾次都不能見到的面?
左右王妃的上頭還有王爺,王爺若發了話,王妃的權力還能剩下多?周瑾寒要是個好相與的還好,可偏他的聲名在外,京城之中還有哪個不知道曜王爺是個心機深沉暴戾無常的?
他一芝麻綠豆大點的都已經聽到了那些傳言。說“抱病”多時,已經推了好幾家的邀約,上門去探的也竟是個個都被打發了,可見生病是假,惹了曜王爺才是真,如今想來正坐著冷板凳呢。
Advertisement
陸長洲每每聽說心里都擔憂,可終歸穆清葭已經不是那個住在他家隔壁的小姑娘了,隔著好幾重的王府院墻,他窺探不了,也不應再試圖窺探。
于是他只問:“妹妹要我做何事?”
覃榆送了一盞雪籠翠山進來又匆匆退了出去。
穆清葭轉頭向窗外,看著不遠那座羅綺盈檐的吊腳樓,看著翹的四角上垂掛作響的鈴鐺。
“兄長對流云榭可有了解嗎?”
陸長洲隨穆清葭的視線過去。
“不太了解,妹妹也知我素來無趣,參與不了這些風花雪月。”他的目平平靜靜的,對流云榭的存在既無迎合也無排斥,只是多有些無奈罷了。“只不過偶爾聽同僚們提起,說那兒是個一擲千金可媲仙宮的地方。”
“仙宮……”穆清葭笑了一聲。
若將流云榭比作仙宮,倒是也不算夸張,畢竟是京城中數一數二的院。
酒娘霓裳舞,香薰霧繞華清宮。京城中多文臣武將世家公子扎堆在里頭,詩作對,會友結朋,千金豪擲,沒點份地位都不好意思進去。
只是這“仙宮”卻不是朝廷公辦的風月娛樂場所。
穆清葭眼底降了溫度——更不該是一個因罪被罰賤籍的能夠去得的地方。
“京城中所有開設的樓坊店鋪在戶部都有登記,我雖對流云榭沒有過多了解,但況還是知道一些的。”
Advertisement
陸長洲見穆清葭似乎對流云榭有些興趣,便一五一十跟說道:“流云榭起自十年前,只用了不到一年便興盛至如今的形。登記在冊的老板是個南方人,世代務農,份背景極為簡單,并不像懂經營上的門道。倒是聽說里頭管事的媽媽長袖善舞八面玲瓏,在那些常客跟前很是得臉。”
“妹妹因何打聽流云榭?”
穆清葭沒有正面回答,收回視線后淺淺抿了一口茶湯,才又問:“兄長聽說過顧家嗎?”
陸長洲一時沒明白:“哪個顧家?”
“十五年前因宮變抄家,曾給前廢帝當過啟蒙老師,與我家王爺頗有淵源的顧闕顧大人家。”
窗外風起,楹簾招搖,陸長洲驚得翻了茶盞。
“妹妹說什麼呢!”
“兄長勿怪。”穆清葭神淡淡,卻不打算就此罷休,“我不是特意要讓兄長為難,著實是心中存疑,這才求兄長替我解。”
陸長洲的面平復了一下,狐疑問:“是曜王他……”
“不是。”穆清葭搖頭,“王爺并未向我說起過往事。”
靜默了一瞬,方目定定地看向陸長洲:“兄長想必也是知道的,在我進王府之前,府里就住著那個人了。”
“那名子?”陸長洲的眉心了。
四年前,周瑾寒將簪煙從流云榭帶走一事,在京城也算鬧得沸沸揚揚。
Advertisement
主要是流云榭中的姑娘價都高,非高富戶本都替們贖不起,再加上做出這事的人又是周瑾寒——一個半夜都能說出來嚇唬不聽話孩子的“活閻王”,戲劇分自然更高。
那時候人人都傳,這保不齊又是一段修羅佛、仙渡劫的神話。
陸長洲緩緩分析道:“當年的傳言中心大多都在曜王爺上,至于那名子,閑話里提起的也不過寥寥。妹妹今日問起顧家,莫非……”
他輕扣著杯沿的指尖一:“那子與顧家有關?”
“確實如此。”穆清葭點頭。披風罩住了大半個,只雙手籠在手爐上,出青蔥似的幾玉指。“是顧闕大人唯一的兒。”
“顧大人的兒?”陸長洲又驚了,“顧家不是滿門都被抄斬——”
似乎是自覺音量太高,他克制了一下,接著道:“十五年前之事,檔案上留下的記錄已經不多了。我只在剛進戶部之時翻閱舊歲戶籍,看到過顧家的記錄。闔族罰罪籍,男丁流放,眷為,偌大的家族幾乎無人活下來。”
倘若那子就是顧闕的兒,那如今就還是背罪的賤籍、是啊!六年前的大赦可并沒有算進去顧家!
想到這里,陸長洲冷汗都出來了。
不怪人人都懼怕周瑾寒,就這種私自買府的事,一個弄不好怒了天威就是抄家滅門的大罪,也就他敢做得如此明目張膽!
“可不對……”陸長洲的眉頭皺起來,“罪臣的家眷,一旦被罰賤籍淪為,一律都由教坊司轄制。登記造冊,年齡籍貫、生平過往、本家因何獲罪,每一筆都要寫得清清楚楚,并由禮部統一收管。倘若沒有陛下親喻赦免,即便老死都得死在教坊司。”
“那麼——”陸長洲向穆清葭,眼底沉下來,“怎麼會到了流云榭?”
猜你喜歡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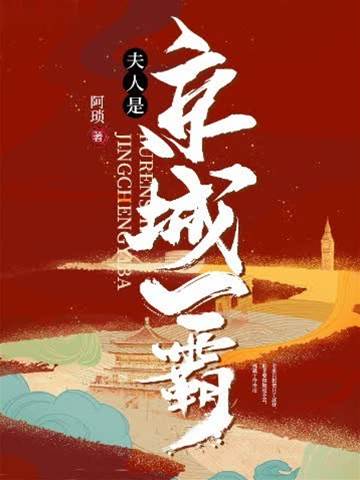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481 章

偏執暴君無能狂怒,皇后欺朕太甚
寧瀟瀟穿書後,意外獲得了可以修改劇情的金手指。 從此她便開啟了在後宮橫著走的爽文女主生活。 跋扈貴妃抱著她的大腿:「聽我說謝謝你,因為有你......」 腹黑皇后跪下對她高呼:「你是我的神」 連一貫對她愛答不理的暴君,竟也毫無徵兆的給她擬了一道封后詔書。 寧瀟瀟攥著封后詔書一臉懵逼:「???我沒改過這劇情呀......」 後來,她能修改劇情的秘密被暴君發現了。 「瀟瀟,幫朕改一個人設,關於你的」 「什麼?」 「吾心悅你,至死不休」
82.9萬字8 96711 -
完結206 章

公府嬌媳
謝知筠出身名門,千金之軀。 一朝聯姻,她嫁給了肅國公府的小公爺衛戟。 衛戟出身草芥,但劍眉星目,俊若繁星,又戰功赫赫,是一時的佳婿之選。 然而,謝知筠嫌棄衛戟經沙場,如刀戟冷酷,從床闈到日常都毫不體貼。 衛戟覺得她那嬌矜樣子特別有趣,故意逗她:「把瑯嬛第一美人娶回家,不能碰,難道還要供著?」 「……滾出去」 在又一次被衛戟索取無度,渾身酸痛的謝知筠做了一場夢。 夢裏,這個只會氣她的男人死了,再沒人替她,替百姓遮風擋雨。 醒來以後,看著身邊的高大男人,謝知筠難得沒有生氣。 只是想要挽救衛戟的性命,似乎只能依靠一場又一場的歡喜事。 她恨得牙癢,張嘴咬了衛戟一口,決定抗爭一把。 「狗男人……再弄疼我,我就休夫」
38.7萬字8 11279 -
完結852 章
醫品毒妃惹不得
二十一世紀最強毒醫蘇長歌,一朝穿越,成了雙目失明的蘇家嫡女。 庶妹搶婚,那渣男就扔了吧,誰愛要誰要! 庶母算計,那惡毒后娘就埋了吧,她親自挖坑。 渣爹冷漠,那就斷絕關系,從此讓他高攀不起! 一場轟動整個皇城的四皇子選妃大會上,她不經意路過,掛著如意環的繡球從天而降,恰好墜落到她的懷里。 權傾天下的冷面閻王四皇子眾目睽睽下一把拉住她,“找死呢?” 她雙目失明卻無所畏懼,當著所有皇家人的面,手捏毒針,精準的對準他,“想斷子絕孫呢?” …… 很久以后,四皇子容珩將蘇長歌緊緊擁在懷里,答了她的問題:“娘子舍得嗎?”
149.5萬字8 5884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