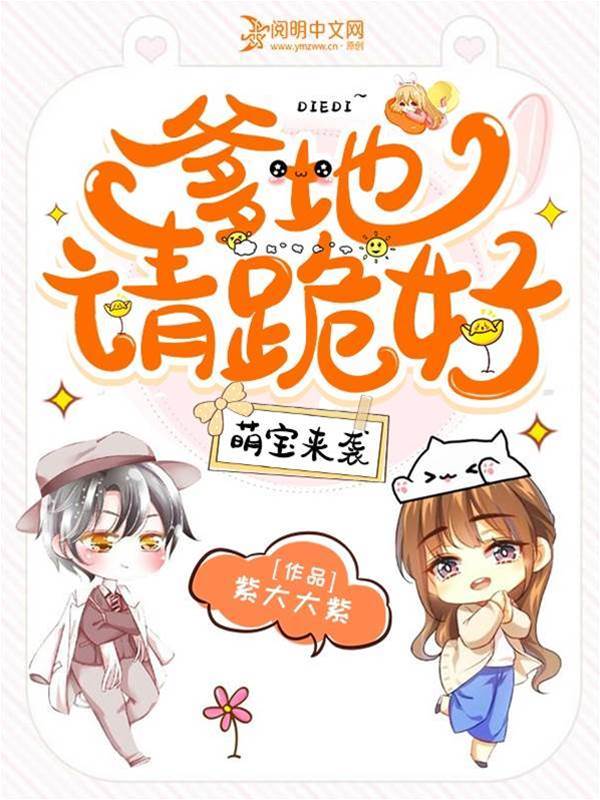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嫁給財閥掌舵人後,頂奢戴到手軟》 第81章 你愛上他了?
攥著纖細手腕的手不斷收,眼中怒火如火山發,磁的嗓音又沉又冷,“阮嫆,我是做了什麽十惡不赦的事,讓你這麽對我?”
“你不妨直接告訴我,我怎麽做你才滿意?”
阮嫆手腕被攥的生疼,還未來得及掙開。
腕上卻覆上了另隻修長冷白的手,溫熱的溫過掌心傳到腕上,作輕卻不容置疑。
冰冷狹長的眸眼底滿是鬱,蘊含著無數鋒利寒芒,隻聽他冷冷啟口,“鬆開,想問什麽,我來跟你說。”
涼薄的目冷嗖嗖的如同利劍,周如覆了層千年不化的寒冰,讓人不住脊椎發寒。
他不開口還好,一開口,似徹底將人激怒。
淩也放開那纖細的手腕,轉而一把揪住那冷傲孤清的男人領,怒火中燒,額上青筋跳。
恨的牙發麻,怒不可遏,“你那點把戲隻能騙騙人,慕景琛,你要真算個男人明正大和我較量,背地裏耍心機耍手段,趁虛而算什麽本事!”
心頭那把無名火,熊熊燃燒,怎麽都按捺不住。
慕景琛什麽話都未說,從他手中一點點出自己被抓皺的襟。
握住阮嫆的手,將人護到後。
削薄的掀起一嘲弄淡然的冷笑。
“你所謂的明正大,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糾纏?”
Advertisement
似還嫌火拱的不夠大,他慢條斯理的整了整被抓的領,淡聲道,“用錢砸人這招屢試不爽吧,我記著淩總投資了不藝人電影,捧紅了不人,確實眼獨到。”
“不過我人的事業還不到淩總心,若真想滿意,我作為的男人就可以代回答你,不要出現在我們兩人的世界裏,跟我都會很滿意。”
話落,似有火稍縱即逝。
淩也桀驁不馴的臉上猝然燃起濃烈的火,猶如狂風驟雨。
‘砰’的一聲將那疏冷矜貴,不疾不徐挑釁的人,一把按到了牆上。
聲音已是怒極,“你他媽再說一次?”
這卑鄙小人當著他的麵,話裏話外竟然都在試圖挑撥他們的關係。
阮嫆看著這兩人見麵水火不容,兩句不對,立馬又要打起來的模樣。
抿了條線,上前護在慕景琛前,終於忍無可忍,“淩也,算我求你,能不能不要再打攪我的生活。”
淩也聽見這話神狠狠地一,似沒聽清,低沉磁的嗓音止不住的抖,啞聲問,“你說什麽。”
“我們那麽多年義,比不過跟他短短兩個月是嗎?”他眼眶泛紅,似不敢相信,卻又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
阮嫆疲憊的輕闔了闔眼,再睜開眸一片決然,“結束了就是結束了,我說過了,跟任何人都無關。”
Advertisement
“他方才那話就是在故意挑撥,你聽不出來嗎?”他蒼白,如行走在沙漠絕的人,既生存又找不到出口,隻能無力辯駁。
“我沒有,之前的我是混,可絕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你要還願意給我個機會,一切我都可以解釋,你寧願聽一個外人信口雌黃,也不願信我?”
“不想聽,我曾給你無數次機會解釋,你都不屑一顧,真相到底什麽樣,現在都已跟我沒任何關係。”阮嫆冷冷的開口。
握住慕景琛的手,從容堅定的道,“而且他也不是外人,我不想再聽見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辱罵詆毀他。”
萬籟俱寂。
淩也隻覺得被棄的痛楚折磨如劇烈的毒藥,侵蝕他的五髒六腑。
甚至站立不穩的後退了一步。
抬起猩紅的眸看那絕的人,“你上他了?”
竟然為另一人與他作對,當著他的麵維護那人,心髒刺痛,鬱結難消。
聽見這話,原寡淡涼薄的人也微微站直了子,視線落回上,清冷的神收斂了冷嘲,眸底一閃而過的不安,指尖微蜷,張的攥了的手,似也在等答案。
阮嫆微愕,一時不知該怎麽回答,從未想過不慕景琛,隻知道並不排斥跟他在一起,也願意縱容他的小心機。
若說喜歡肯定是有的,說還太遙遠。
Advertisement
直到現在也覺得,他們還是隨時可以分手的關係,不一定真能走到最後。
雖然如此卻也不想因此被淩也窺出破綻,再來糾纏。
冷聲答,“是,所以別再糾纏。”
話落,拉著慕景琛往外而去。
淩也著破碎的聲音,在後突然譏諷,“阮嫆,別騙自己了,你不他。”
因為我見過你回答不一個人是什麽模樣,所以也能輕而易舉的看穿你的偽裝。
他邊溢出慘淡的笑,那向來煥發的英氣全然消失,看向立在旁邊的頎長影,嘲諷道,“慕景琛,你還是什麽也不是。”
阮嫆覺到側的人背脊一僵。
慕景琛薄抿線,出涼薄的婺殘冷,下頜線越繃越,強忍著將那人狠揍一頓,讓他閉的衝。
腦中卻還存著一理智,不能這麽做,這是阮氏,若他手說不準隻會招來的厭惡。
線條冷的頜骨微,克製而忍的,什麽話都未說,反握了的手,往電梯間走。
不理會後那個瘋子。
溫暖的大手頭一次似用盡了全力,將手握的發疼。
掙開,卻被握的更。
出了大樓,拽住那不大對勁的人,這才發現狹長疏冷的眼尾薄紅。
一閃而過的水霧,眨眼間就消失不見,沉無盡的寒風中。
阮嫆心頭一震,斥責他弄疼的話梗在頭。
風吹來,黑曜的碎發在冷風中放肆的飛揚,散在拔的額前,遮去他幽深眸裏流的暗影。
棱角分明冷漠疏離的臉上著凜冽狠決,如同褪去所有偽裝地獄而來的修羅,讓人不由打了個冷。
“慕景琛,你別聽他胡說……”愣愣的開口解釋。
話未說完,下一瞬就被人擁進了懷裏,的,恨不得鑲嵌進他的懷裏。
冰冷到蜇人的聲音,抑著緒,佯裝雲淡風輕的緩緩開口,“沒關係,我們有一輩子時間慢慢培養,你在我邊就行。”
猜你喜歡
-
完結566 章

顧先生的金絲雀
c市人人知曉,c市首富顧江年養了隻金絲雀。金絲雀顧大局識大體一顰一笑皆為豪門典範,人人羨慕顧先生得嬌妻如此。可顧先生知曉,他的金絲雀,遲早有天得飛。某日,君華集團董事長出席國際商業會談,記者舉著長槍短炮窮追不捨問道:“顧先生,請問您是如何跟顧太太走到一起的?”顧江年前行腳步一頓,微轉身,笑容清淺:“畫地為牢,徐徐圖之。”好友笑問:“金絲雀飛瞭如何?”男人斜靠在座椅上,唇角輕勾,修長的指尖點了點菸灰,話語間端的是殘忍無情,“那就折了翅膀毀了夢想圈起來養。”
159.6萬字5 1757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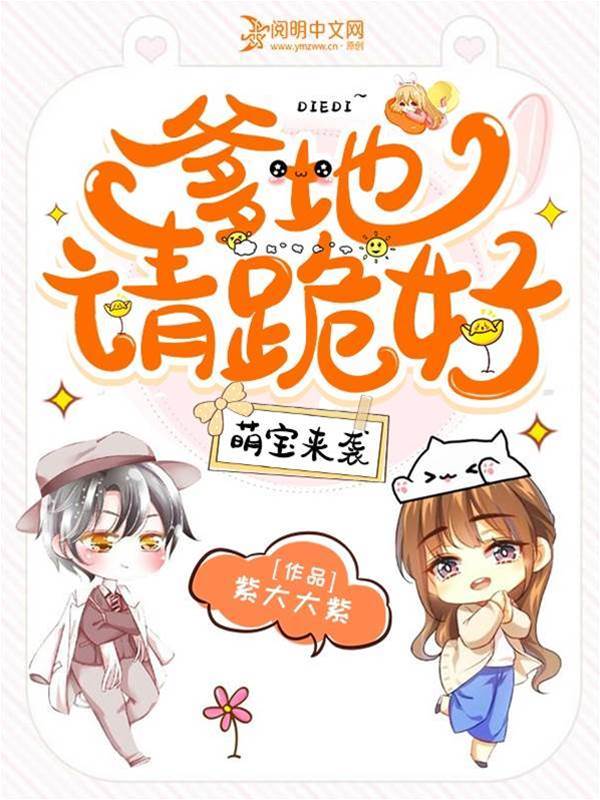
萌寶來襲:爹地請跪好
她在家苦心等待那麼多年,為了他,放棄自己的寶貴年華! 他卻說“你真惡心” 她想要為自己澄清一切,可是他從來不聽勸告,親手將她送去牢房,她苦心在牢房里生下孩子。 幾年后他來搶孩子,當年的事情逐漸拉開序幕。 他哭著說“夫人,我錯了!” 某寶說“爹地跪好。”
129.7萬字8 24178 -
完結83 章

墜落
周挽X陸西驍陽明中學大家都知道,周挽內向默然,陸西驍張揚難馴。兩人天差地別,八竿子打不到一塊兒。誰都沒有想到,有一天這兩人會站在一起。接著,流言又換了一種——陸西驍這樣的人,女友一個接一個換,那周挽就憑一張初戀臉,不過一時新鮮,要不了多久就…
32.4萬字8 6560 -
連載400 章

訂婚宴,陸總偷偷勾她尾指
[又名:訂婚宴,被前任小叔親到腿軟]、[京圈佛子強勢上位!]京圈太子爺陸野的未婚妻顧言驚豔、勾人、脾氣好,圈內皆知有陸野的地方必有顧言,某天,聽說顧言提了分手。陸野散漫,“說了她兩句重話,不出三天,她會自己回來。”三天又三天。陸野醉酒沒人接,忍不住撥了顧言號碼,竟然被拉黑了。有八卦拍到顧言被神秘男人送回家,陸野驀地心裏空了一塊。後來,聽說陸野不顧暴雨狼狽,偏執的在前女友家門口站了一夜。第二天,那扇門終於打開。“言言!我想你…”一抹頎長的身影裹著浴巾走來。“小叔?……言言?”那個驕矜尊高的男人攬顧言入懷,睨向陸野,“你該改口了。”—那晚,顧言把陸野的小叔給睡了,第二天她又怕又後悔,轉身就逃。她辭了工作,換了住處。電梯遇到他,她假裝等下一趟。直到她在酒吧與人相親,直接被人擄走。逼仄的小巷,沉重的氣息侵入,強吻,“再跑,腿打斷。”—他一步步誘她深陷,怎麼可能逃出他手掌心。
70.5萬字8.18 30461 -
完結1 章

又是落花時節逢君
“向老師,你真的要申請離開去南疆支教嗎?那邊教學條件極差,方圓百里都找不到幾個支教老師。”看著向晚拿來的申請材料,校長有些疑惑。 畢竟她還有兩個月援疆期就圓滿結束了,這個節點上她卻突然申請去更遠更偏僻的地方繼續支教。 向晚扯起一抹笑意,聲音平和卻異常堅定:“是,校長。我已經向組織重新申請了兩年,我要去南疆。” 見她去意已決,校長也不在挽留,直接在申請書上蓋章:“等組織審批,大概十天后,你就可以走了。” “不過這事你和江老師商量好了嗎?他把你當心眼子一樣護著,怎麼能舍得你去南疆那邊。” 向晚面上一片澀然。 全校都知道江野是二十四孝好老公,對她好的就像心肝寶貝一樣。 可偏偏就是這樣愛她入骨的男人,竟會出軌另一個女人。 這叫向晚有些難以理解。 難道一個人的心,真的能分兩半交給另一個人嗎? 她搖搖頭堅定地表示:“不用跟他說了,反正他援期也快結束了。” 校長不明所以地看了她好幾眼,終究是沒開口。 剛走出門就收到黃詩琪發來的照片,還沒點開看。
3萬字8 1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