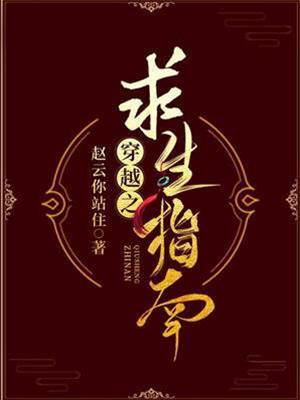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燕宮殺,公子他日日嬌寵》 第65章 新的謀算
車一時靜了下來。
他仿若無事一般自顧自斟了茶細細啜飲,信口問道,“你猜,你舅舅為何不敕封你為郡主,或是公主?”
小七不答他。
自己是什麼出,在沈家又是什麼境遇,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有關氏與沈淑人在,這輩子都不可能做什麼郡主公主。
但也并沒有什麼關系,沈淑人如今是魏國公主,不也要嫁給燕莊王那個生了病的老頭子嗎?
可見做公主也并沒有什麼好。
只盼著回桃林,山間柴門自在地過余生。
但那人所想與顯然完全不一樣,那人道,“魏國的郡主在燕國為奴為婢,他們卻毫無辦法,丟不丟人?”
小七心頭一凜,原來如此。
抬眉向許瞻,那人拈起帕子拭凈了上漬,繼而挑開帷幔,將帕子扔了出去。
心口一窒,想,在許瞻心里終究是不干凈的,是個“臟東西”。
但這不算壞事,于而言,他的嫌惡是好事。
守著子之,待攢夠了五百刀幣便能干干凈凈地回魏國,干干凈凈地見大表哥。
Advertisement
那人兀自閉目養神,那棱角分明的臉也只有闔上一雙犀利的目時才能顯出幾分和來。
王青蓋車四角垂下的赤金鈴鐺叮咚作響,十六只馬蹄在燕宮的青石板上踩出清清脆脆的聲響。
終究是離長樂宮越來越遠。
也離的大表哥越來越遠。
小七乖順坐著,心里卻百轉千回。
暗暗盤算,總得先想辦法見大表哥一面,把許瞻的謀全盤托出。
一個人不了事,要離開蘭臺,必須借槿娘的力。
而如今槿娘尚被關在柴房,許瞻又盯得,要便好似只有裝病一條路可走。
轉念一想,倒也不必裝病。
這子里的傷沒有好全,究其原因到底是轅門那一摔傷了本,后來斷斷續續地飲著湯藥,但時有時停的,至今也并沒有什麼起。
眼瞧著自辰時至現在一滴湯藥都不曾飲過,的確也該發病了。
若是昏倒,抑或爭點氣再流些鼻,便能回聽雪臺將養,那槿娘作為蘭臺唯一的婢子,自然要回來照顧的湯藥。
心里想得清清楚楚,人也已經到了蘭臺。
Advertisement
聽周延年“吁”地一聲勒住了馬,便見許瞻徑自下了王青蓋車。
那人還在生氣,并不理會,甚至連一個眼風都不曾往后掃來。
小七想,不理會才好,他若總盯著,倒妨礙了施展演技。
悄悄掀開帷幔向外瞧去,蘭臺真是壇宇顯敞,高門納駟,便是在府邸之外亦能到森嚴的迫。
是如論如何都不愿邁進蘭臺的大門。
于而言,這地方形同牢獄罷了。
小七心里悶悶的,提起袍便跳下馬車。
這一跳,果然險些流出鼻來。
已經覺到腥氣就在鼻腔之中了,可惜差
了些火候,竟沒能流下。
若定要跟他到青瓦樓的話,有把握在到青瓦樓之前便他相信——一如從前一樣發了病。
守在雙闕的帶刀侍衛恭謹施禮,“公子回來了。”
許瞻淡淡應了一聲,自顧自上了臺基往府里去了。
小七提起袍擺跟上去,那人量高步子又大,不需多久就輕易將甩在后。
若是嫌慢了,倒也能停步看上一眼,開口時聲音清清冷冷的,“跟不上便周延年扛你走。”
Advertisement
小七心里不是滋味。
什麼了?
再跑了幾步,鼻尖一酸,那早就候在鼻中卻遲遲不肯落下的吧嗒一下墜了下來。
手接住了,暗暗松了一口氣。
緩緩停下步子,就那麼眼睜睜地看著一滴一滴地墜到手心來,頭頂的青天白日刺得人睜不開眼,心里的竊喜卻蓋過了短促的息。
小七的手微微發起抖來,低聲他,“公子”
還不待抬頭,一片黑影已了過來,繼而是緋的袍與垂至腳踝的玉佩閃進眼簾。
子一輕,旋即天旋地轉,原是被那人打橫抱了起來。
不說人怎樣,但他上的雪松味真好聞呀。
忽而竟生了一種奇怪的覺,約覺得他的懷抱十分悉,好似從前便被他如此抱過一般。
但分明是沒有的。
若是細想,便斷定是沒有過的。
他嫌子污穢,恨不得敬而遠之,尤其曾數次要將打發到軍營里去,說低賤浮,是娼,是臟東西。
因而自然是沒有的。
日雖盛,小七卻凜然生寒。
下意識地著許瞻,那人眉峰蹙著,薄抿著,那雙眸神復雜,此時此刻,他在想什麼呢?
小七辨不分明。
低喃道,“公子,奴想回聽雪臺。”
那人沒有說話。
小七當他沒有聽見,抬手去抓他的手臂,“公子”
那人垂眸來,依舊沒有說話。
他不應,便一直不肯松手,依舊道,“公子。”
以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方式要會魏使,就一定要回聽雪臺。
青瓦樓就在他的眼皮底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
那人凝眉不展,半晌過去,總算淡淡地應了一聲,“嗯。”
心里一安,十分清醒,“公子,奴與槿娘在一起久了,想要槿娘陪著說說話”
那人又是淡然應了,“知道了。”
小七這才垂下手去,心里驟然一松,繼而歉然嘆道,“弄臟公子了。”
便見那人眼角一紅。
的臉頰在他的口,能到他膛的起伏比方才更甚。
他的膛寬厚結實,他的雙臂強勁有力,那是一雙能安邦定國的手,亦是一雙能攪弄風云的手,是一雙能挽雕弓天狼的手。
骨節分明又力道極大的手。
猜你喜歡
-
完結105 章

嬌嬌(重生)
燕家嬌女,殊色傾城,寵冠后宮, 一朝國破,跌落塵埃,被新帝強占,屈辱不堪。 一杯毒酒恩仇兩訖,再睜眼,她回到了十六歲。 曾經的冤家一個個你方唱罷我登場, 瑟瑟眼波橫流,笑而不語:前世的賬正好一并算一算。 孰料,被她毒死的那位也重生了。 瑟瑟:!!!藥丸T﹏T 為了活命,瑟瑟不得不扮演前世的自己。 然而,常在河邊走,難能不濕鞋? 真相大白, 那人狠狠鉗住她的下巴,目光冰冷:敢騙朕,嗯? 奉爾入掌,嗜爾入骨 因愛生恨黑化大佬VS美貌動人心機嬌嬌,架空,雙重生甜寵向,1V1,he。
35.5萬字8 30986 -
完結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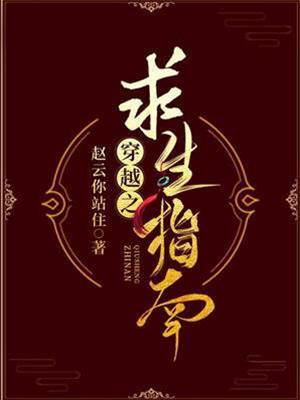
穿越之求生指南
同樣是穿越,女主沒有金手指,一路艱難求生,還要帶上恩人家拖油瓶的小娃娃。沿街乞討,被綁架,好不容易抱上男主大腿結果還要和各路人馬斗智斗勇,女主以為自己在打怪升級,卻不知其中的危險重重!好在苦心人天不負,她有男主一路偏寵。想要閑云野鶴,先同男主一起實現天下繁榮。
34.7萬字8 6919 -
完結522 章
寵后之路誤惹狼君萬萬歲
辛鳶對天發誓,當年她撿到家裏那頭狼時純粹是因為愛心,要是她知道那頭狼會有朝一日搖身一變成為九五至尊的話,她絕對……絕對會更早把他抱回家! 開玩笑,像這樣美貌忠犬霸氣護妻的狼君還能上哪找?不早點看好,難道還等著別人來搶嗎?某狼君:放心,誰來也搶不走! 辛鳶:我得意地笑了~
91萬字8 20048 -
完結315 章

攬芳華
京城落魄貴女馮嘉幼做了個夢,夢到了未來的當朝一品。 醒來後,發現竟然真有其人,如今還只是大理寺裏的一個芝麻小官。 她決定先下手爲強,“劫”走當夫郎。 北漠十八寨少寨主謝攬,冒名頂替來到京城,潛伏在大理寺準備幹一件大事。 沒想到前腳剛站穩,後腳就被個女人給“劫”了。
48.7萬字8.18 854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