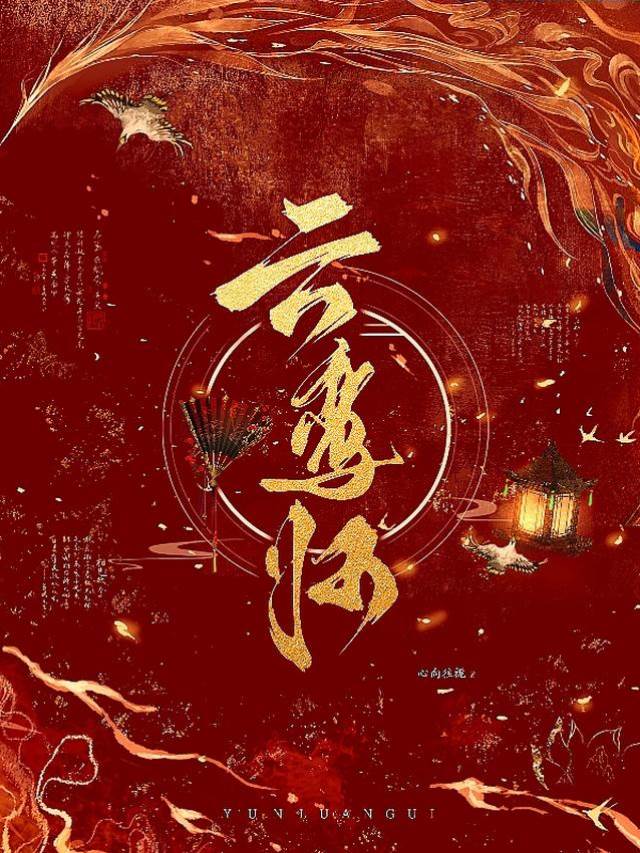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瑤臺春》 第 33 章
自從聖上將留在道觀之後,鄭玉磬很聽見有人敢直接稱呼自己的名字,便是有,那也不是什麽好話。
雖然窺見了寧越一些,猜測這並不是他的本來麵目,但就是這樣看著他,也實在不知道到底是哪位相或者有仇的同鄉男子宮做了侍。
顯德為了討好,把寧越的檔案調出來給看,他家中犯了大罪,又無力用金錢贖買,隻能被連坐,宮為奴,他的籍貫與來曆極為陌生,自己也瞧不出什麽不妥當的地方。
但瞧見他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眸裏一顆一顆湧出淚來,從那張合的麵上蜿蜒而下,鄭玉磬卻又有一瞬間的心。
寧越苦笑了一聲,或許也是得益於這副卻致的皮囊,自己這樣矯才不會心上的子覺得討厭。
“總管日披著一副假皮囊,不覺得累麽?”鄭玉磬認真地審視著他的容貌,強自鎮定:“本宮從未見過你的真麵目,談何記得?”
寧越搖了搖頭,手去按彈不得的小,苦笑道:“還是眼下這般最好,若以真麵目相對,娘娘夜裏怕是要做噩夢的。”
他從出口的那一刻便已經後悔了,如今的他已經算不得一個男人,麵容醜陋可怖,份低賤,又何苦連最後一點麵和自尊都不留給當初那個意氣風發的慕容儼呢?
慕容儼早該死在獄的第一天,從生到死,一直都是那個傾心
的九公子,接下去多活一刻鍾,都隻是在為慕容氏又添了一分辱。
鄭玉磬怔怔瞧著他,他語氣裏的落寞與淒楚並不似偽裝,但人心隔肚皮,不敢留一個不知底的人在自己邊:“本宮從前認識你嗎?”
“何止是認識……”寧越苦一笑,跪坐在榻邊,到手底的筋絡重新變得,才輕地把鄭玉磬的放下:“奴婢不才,尚與娘娘有過一段未的姻緣。”
Advertisement
他見到鄭玉磬眼中的震驚也不覺得意外,隻是展了袖口,將手臂上的那一塊月牙形狀的陳舊傷疤給瞧,眼中微含了些期盼:“慕容家的九郎君,不知道娘娘還記不記得?”
那傷疤是馬球桿所造的舊傷,當年他便是用這隻手來接擲過來的果子,而後在馬球賽的下半場負了傷。
不過對方既然是聖上的皇子,家中也便隻好忍下這口氣,當作是競賽時的一時失手。
“你不是已經在牢中自盡了麽?”對於慕容儼這個人,鄭玉磬如今得想一想才能記起來,著與那人完全不符的麵容,“蕭明稷說你不堪刑,夜裏被人發現便扔到荒山野嶺去喂狼了……怎麽會宮做侍?”
難以置信地盯著眼前人看,若說完全不同倒也不是,雖然人遭折磨以後形不可避免有些改變,但骨架總還是在那裏的。
他們這些世家的公子,便是寧肯去死也不會辱宮,記憶裏的
慕容儼便是這樣的人,這樣活下去有時候還不如死了。
“娘娘不必這樣看著我,奴婢是自願宮的,”寧越淡淡一笑,剩下的卻不願意多言:“若不進宮,便得同家人一起去服苦役,又或者凍而死,有時候進宮反而還好些,服侍了貴人,得到娘娘的喜歡,說不定將來還有別的轉機。”
他忍恥宮,除了是因為想要謀一條生路,也是有想要接近紫宸殿的意思。
三皇子的權勢再大,聖上若要他死他也活不到第二天,曆朝曆代的宦政、殘害忠良一事並不在數,多他一個不多,他一個也不。
但是被投那暗無天日的牢籠,他這輩子都不會有接近天子的機會。
一開始侍監選拔他來錦樂宮的伺候時候,說不失是不可能的,然而當三皇子那邊傳來消息,他知道這個貴妃是鄭玉磬、特別還懷有孕之時,他突然便生出一個更絕妙的主意。
Advertisement
聖上畢竟是久經的君主,即便年邁昏庸、聽信讒言,恐怕也得再等個二三十年,他的子未必能熬到那個時候,彼時聖上邊伺候的人也未必是他。
同樣是斡旋在紫宸殿與蕭明稷之間,與其去賭那麽一個未來,倒不如扶持貴妃的皇子登位,即便他死了,隻要貴妃的小皇子能登上那個位置,也不會蕭明稷有機會活下去。
天家骨之間的誼太淡薄,貴妃也是個聰明的人,不會意
識不到蕭明稷對於皇位的威脅。
“有時候奴婢也在想,是罪孽之,割了也便割了,”寧越勉強笑道:“隻是天意弄人,兜兜轉轉,又來伺候了您,有時候想要盡心盡力伺候您,也隻能用別的工夫”
“我不用……你不必這樣伺候我。”
鄭玉磬斜倚在靠枕上,本來是因為上的疼而難驚醒,但是如今卻睡意全無了,心中微含疑:“可是原本慕容伯父是襄助廢太子的,蕭明稷將你全家下獄,你怎麽肯為他做事?”
蕭明稷雖然不肯求,但是他邊的人卻了不訊息給。
慕容氏與太子勾結,三殿下雖說是太子一黨,但也得秉公執法,聖上對於太子縱然容忍,然而及底線也該清理一些不知好歹,在皇帝年富力強之時就想要從龍之功的臣子。
慕容儼無論手上有沒有沾過骯髒的事,那些他父親所搜刮來的民脂民膏,總是他用過的,依照殿下對貪腐的深惡痛絕,便是直接殺了他家也沒什麽。
畢竟涉及朝政,鄭玉磬也不好多問,這些人搜刮的汗累累,到了被清算的那一日,必然要加倍償還,慕容儼熬不過去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作為他從前的未婚妻,能做到這一點已經是仁至義盡。
Advertisement
的郎即便行事狠辣一些,也是為了朝局,為了民眾,父兄的江山更安穩一些,因此後麵也不敢再求蕭明稷,怕他覺
得是個是非不分的子。
但如今瞧著寧越這張臉,卻對這句話產生了搖。
他的所作所為當真如此大義凜然嗎,難道就沒有摻雜半點私心?
寧越見怔怔,以為是不信自己所說,珍而重之地捧起的手,引導用指尖輕輕自己額頭的傷,隔著致的偽裝他難以言說的傷痕:“東宮將慕容氏看作了棄子,任憑三殿下置,奴婢若要謀求一條宮的生路,自然得倚靠主事的欽差。”
旁人如果畏懼死罪而想淨宮當然沒有這麽容易,但他有這樣的想法,卻比做修建宅院的宮奴、又或是直接揚了骨灰更加蕭明稷痛快。
特別是他被派遣到錦樂宮這事,說沒有蕭明稷暗中的運作,恐怕是不的。
他的心上人為了天底下最尊貴之人的妃妾,懷著聖上的孩子,卻被肆意地玩弄和拋棄,而他的每一次靠近與示好,都鄭玉磬無比厭惡。
聖上在錦樂宮與貴妃親昵的每一刻,都在提醒這位近服侍的掌事,他是個低賤的閹人,不像是聖上那般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給予作為人的快樂。
這種臥薪嚐膽的煎熬有他一個人知道就夠了,若不是貴妃憔悴如斯,又瀕臨生產,他也不願意告訴。
鄭玉磬須得用些力氣才能到裏的凹凸不平,不同於普通人理的走向,那裏約有一個刻字。
隻有被流放的囚犯才會在臉上
刻字,宮中伺候貴人的侍沒有了下麵,卻不必這樣的侮辱,慕容儼卻將這兩項奇恥大辱都盡了。
坐在那裏不聲不響,直到一方的帕子拭的麵頰,鄭玉磬才察覺自己流淚了。
“奴婢同娘娘說這些,不是為了娘娘可憐同奴婢,”寧越聲道:“家父卷進東宮之爭,原本就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搭上了家命,娘娘不必過門一同到連累,也是一件好事。”
“奴婢知道,您子並沒有外麵說的那般差,”寧越聲音低下去,似乎是擔心隔牆有耳,他著鄭玉磬的小腹:“您若是有什麽要做的事,枕珠與岑太醫怕是不夠的。”
他觀察細致微,貴妃似乎不太願與聖上行男之事,但也是自從有了鍾氏之後,貴妃才敢放心地誇大子的不適,假稱落紅晦氣,子倦怠不堪,將聖上推到別人那裏去。
即便是如此,聖人留宿錦樂宮的時間也仍然不。
心思被人破,鄭玉磬也頗震驚,每次請太醫診脈都是隻留枕珠在殿,除了岑太醫與和枕珠之外,並無第四個人知道子的況。
寧越不能近,竟然也會猜出來?
“娘娘放心,三殿下那裏知道的事,同外人並沒有什麽兩樣,”寧越笑了笑:“三殿下尋來一個與孝慈皇後與幾分相似的子,雖不是出自娘娘的授意,卻合了您的心意,對麽?”
“
你說鍾婕妤?”
鄭玉磬隻見過鍾妍一麵,那時還是東宮的宮人,那個子的容貌固然不錯,但說實話也沒到聖上寵的地步。
若有所思地躺回了枕上,“難怪……難怪大皇子妃會不惜拋頭臉,到我宮門前跪著。”
廢太子妃這個時候最不應該得罪的就是,然而那個子卻似乎心底有了把握一般,不僅這個貴妃庶母難做,還一個宮人在聖上麵前臉,刻意勾引。
或許那個時候廢太子妃與蕭明稷明麵上高低不讓,心底卻都如明鏡一般,嘲笑這個被蒙在鼓裏的貴妃,聖上放在心上的人從來隻有孝慈皇後一人,隻是一個自以為是的癡人。
追查欠款是一件難事,蕭明稷的目的都已經達到了,這片爛攤子聖上肯親口下令不許再提,不止是東宮鬆一口氣,他也是求之不得。
之前高估了自己在聖上心中的份量,也從未害過別人,尚且不敢輕易下手……如今看來,倒是多慮了。
“你先下去吧,容我緩一緩。”
現在驟然知道了許多事,實在是半分睡意也無,心中混沌不安,但是瞧見跪在地上不能窺見真實麵目的寧越,又有些不忍地歎了一口氣,聲道:“明日……便進來伺候,不用站到外間去了。”
寧越瞧了一回,見貴妃麵略好了些,才應了一聲諾,重新將的鎖子帳掩好退了下去,獨留鄭玉磬一人高床
枕,無法眠。
自己的丈夫好歹還與有一個孩子,若是秦君宜九泉之下有知,冤魂也能稍稍安心,慕容氏雖然咎由自取,但慕容儼的經曆,已經是罪罰過重了。
皇帝的調令下得急,他們夫妻二人知道這一別或許便要一兩年,夜裏癡纏自然便多了,想著法子能盡早有孕才好,省得鄭玉磬沒有孩子,在別人麵前被了一頭。
隻是兩人私底下行周公之禮都不敢第三人知道,生怕母親和幾位嫂子小姑知道了生氣笑話。
秦君宜是一個守禮的君子,但熱主起來的時候卻又沒有男子可以拒絕,又是即將分別,不說妻子,他也是想得厲害。
那個時候已經褪去了聖上如今常常歎的青,不斷地親吻郎君的頸項,那裏是他最不得人的地方,壞心思地坐到他懷裏,把他親得眼中含淚,子也跟著輕,撒要他力氣大些,兩個人正大明地在書房裏待著,卻總在做些的事。
連婆母都有些好奇,怎麽兒子考上了進士,也有了妻做伴,那些日子反而比從前更加用功了些。
後來出長安城的時候,他覺得男子在這件事上哭泣有些丟人,翻做主了兩回,想振一振夫綱。
本來在外麵是害的,但是想一想夫君這樣一走,蕭明稷還不知道要怎麽迫再出去見一麵,半推半就便從了,逆旅分別之後,用帕潔淨了
子才了去道觀祈求保佑生子的心思。
猜你喜歡
-
完結2981 章

冷君一笑傾城
“王爷!王爷!王妃把大蒙国皇子挂城墙上了!”某王爷一挑眉:“瞧瞧,我家王妃就是举止有度。去,把他衣服扒了,给王妃助助威!” “王爷!王爷!王妃闯进皇宫把三皇子给揍了!”某王爷一弯唇:“揍得好!王妃心善,必不舍得下狠手,去,把三皇子再揍一遍!” “王爷!王爷!王妃给您写了封休书,贴到金銮殿殿门上了!”某王爷拍案而起,夺门而出:“反了她了!进了本王的门,就是本王的人!想走?没门儿!”“王爷!王爷!王妃把大蒙国皇子挂城墙上了!”某王爷一挑眉:“瞧瞧,我家王妃就是举止有度。去,把他衣服扒了,给王妃...
524.2萬字8 39937 -
完結501 章

天才萌寶腹黑娘親
一朝穿越,變為農家女,家徒四壁也就算了,為何身邊還帶了個拖油瓶? 幾經波折,才發現原來與她生出這個拖油瓶的男人一直在她身邊,更讓她大跌眼鏡的是,這個男人的身份,並不尋常……
88.4萬字8 16272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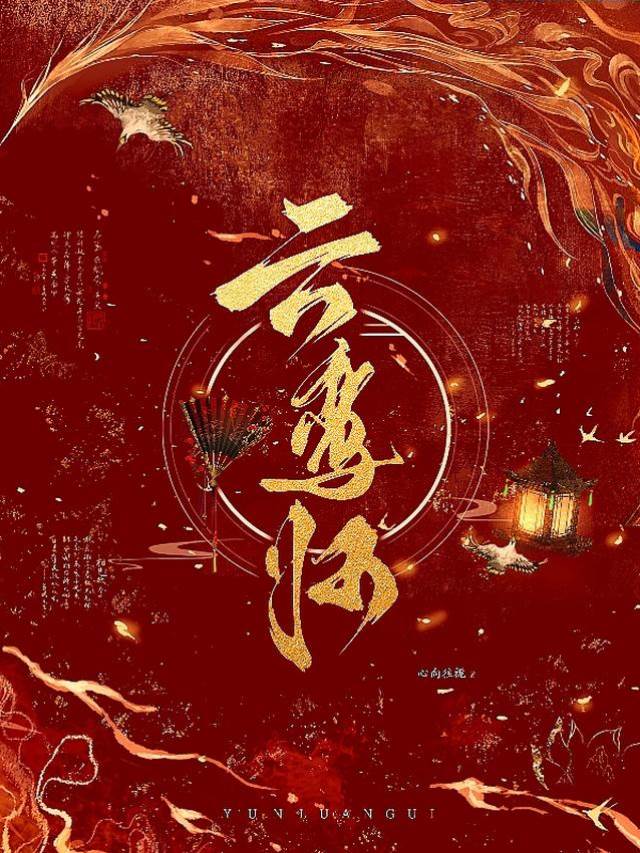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
完結178 章

青柯一夢(探案)
平靜祥和的縣城突發兇案,兩名死者曖昧的倒在一起,是殉情,是謀殺?衙差很快便鎖定了兇手——什麽?是我?我可剛穿越來啊!菜鳥律師只好據理力爭為自己雪冤,突又蹦出個書生嗆聲,嘿,你又是誰!王羽書身份坐實,然丫鬟失蹤,記憶全無,落水真相成謎,又遇到一樁接一樁的奇案~還有你,你這個可疑的書生,你到底是誰!【架空王朝·懸疑長篇·雙潔】感情戲主極限拉扯,相互試探;後期男主追妻狂魔雙強大腦,同頻共振。案件篇:三殺開局,疑兇竟叫武大郎?貴妃醉酒一曲衷腸,伶人卻遭拋屍辱身?鸚鵡學舌,五鬼運財,究竟是誰嚇破了膽?采花大盜喜好獨特,案中有案玄機幾何?……【主偵探(女主)視角,第一人稱沉浸式破案,不喜慎入】【案件無玄幻要素,謹記唯物主義科學發展觀!】——————預收:《甘棠遺愛(探案)》,又名《少卿走遠,別影響我斷案》青朝天寶年間,威震朝野的天下第一女推官馮昭遇刺身亡,帝震怒,令刑部牽頭速查此案。然馮昭屍體莫名消失,查其遺物更發現敵國傳國玉璽。一時間,馮昭陷入叛國罪名,無人再查她的被刺。此案束之高閣,終成懸案。十年後,身份來歷不明的女俠客馮棠舟欲重翻舊案,卻屢受時任大理寺少卿淩西竹阻擾。她疑他牽涉舊案,表面公正無私,實則作僞瞞騙他疑她身份作假,表面大義凜然,實為攀附名聲然面臨一樁樁詭異奇案、一雙雙攪局黑手,竟也是她為他撥雲見日,他為她正道尋心【刀子嘴刀子心女俠客vs腹黑冷面小侯爺】【古風推理單元文,力主本格】同樣的架空王朝,不一樣的單元探案故事!更有王羽書限時返場呦~~內容標簽:情有獨鐘 穿越時空 懸疑推理 正劇 HE 單元文其它:本格推理搞事業大女主
59.8萬字8 186 -
完結116 章

失憶后的夫人又軟又甜
攝政王沈縱與夫人明芙成親多年感情不睦。明芙執意要與沈縱和離。 只是沒想到,兩人正要和離之時,明芙的腦袋被花盆砸了,昏迷不醒,生命危在旦夕,若是當晚醒不過來,必死無疑。 沈縱不想明芙死,便威嚇道:“明芙,我們還沒和離,如果你現在死了,這輩子也別想甩掉我,將來還會和我葬在一起,到陰間當對死鬼夫婦。” 不想這樣的話,現在立刻馬上,醒過來。 昏迷不醒的明芙,手指動了動。 沈縱見她有了反應:“如果你敢死,我不止和你葬在一起,下輩子還娶你,死也不跟你和離,生生世世都纏着你,害怕嗎?” 怕就給我起來! * 明芙失憶昏迷,意識模糊之際,有個聲音斷斷續續傳來,他說—— 死也要和她葬在一起,要和她做一對鬼夫妻。 下輩子要娶她。 生生世世都要纏着她。 …… 明芙被沈縱的“肉麻深情”所感動,醒了過來,盯着他的俊臉,羞澀道:“我們不要做鬼夫妻,也不要等下輩子,這輩子阿芙就和郎君恩愛到白頭。” 沈縱:??! 得知明芙失憶並且誤聽了他的話,沈縱忙解釋:“你誤會了,其實我們……” 明芙上前在他脣上甜甜地蓋了個章:“我們什麼?” 沈縱:“我們……很好。” 曾是怨偶的兩人,陰差陽錯甜蜜地生活在了一起,成了恩愛夫妻。直到某天明芙想起了一切,氣鼓鼓地大罵沈縱:“臭不要臉,大騙子!” 沈縱理直氣壯:“是你先說喜歡我的。” 【小劇場】 若干年後,小包子眨着圓滾滾的大眼睛,撲進明芙懷裏:“阿孃,窩要舉報給你一個關於爹爹的祕密!” “你每次睡午覺,他都會跑來偷親你。”
17.9萬字8 864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