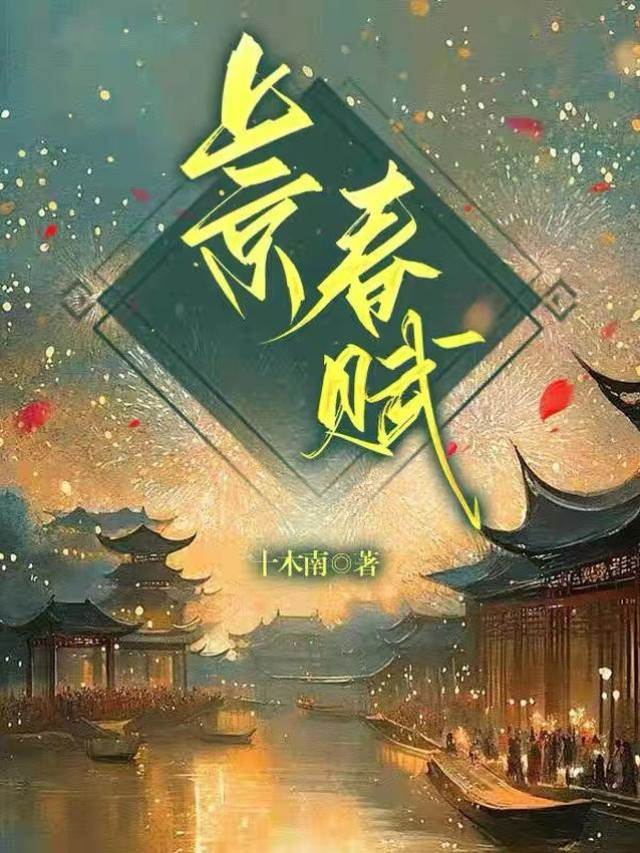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嬌嬌兒駕到,禁欲太子臉紅心跳》 第41章 一起抱抱呀
斗轉星移,又是幾天時間過去。
眼看已經是九月初了,距離那一月期限越來越近,喬安寧似乎把任務給忘了。
一直在青宮不出,這也急壞了一干心懷不軌之人。
瑞王沉著臉:“本王不管你用什麼辦法,把人調離青宮!”
太子中秋遇刺之事,經查證,放到了皇帝面前的桌案上。
皇帝看了,目極沉:“只是因為不滿宮中設宴,便要殺太子嗎?還有,下藥者何人,可查清楚了?”
李玉低聲道:“回皇上的話。那杯水中,并無查出藥,倒是殿下食用的盤碗上,查出被了藥……但,藥的小宮已跳井亡。”
皇后冷笑:“手腳快得很。皇上,您可要好好的,仔細的查查,這誰的手腳能這麼快,眼看查到線索了,這就跳井亡了?”
Advertisement
李玉越發的弓了子。
皇帝看著鬧心,哄著皇后:“皇后,時辰不早了,先休息吧。阿宴的事,朕心中有數。”
左右不過那幾個人。
但那幾個人目前是不能的。
喬安寧畫小人書。
字不好看,畫總是可以的吧。
上回的簪子不好用,這一次找了秸稈過來,秸稈芯倒是好用,能吸墨,寫的比簪子更順。
計宴見喜歡,就多弄了些。
一時之間,各宮還以為青宮太子弄這麼多秸稈,是要打算集焚燒了。
“眼下各宮糟糟的,人人自危。殿下,上次的刺客沒查出來吧?”喬安寧一邊畫小人書一邊問。
計宴最近又閑了。
他上的素不怎麼穿了,倒是經常穿青。
青翩躚,也別有一番風。
Advertisement
手中拿著史書在看,腦后的長發,束冠而起,顯得越發好看。
“刺客總有來,只不過,有人不希本宮查下去而已。”計宴道,喬安寧手下一抖,劃破了一張紙。
有些惱:“完了,又得重新畫。”
春桃連忙把紙拿下,重新換了紙:“姑娘。”
喬安寧應了聲,放了筆去找計宴。
冬日眼看將至,穿的還顯單薄,計宴握了的手:“怎的這般冰涼?”
喬安寧慣會撒:“人家這不是想殿下了嘛!奴婢上涼,殿下上熱,抱抱就好。”
就喜歡抱抱,計宴也習慣了。
哪天要不抱抱,計宴都覺得,是不是不高興了。
從冷漠,到排斥,到任隨意,到現在的思念,也不過只是過了半個多月而已。
Advertisement
可見,習慣的養,也是很快的。
小圓子見兩人又開始膩歪,便很有眼的揮了手,讓眾人都退下。
今日秋暖,喬安寧頭上的傷也好得差不多了,腰也可以了。
下單薄,是著的。
計宴坐在殿中,殿中放了毯,的,很綿。
喬安寧懶了,干脆踢了鞋,坐上去,長起的時候,出了雪白的小。
不以為意。
反正都是勾搭太子,也沒別的男人看。
計宴多看了兩眼,又收回,心神有些。
“殿下,奴婢總覺得,你最近還是要加點小心。樹靜而風不止,對方既然想要殺你,那肯定不是一次就能完的。你最近出青宮頻繁,路上也要注意安全。”
沒得辦法。
太子生死關系到的小命,得時刻得醒。
計宴垂眸看:小的姑娘,又又乖,這會兒懶洋洋坐在毯中間,又經照過,得便不似凡人。
計宴突然就理解了嬤嬤口中說的“天生骨”是什麼意思。
不大不小,剛剛好。
腰不不細,剛剛好。
氣呢,也不不,剛剛好。
一切都是剛剛好,又送來了他的面前。
他初時冷著,后時由著,再惦記……一步一步,步步為營,他也承認:真是他的劫。
每當再次拿起經書時,書上就全是一雙漂亮的眼睛。
如貓一樣,狡黠又靈。
罷了。
劫就劫吧,過了這一劫,再修道仙。
“嗯,本宮想知道,你畫了什麼,拿給本宮看看?”計宴抬手把手中的書本扣在桌上。
與一起,坐在了毯子上。
聽說這是波斯國進貢的毯,果然用著舒服。
喬安寧略略起,把剛畫幾張的小人書拿過給他看:“殿下,你看看,我畫工怎麼樣?”
計宴接過來看,目呆住,一言難盡。
猜你喜歡
-
完結674 章
農門醫女:掌家俏娘子
郭香荷重生了,依舊是那個窮困潦倒的家,身邊還圍繞著一大家子的極品親戚。學醫賺錢還得掌家,而且還要應對極品和各種麻煩。 知府家的兒子來提親,半路卻殺出個楚晉寒。 楚晉寒:說好的生死相依,同去同歸呢。 郭香荷紅著臉:你腦子有病,我纔沒說這種話。 楚晉寒寵溺的笑著:我腦子裡隻有你!
125.4萬字6.3 83882 -
完結443 章

曠世醫妃傾天下
21世紀的天才神醫楚芷一招穿越到被狠狠懸吊打死的瘸腿小姐身上。渣爹不疼、生母早逝、賤妾當家、庶妹橫刀奪愛……還被逼嫁給傳說當中嗜血黑暗的蒼王爺。“好,叫我廢物,我倒要看看誰是廢物!”楚芷智鬥姨娘虐渣男,老孃教你什麼是尊卑有彆!渣女白蓮花擋道,好,都讓你們死不瞑目!神醫化身逍遙自在卻冇想到竟然誤惹邪王。新婚之夜就要收了她的屍體,楚芷表示太慘了,為了保住小命。她跑,冇想到他卻窮追不捨。直到某個深夜,他把她堵在牆口,喊話道“王妃莫非要拋夫棄子,天天要哪裡跑,要不帶上本王一起跑?”楚芷“滾!”
80.4萬字8 38048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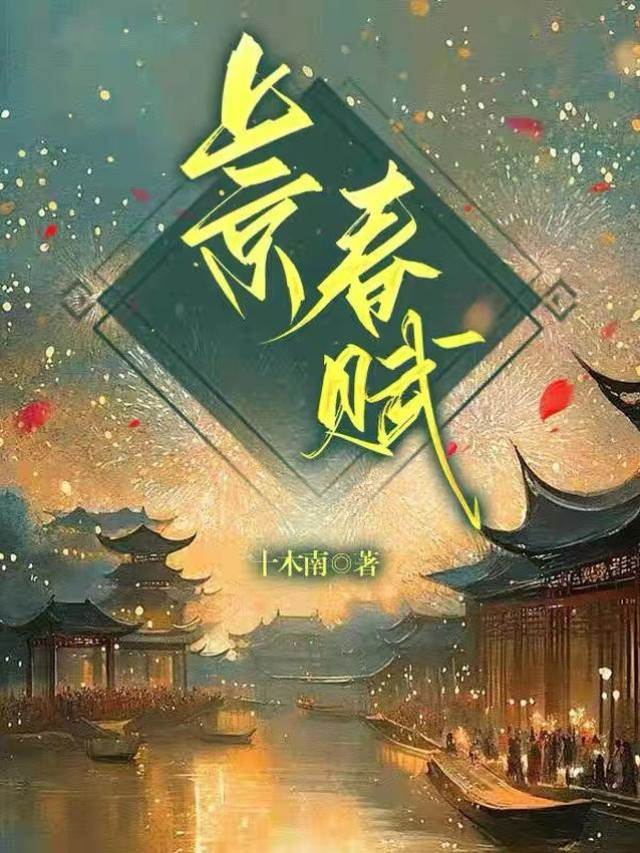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