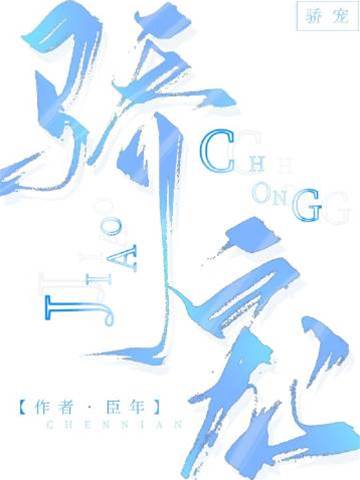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甜欲!閃婚後被閨蜜小叔寵溺入懷》 番外23樊亦星?庫楠
樊亦星拿筷子的手停住,自從養了南南後,他就不吃狗了。
說起南南,每天他回家南南都會撲騰小短跑到門口迎接,今天怎麽……
他視線再次落在沸騰的火鍋上,想到什麽,臉倏然大變,猛地看向庫楠:“你把南南怎麽了?”
庫楠挑眉:“你說呢?”
“說!”
這一聲太暴戾,把庫楠震了下,對上樊亦星要把他頭按進沸騰火鍋裏的眼神,桃花眼一斂,有點吃味,聲音也拔高了些:
“我能把它怎麽樣,在家好吃好喝伺候著,我爸媽我都沒這麽盡心伺候過!”
像是聽到有人提到它,臺上麵壁思過的可憐小狗吧噠吧噠就跑來了:“汪!”
樊亦星聽到南南的聲神一鬆,彎腰把小家夥提起來放到上,了小狗頭:“嚇死我了,今天怎麽沒到門口接我?”
“……”
南南是不會說人話,不然它一定要把庫楠“狗”的惡劣行徑痛訴一天一夜!
它可憐地往樊亦星懷裏拱,希主人能明白它的悲慘心,但終究吃了不會說人話的虧,樊亦星隻當小家夥在撒。
反而庫楠開口了,他抱著臂,冷冷看著對麵親的一人一狗:“別隻顧著狗,你剛什麽意思,你以為我把南南宰了?”
你沒想過嗎?
南南幽怨地看過去,又快速把眼珠別回來,慫得一批。
“這條狗,我下午給他洗了澡,剪了指甲,還給他講故事帶它玩。”庫楠繃著臉,“就這麽好心好意對你的狗,到頭來換你滿心揣測,我他媽圖什麽!”
“……”
南南狗眼瞪大。
澡是洗了,但公報私仇拿花灑噴它,還笑它醜,一口一個土狗,什麽土狗,明明是中華田園犬好吧。
指甲也剪了,但剪出來有多難看它都懶得說,它牙啃都比他剪得好。
Advertisement
故事就更不要說了,所謂的講故事就是拿火腸吊在它眼前,又不準它吃,它隻能眼地看著饞著,並聽他長達半個小時的家長教育。
他沒一個字是真的,家人們誰懂啊!
然,樊亦星卻信了,麵上掠過一不自然,拍了拍南南的屁讓它下去,清咳一聲:“那個……對不起,誤會你了。”
庫楠依舊繃著臉:“沒有實質的道歉跟放屁沒區別。”
南南狗臉麻木,它就知道,一個男人打你的住所,肯定沒安好心。
果然,樊亦星抬眸看他:“你要什麽實質?”
太過分的樊亦星不會同意,庫楠深知這一點,所以沒太過分:“看在你誠心道歉的份上,我大人大量,讓我在你這住一個星期,這事就算了。”
“不行。”樊亦星想也不想地拒絕。
“五天。”庫楠作出讓步。
“不行。”
“三天。”
“說了不行。”
庫楠著嫋嫋白煙後的那張臉,咬了咬牙,退到底線:“一天,就今晚!”
樊亦星子往後靠,指節彎曲敲了敲桌麵:“說好的,發生關係不扯其他,不要壞規矩,而且你自己說的,吃完火鍋就走。”
渣味十足的發言,直接讓庫楠沉了臉。
“樊亦星,你就這麽怕跟老子扯上關係?我是醜啊還是怎麽,有這麽拿不出手?”
燈自頭頂落下,樊亦星垂眸,眼下覆上一抹影。
恰恰相反,庫楠不是拿不出手,而是太拿得出手。
有些好的東西,不要妄想,一旦妄想就會上癮,上癮是毒,染上毒再戒跟筋剝皮沒區別。
他也是在投過一段心俱傷的後,才明白這個刻骨道理。
沒妄想,便不會傷。
見他不說話,庫楠更氣:“你總說玩玩而已,我想問你,你見過圈裏和誰一玩就玩大半年,他媽的有這時間,京北能睡半個gay圈了!”
Advertisement
“你去睡,沒人攔你。”
樊亦星眉目冷淡,除了渣更多的是抗拒漠然:“想換炮友隨便,又沒規定一輩子就睡我一個。”
“好,你說的!”
庫楠氣得口起伏,他從國外玩到國,向來隻有別人他的份,從沒像現在這樣,從人到狗,他媽的誰誰,他不玩了!
椅子地麵發出刺耳聲響,庫楠沒再說一句話,黑著臉換鞋,摔門離開。
空氣中的香味越來越濃鬱,沸騰的火鍋在安靜的客廳顯得尤其熱鬧,襯得餐桌旁的人就尤其孤單。
樊亦星坐在那,聞著麻辣牛油的香味,很明顯,庫楠騙他的,本不是狗火鍋,但有什麽關係呢,不重要了。
他拿筷子把牛卷全下進鍋,了夾出幾筷子,不過兩口便吃不下了。
火鍋這東西,一個人吃真他媽可憐。
他關了火鍋,神依舊很淡,卻著落寞憂傷。
起回臥室,關門聲響起。
南南看看大門,又看看臥室門,小小的狗眼睛裏充滿大大的疑。
搞不懂,真的搞不懂。
有什麽不能吃完火鍋再吵呢?
-
庫楠不想回家,樊亦星沒在他家留過宿,但他的痕跡卻無不在。
他用過的巾,喝過水的杯子,穿過的拖鞋,枕過的枕頭……
有他的痕跡,卻又像假的一樣,痕跡淡得看不見,可笑。
兜轉到常去的一家酒吧,準確地說是沒和樊亦星搞在一起前常去的酒吧,兩人在一起後,基本晚上的娛樂活就是上床上床,還是上床。
真像樊亦星說的那樣,除了打炮,他們之間毫無瓜葛。
點了酒,在吧臺前坐下,一杯龍舌蘭下肚,眼都沒眨。
調酒師都看呆了,龍舌蘭這玩意兒還能一口悶?
酒一杯杯上,庫楠一杯杯地灌,灌得調酒師都心驚跳,生怕猝死在酒吧找他麻煩。
Advertisement
好在庫楠的酒量不是蓋的,沒猝死也沒爛醉,隻是眼神有些迷離,像醉不像醉。
一隻冷白修長的手搭到他肩上,庫楠頭都沒抬:“不約。”
那隻手沒撤離,反而得寸進尺地往他脖頸去,指尖挲了下他下頜線的。
“我說了不約,你他媽耳朵有問題?”
庫楠喝了酒,酒勁上頭,來了幾波想搭訕的人都被他惡氣趕走,這人不識趣的作更是惹惱他。
那人卻不在意被罵,反而輕笑出聲,嗓音溫潤:“原來我們庫大設計師也有為買醉的這天。”
聲音聽著耳,庫楠瞇眸看去:“是你。”
季逾白收回手,好笑看他:“覺有點失啊,不然你想是誰?”
想有什麽用,他又不會來。
庫楠又灌一口酒,轉移話題:“你也來喝酒?”
“來找我哥,這是我哥的酒吧。”
“還沒跟你哥掰扯清楚?”庫楠斜睨他一眼:“你小子可以啊,玩骨科。”
季逾白麵一僵:“他又不是我親哥。”
“知道是領養,但總歸在一個戶口本上。”
庫楠一頓,想起自己都一團糟,還評判起別人的事了,不自嘲笑道:“別說這些了,難得上,來喝一個。”
季逾白過來撲了個空,也鬱結著,便同庫楠喝起了酒。
不知喝了多,也不知喝了多久,喝到後麵,兩人淚眼汪汪大罵渣男,就差抱頭痛哭了。
這一幕,恰好被好事者拍了下來。
庫楠和樊亦星,兩個極品,在0多1的圈裏,不知惹多人垂涎。
兩人剛膩乎上那會兒,被小0撞見,那覺天崩了似的,忙不迭把消息傳了出去,惹得圈裏一片哀嚎。
有人好奇,最後兩人誰妥協,誰上了位。
討論來討論去沒個結果,更猜不出是真心真意還是一時玩個新鮮。
直到後來沒怎麽見人出來玩,便知道,可能來真的。
誰知今天酒吧又撞見,庫楠和其他男人靠在一起,那距離,覺再近幾公分就親上了。
樊亦星不知道圈裏因為幾張照片又掀起八卦的浪,那些照片轉了個圈,最後還是發到他這來了。
一個關係還不錯的朋友,好奇地問:“分手?還是吃?”
樊亦星彼時洗完澡坐在床邊,手指來回那幾張照片,眸子微沉。
“想換炮友隨便,沒規定一輩子就睡我一個。”
他自己說的話,接著是庫楠那句賭氣的話:“好,你說的!”
頭發上的水沒很幹,發尾嗒嗒滴著水,落在的肩上,劃下一道水痕。
樊亦星坐了很久,直到頭發都不再滴水,他才扔了手裏的巾把照片轉手發給庫楠。
沒指他回,指不定這會兒春宵一刻呢。
誰知,庫楠回了信息,還回得很快。
就兩個字:【渣男!】
樊亦星覺得好笑,摔門走的是他,去酒吧和其他男人摟摟抱抱的人也是他,到頭來罵他渣男。
樊亦星不是不講道理的人,也不會為了幾張照片就斷定什麽。
他問:【照片怎麽回事,那人跟你什麽關係?】
庫楠:【不是你說的隨便換炮友,你管我!】
樊亦星皺了皺眉,一時分辨不出他是酒後氣話還是真心話。
樊亦星:【你要是醉了我當沒看見這句話,我是說可以隨便換炮友,但是換的話我們就沒必要繼續,我不可能跟人同用一個人。】
這次回的是語音,樊亦星點開,庫楠清醒的、低磁的嗓音回在房間:
“樊亦星,你真把自己當個寶了?你自己說玩玩而已,現在又說換炮友就不繼續,不三不四的關係還要求一心一意,是不是被C傻了?”
他的語氣不像賭氣,而是認真的,帶著某種戲謔的嘲諷,像綿的針,一下刺了過來,躲閃不及。
樊亦星拿著手機,突然胃裏一陣翻滾,他衝到浴室,對著馬桶幹嘔了好幾下,卻什麽都沒嘔出來。
他扶著洗手臺邊緣站起,看到鏡中的臉,蒼白得可怕,像要噶了一樣。
許久,他打開水龍頭,掬了幾捧水洗臉,再抬頭,臉好了些。
他衝鏡中的自己扯了扯,回到房間。
手機扔在床上,他拿起來,把庫楠微信帶電話拖進黑名單,抬眼見深藍大床,白天沒怎麽收拾,床單的褶皺還在,昭告著昨晚發生過的激烈事。
他利落地換下四件套,沒放進洗機裏,而是扔進了垃圾桶。
嫌在垃圾桶裏礙眼,他凝視片刻,又彎腰把垃圾袋捆好,扔去門外。
-
庫楠不記得怎麽回的家,反正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中午。
他埋在樊亦星慣睡的枕頭上,深吸了口氣,才後知後覺,他和樊亦星吵架了。
他坐起來,了宿醉的頭,到手機發現關機了,充電的間隙,去浴室洗漱。
等他出來,手機已經開機,他第一時間找到樊亦星的微信,看到信息的時候,眉心猛地一跳。
跳的是照片,也是樊亦星回的那兩句話。
最後一條是他自己的語音,他點開來,然後,他就會到了什麽,不作就不會死。
在床邊冷靜了兩分鍾,又了煙加強冷靜五分鍾後,他端正坐好,打算以真誠的態度解釋下昨晚的事。
包括那條混蛋十足的語音。
他清了清嗓子,刻意用宿醉醒來的氣泡音對著手機說:“阿星,昨晚那個是普通朋友,我們沒任何關係,你不要誤會。至於後來的話,我喝醉了,都是我瞎說的,你別往心裏去。”
犯錯了不要,隻要認錯態度良好,問題不大。
庫楠自我覺良好地把手機從邊移開,低頭就看見無比刺眼的一行字:
【消息已發出,但被對方拒收了】
黑名單?
庫楠皺眉,又撥電話過去,毫無疑問,也打不通,拉黑了。
庫楠怔住,隨即一氣湧上來。
很明顯樊亦星翻臉了,不知因為照片還是因為他的混話,但怎麽說,至當麵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吧,就這樣無把他拖進黑名單,把他當什麽了?
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玩?
甚至連“分手”兩個字都不屑於給的玩。
哦,對了,他們都沒在一起過,何來分手?
真他媽的可笑。
惱怒和挫敗在心口織,誰還沒點脾氣了,誰又缺了誰活不了!
真心累了。
他倏然發笑,笑得又眼眶發紅,最後把樊亦星的電話和微信拖進黑名單,扔了手機倒在床上,久久沒有彈。
猜你喜歡
-
完結620 章
暖婚蜜愛:軍官寵上癮
向暖從小爹不疼娘不愛,所以也不敢奢望幸福,直到她遇上牧野。
143.8萬字7.86 774556 -
連載229 章

穿成影帝的炮灰前妻
楊千千是娛樂圈著名經紀人,她工作非常努力,最後她過勞死了。 然後她發現自己穿成了書裡和自己同名的一個炮灰,男主的契約前妻。 書裡原主因為不想離婚而下藥男主,然後原主懷孕,她以孩子為籌碼想要得到男主的感情,可是最後被男主以虐待兒童送進了監獄,最後也死在了監獄。 現在楊千千來了,對於男主她表示:對不起,我不感興趣。 楊千千穿書後的想法就是,好好工作,好好帶娃,至於孩子爹……親爹沒有那就找後爸!!! 某影帝:後爸?不可能的,這輩子你都別想了,這親爹他兒子要定了!!!
21.1萬字8 19266 -
連載1496 章
盛寵嬌妻:傅少,別上癮
「這姿勢怎麼演?」「躺著,我教你。」拍一場替身戲,沈未晞成了令人聞風喪膽的傅家掌權者→傅錦寒的女人。被最親最信任的人背叛又遭遇失身,她決定綻放實力活出自我,一心虐渣追尋夢想,並杜絕男人,然而傅錦寒強勢闖入她的生活。從此,沈未晞身軟腿軟心也暖,渣渣虐得爽翻天,愛情事業雙豐收。某天,傅錦寒求婚,沈未晞笑得像個小妖精:「沈影後的聘禮很貴喲。」傅錦寒給她戴上獨一無二的鑽戒:「我就是聘禮!」沈未晞:「這輩子,你都不許後悔!」傅錦寒摁住了她:「人、心、傅家、影視圈都是你的。現在就造個寶寶,五重保險。」【雙C,1V1,HE,甜寵】
215.5萬字8 17413 -
完結60 章

上心
他會把他清理干凈,變回曾經漂亮的樣子 現代架空,背景男男婚姻合法。 ===== 郁松年看著沈恕,苦笑道:“結婚還是得和喜歡的人結吧。” 沈恕:“沒想到你這麼浪漫主義,我們圈的人不都是商業聯姻嗎?” “如果你實在很擔心,可以先簽合同,確認年限,到時好聚好散。” 他把這當作一場買賣。 而實際上,沈恕覺得自己是撿回一條臟兮兮的小狗,他會把他清理干凈,變回曾經漂漂亮亮的樣子。 ==== 年下 先婚后愛(?) 沈恕(受)x郁松年(攻) HE 先婚后愛
15.7萬字8 5645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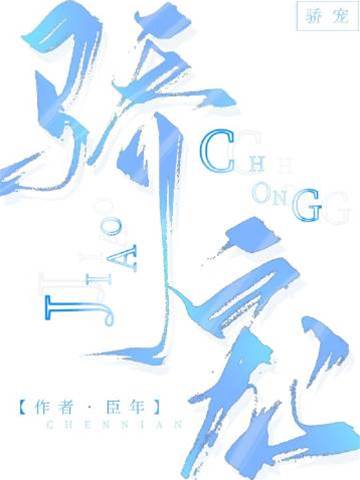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303 章

江少的小祖宗戰鬥力爆表
阮陽打架很厲害 六歲,同學嘲笑她沒媽媽 她就一拳一拳掄過去,同學進了醫院,她進了警局 十二歲,柔道館的人嫌她弱,敗壞門風 她就一個一個挑戰,掀翻了整個柔道館。 十八歲,校霸找茬 她一個放倒八個 直到有一天,江修嶼成了她的監護人—— “這些雜碎弱不禁風,哪用得著阮阮動手” 從此,修羅放下了屠刀 順帶著拿起了五年高考三年模擬 啊,要高考 …… 江修嶼對阮陽 六年前一見鐘情 六年後,是蓄謀已久 他一直以為小姑孃的心挺難捂熱 卻不知道 某個空白的角落,早就已經填滿了細碎的光芒 於是,在江修嶼告白的時候 阮陽挑著他的下巴 又撩又野,“二爺,你先動的心,可是,是我先動的嘴。” 說完,在他唇上啄了一口 【戰鬥力爆表又野又颯阮小姐】×【蓄謀已久極致偏寵江二爺】
51.5萬字8 5108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