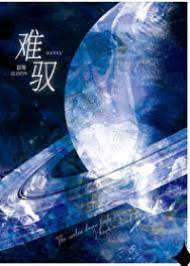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他等我分手很久了》 第73頁
他的膛堅寬闊,與的細膩撞,磨礪出人的花火,在無聲的黑夜里滋生。
陳瑜清也注意到了這樣的力,他很快垂下手臂,盡量減與的接面積。
可睡著了也不安分,在他松手的同時,的勾上他勁窄的腰,整個人樹袋熊一樣吊掛在他脖子上。他寬松的領被蹭垮一截,出清晰的鎖骨線。
陳瑜清抱著莊斐往臥室里走,腳步很沉。
呼吸很重。
這樣的莊斐真要命。
可說,好困。為了讓繼續睡覺,他只能獨自去熬過這漫漫長夜。
他走進的臥室里,弓彎腰,將平放在松的床墊上,他面無表地拽著被子替蓋上,連同腦袋一塊兒全都遮住,像他自己睡覺那樣。
莊斐眼前一片黑。
陳瑜清不發一言地往外走,走兩步想起來,大學室友曾經說過他這種蒙著腦袋睡覺的睡眠方式很怪異。
從前,他不以為意,但……
他原路返回,把莊斐的腦袋從被子里撥出來,條紋被角在頸下,像一只慵懶的貓。
Advertisement
莊斐很漂亮,是那種張揚而明的好,哪怕睡著了,仍掩蓋不了的芒。
他的結上下滾了下,仍對如今已是他朋友這件事覺到不真實。
莊斐仍困得睜不開眼,但這會兒有些意識了,抬起手臂準地抓握住他的手指:“你別回去睡了。”
陳瑜清怔了良久:“那我去外面睡。”
他聲音低啞致命卻又不解風,莊斐有點不高興,呼呼嘟囔一句:“我的床上是有釘子會扎你嗎?”
“沒有。”
命不可違。
陳瑜清坐在床邊作緩慢地掉外套和長,他掀開被子,在床的左側邊躺好。
床不小,他控制住自己沒有著。
但他睡不著。
他沒有辦法和躺在同一張床上,卻什麼都不做,而是沒心沒肺地睡覺。
另外,的窗簾沒有完全拉合,有月穿過窗臺,和也刺目,客廳里的音樂聲低迷卻也煩人。
這些都注定他一夜睜眼到天明。
凌晨三點,莊斐因為口醒過來喝水。意外發現自己旁躺了一道黑影,先是愣了一下,隨后便想起來,昨晚上睡得迷迷糊糊,好像是對他發出了邀請。
Advertisement
怎麼對他說的來著?
【你別回去了。】
【我的床上是有釘子會扎你嗎?】
這怎麼回憶都是一種威利。莊斐放松的神經一下子繃起來,水也不敢喝了。繼續保持剛才的姿勢,一不地裝睡。
但這微小的幅度仍是引起了陳瑜清的關注,他的聲音似乎有一些抱怨:“莊斐,我睡不著。”
是了,這換誰能睡著啊?
莊斐知道了他就躺在邊,也睡不著啊。
但出于愧疚,莊斐還是大方地出了自己的一條手臂:“那……你要不要枕著我睡?”
陳瑜清偏過腦袋看一眼,眼里毫不掩飾他的不可思議與震驚,好像再明晃晃地質問,枕著你我就能睡著了?我睡不著是因為我自己沒有手臂可枕嗎?
理是這麼個理。
莊斐訕笑,收回手臂。卻在回之際,他往這邊挪了挪,腦袋自然地抬起,將的手臂在茸茸的腦袋下。
但他不是那種沉沉的住,準確地說,的手臂只是墊在他的后頸下,在一小截空心拱起的弧度,所以也就不到外界的沉重與力。
Advertisement
那麼,沉重與力都來自哪里?
來自自己心深的那些不安分與蠢蠢。
“能睡著了嗎?”過了一會兒,莊斐心懷鬼胎地問。
陳瑜清誠實地搖了搖頭:“我不能。”
莊斐所需要的睡眠時間在六個小時左右,這會兒雖然只睡到三個小時,但已經睡得清醒了。睡醒了,那麼不繼續睡也沒關系了。
但……陳瑜清他一夜沒睡呢,就人好生心。
莊斐側過,抬起另一條手臂,的手掌一下接在下地拍在他腦袋上,似做安。
“現在呢?”
的力道綿綿的,像貓爪輕輕摁頭。
撓得他心中愈發的覺到意。
“更不能了。”
“……”莊斐耐著子:“要不,聊點兒什麼?”
“嗯。”
“聊什麼呢?”
“隨便。”
接下來,便是一陣沉默。
其實這段時間和陳瑜清相下來,莊斐發現跟他聊天也不是很困難,他雖然話不多,但只要開口問了,他就會回答,并不會像從前那樣置于尷尬的境地,可能這就是為他朋友的優待吧。
問什麼答什麼。
只要能找出話題來聊……
但現在他們倆躺在一張床上,莊斐腦子里面也是空空的,聊什麼都覺得不對,說什麼都覺得不合適……
被迫沉默。
空氣里有什麼正在沉默中快速發酵,床上的溫度不知不覺地攀高,兩個人都開始心不在焉。
醞釀與較量之下。
“莊斐。”
這一次是陳瑜清先開口。
“嗯。”
“和昨天晚上相比”,他側過和面對面,“你現在還困嗎?”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870 章

大佬的大佬甜妻
一次意外,她救下帝國大佬,大佬非要以身相許娶她。 眾人紛紛嘲諷:就這種鄉下來的土包子也配得上夜少?什麼?又土又丑又沒用?她反手一個大……驚世美貌、無數馬甲漸漸暴露。 慕夏隱藏身份回國,只為查清母親去世真相。 當馬甲一個個被扒,眾人驚覺:原來大佬的老婆才是真正的大佬!
169.3萬字8.33 11991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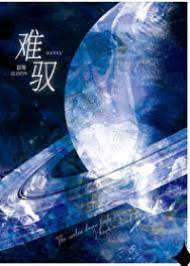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879 章

閃婚秘寵:首富大佬愛妻入骨!
為了擺脫原生家庭,她與陌生男人一紙協議閃婚了!婚后男人要同居,她說,“我們說好了各過各的。” 男人要豪車接送她,她說,“坐你車我暈車。” 面對她拒絕他一億拍來的珠寶,男人終于怒了,“不值什麼錢,看得順眼留著,不順眼去賣了!” 原以為這場婚姻各取所需,他有需要,她回應;她有麻煩,他第一時間出手,其余時間互不干涉…… 直到媒體采訪某個從未露過面的世界首富,“……聽聞封先生妻子出身不高?”鏡頭前的男人表示,“所以大家不要欺負她,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些千金富太太渣渣們看著他驚艷名流圈的老婆,一個個流淚控訴:封大首富,到底誰欺負誰啊!
163.7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