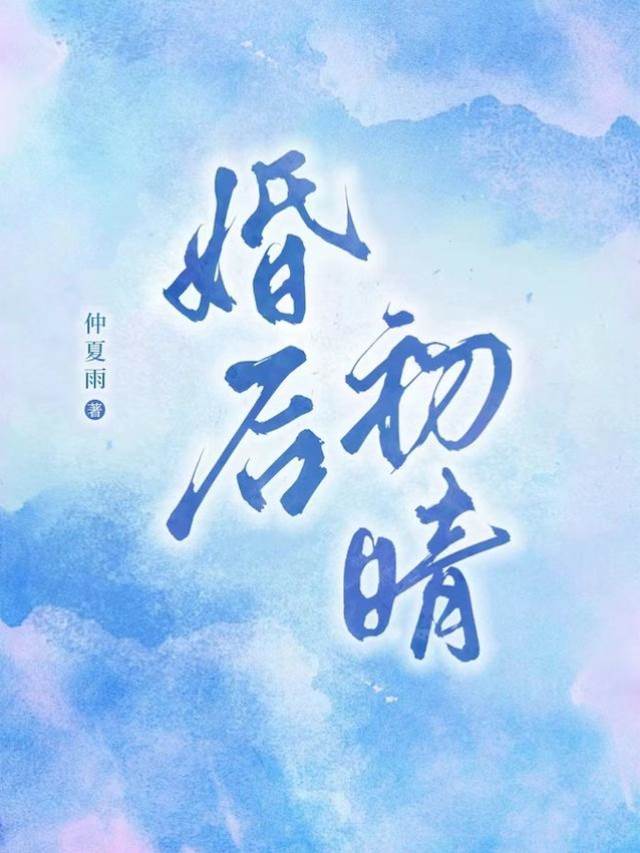《霍教授上癮后,溫小姐不撩了》 90. 他想陪著她
溫黎那些年待在國外,沒見飛車黨搶劫,甚至還見過被飛車黨捅得腸子都流出來,還被拖在托車后面拖行了幾百米的無辜路人。
一邊后悔怎麼就沒把包拱手送出去,一邊絕地閉上了眼睛。
預料中的疼痛沒有襲來,落一個堅實的懷抱,摔在地上的時候,霍遠琛甚至都用力把托舉起來,給做了墊。
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那群飛車黨早就看不見蹤跡了。 ?.?????.??
被霍遠琛死死按在懷里,因為得太近,能清楚地聽見他咚咚咚的心跳聲。抬起頭的時候,正好和他四目相對,他眉心皺得很深,又急又快地問“有沒有事?”
溫黎確認上沒有疼痛的地方,才搖搖頭,說“沒,我沒事。”
霍遠琛的臉便沉下來,語氣不太好地問“飛車黨也不怕,那個包,對你很重要?”
溫黎這會兒驚魂未定,狼狽地坐在地上理了理思路,努力向他解釋“包倒不貴,但是里面有我的護照,還有我出國前兌換的現金,數額不。我剛才就是想著這個,才去跟他們搶包的。”
霍遠琛臉更加難看地批評“錢丟了就丟了,你跟著我出來,難道我會讓你流落街頭?護照雖然重要,但跟你的生命相比,不值一提。”
溫黎知道他說的是對的,剛才的事,確實是判斷失誤了。沒跟他吵,只是有點著急,問他”那現在怎麼辦?他們把我的護照搶走,肯定找不回來了。沒了護照,我就沒有份的人,哪里也去不了。別說去找我哥哥,恐怕連回國都是問題。”
霍遠琛見那張臉白得厲害,知道被嚇怕了,也就沒再批評,把從地上拉起來,說“先回酒店再說。”
Advertisement
溫黎這一路上都難的,一想到的護照大概率是找不回來了,就絕地想哭。加上包里那些錢,就更難了。
不知道哥哥到底是因為什麼緣故才失蹤的,但也猜到了,既然哥哥還活著,卻這麼久了都不和家里聯系,說明他現在的境很危險。不管是電子支付還是刷卡,都有暴行蹤的危險,所以早就想好了,如果這次能找到哥哥,不管他愿不愿意跟回去,得先保證哥哥的生命安,再留下錢給他。
能讓他食無憂,也就不虛此行了。包里那些錢,是出國前用剩下的積蓄兌換的,沒想到還沒去找哥哥了,那些錢就便宜了那些該死的飛車黨。
那些渾蛋這會兒一定在邊數錢邊笑吧,笑這個東方白癡人給他們送去了一大筆錢。
可能是這一路上太沉默了,下車的時候,霍遠琛安了一句,說“我已經報警了。警察會理的。”
溫黎很沒神地“嗯”了聲,并不抱多希。知道國外那些警察的水平,尤其是對像這樣無權無勢的東方人,不當著的面奚落嘲笑活該就不錯了,幫找回被搶走的東西?想都不敢想。
閉了閉眼,想起剛到國時目擊到的那個被飛車黨捅傷,把地磚都染紅了的路人,他當時也報了警,可結果呢?警察來了以后,只是例行公事地詢問了兩句,然后一臉無所謂地說“你
太倒霉了。”
覺得這句話也同樣適合。
也太倒霉了。
霍遠琛把送回房間,沒什麼力氣地說了句“你走吧。我一個人可以的。你還有工作,我已經耽誤了你很多時間,不想連累你加班。”
霍遠琛看了看蒼白的臉,抬腳邁進了房間。見還杵在門口不,又返回去,把抱起來,一路抱到了床上。
Advertisement
“我沒有工作要忙,我可以陪你。”他說著,了鞋和外套,鉆進了的被窩。
過程中,一直小心翼翼避開做手的地方。
溫黎這會兒并不想和他親近,手推了他一把“你別騙我了,你每天的事都很多。這幾天在醫院,好幾次我半夜醒來,都看見你抱著電腦,窩在小沙發上加班。”
掌心下服的不太對,似乎有什麼凝固了粘在料纖維里,用指尖扣了扣,一下子臉變了。
再把被子掀開,看到他襯上那已經干涸的一片深紅時,聲音都在發抖“你傷了?被飛車黨的匕首劃傷的?”
霍遠琛也看了一眼,并不是很在意地抬了抬胳膊,輕描淡寫道“就一點皮外傷,你不說,我都沒注意到。”
他半條袖子都紅了,之前有深外套擋著看不出來,這會兒只剩下淺襯了,就格外目驚心。
溫黎才不信這只是皮外傷,鬧著要讓他去醫院。
霍遠琛被吵得沒辦法,只好說“酒店就有急救箱,我自己理下就行,去醫院太小題大做了,我真沒覺得有多疼。”
溫黎不放心,非要看著他清洗包扎,見他傷口真的不深才不再堅持讓他去醫院。
“我又連累你傷了。”有點自責地說,“加上上回你被孟瑾年媽媽燙傷那次,我已經讓你了兩次傷了。”
霍遠琛把摟進懷里,安地拍著的脊背,說“你這胡思想的病可得改改,不利于恢復。”
溫黎還想說什麼,他已經手合上了的眼睛“睡吧,我陪你一起睡。”
可溫黎睡不著。腦子里跟開了火車站一樣,一會兒想哥哥,一會兒又惦記的護照,懊悔怎麼就把護照放在那個包里,沒有帶著了?
Advertisement
最后,還是忍不住去想了那個被飛車黨捅傷的路人。奇怪得很,明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以為都忘干凈了,這會兒卻能清晰地回想起當時的畫面,最后聚焦滿目的腥紅。
止不住抖起來。
霍遠琛覺到了,問“怎麼了?”
溫黎就把國那件事說了。末了,心有余悸地說“我那時候剛去沒多久,就遇上這種事,我被嚇壞了,哭著求我爸媽讓我回國。可我爸媽不肯,非要我留在國,你能想象到我當時有多害怕嗎?”
霍遠琛收了抱著的胳膊,聲哄著,讓快點睡覺。
后來迷迷糊糊將睡未睡的時候,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好像聽見他說了一句。
“要是我那時候陪著你就好了。”"溫黎那些年待在國外,沒見飛車黨搶劫,甚至還見過被飛車黨捅得腸子都流出來,還被拖在托車后面拖行了幾百米的無辜路人。
一邊后悔怎麼就沒把包拱手送出去,一邊絕地閉上了眼睛。
預料中的疼痛沒有襲來,落一個堅實的懷抱,摔在地上的時候,霍遠琛甚至都用力把托舉起來,給做了墊。
從地上爬起來的時候,那群飛車黨早就看不見蹤跡了。
被霍遠琛死死按在懷里,因為得太近,能清楚地聽見他咚咚咚的心跳聲。抬起頭的時候,正好和他四目相對,他眉心皺得很深,又急又快地問“有沒有事?”
溫黎確認上沒有疼痛的地方,才搖搖頭,說“沒,我沒事。”
霍遠琛的臉便沉下來,語氣不太好地問“飛車黨也不怕,那個包,對你很重要?”
溫黎這會兒驚魂未定,狼狽地坐在地上理了理思路,努力向他解釋“包倒不貴,但是里面有我的護照,還有我出國前兌換的現金,數額不。我剛才就是想著這個,才去跟他們搶包的。”
霍遠琛臉更加難看地批評“錢丟了就丟了,你跟著我出來,難道我會讓你流落街頭?護照雖然重要,但跟你的生命相比,不值一提。”
溫黎知道他說的是對的,剛才的事,確實是判斷失誤了。沒跟他吵,只是有點著急,問他”那現在怎麼辦?他們把我的護照搶走,肯定找不回來了。沒了護照,我就沒有份的人,哪里也去不了。別說去找我哥哥,恐怕連回國都是問題。” ?.?????.??
霍遠琛見那張臉白得厲害,知道被嚇怕了,也就沒再批評,把從地上拉起來,說“先回酒店再說。”
溫黎這一路上都難的,一想到的護照大概率是找不回來了,就絕地想哭。加上包里那些錢,就更難了。
不知道哥哥到底是因為什麼緣故才失蹤的,但也猜到了,既然哥哥還活著,卻這麼久了都不和家里聯系,說明他現在的境很危險。不管是電子支付還是刷卡,都有暴行蹤的危險,所以早就想好了,如果這次能找到哥哥,不管他愿不愿意跟回去,得先保證哥哥的生命安,再留下錢給他。
能讓他食無憂,也就不虛此行了。包里那些錢,是出國前用剩下的積蓄兌換的,沒想到還沒去找哥哥了,那些錢就便宜了那些該死的飛車黨。
那些渾蛋這會兒一定在邊數錢邊笑吧,笑這個東方白癡人給他們送去了一大筆錢。
可能是這一路上太沉默了,下車的時候,霍遠琛安了一句,說“我已經報警了。警察會理的。”
溫黎很沒神地“嗯”了聲,并不抱多希。知道國外那些警察的水平,尤其是對像這樣無權無勢的東方人,不當著的面奚落嘲笑活該就不錯了,幫找回被搶走的東西?想都不敢想。
閉了閉眼,想起剛到國時目擊到的那個被飛車黨捅傷,把地磚都染紅了的路人,他當時也報了警,可結果呢?警察來了以后,只是例行公事地詢問了兩句,然后一臉無所謂地說“你
太倒霉了。”
覺得這句話也同樣適合。
也太倒霉了。
霍遠琛把送回房間,沒什麼力氣地說了句“你走吧。我一個人可以的。你還有工作,我已經耽誤了你很多時間,不想連累你加班。”
霍遠琛看了看蒼白的臉,抬腳邁進了房間。見還杵在門口不,又返回去,把抱起來,一路抱到了床上。
“我沒有工作要忙,我可以陪你。”他說著,了鞋和外套,鉆進了的被窩。
過程中,一直小心翼翼避開做手的地方。
溫黎這會兒并不想和他親近,手推了他一把“你別騙我了,你每天的事都很多。這幾天在醫院,好幾次我半夜醒來,都看見你抱著電腦,窩在小沙發上加班。”
掌心下服的不太對,似乎有什麼凝固了粘在料纖維里,用指尖扣了扣,一下子臉變了。
再把被子掀開,看到他襯上那已經干涸的一片深紅時,聲音都在發抖“你傷了?被飛車黨的匕首劃傷的?”
霍遠琛也看了一眼,并不是很在意地抬了抬胳膊,輕描淡寫道“就一點皮外傷,你不說,我都沒注意到。”
他半條袖子都紅了,之前有深外套擋著看不出來,這會兒只剩下淺襯了,就格外目驚心。
溫黎才不信這只是皮外傷,鬧著要讓他去醫院。
霍遠琛被吵得沒辦法,只好說“酒店就有急救箱,我自己理下就行,去醫院太小題大做了,我真沒覺得有多疼。”
溫黎不放心,非要看著他清洗包扎,見他傷口真的不深才不再堅持讓他去醫院。
“我又連累你傷了。”有點自責地說,“加上上回你被孟瑾年媽媽燙傷那次,我已經讓你了兩次傷了。”
霍遠琛把摟進懷里,安地拍著的脊背,說“你這胡思想的病可得改改,不利于恢復。”
溫黎還想說什麼,他已經手合上了的眼睛“睡吧,我陪你一起睡。”
可溫黎睡不著。腦子里跟開了火車站一樣,一會兒想哥哥,一會兒又惦記的護照,懊悔怎麼就把護照放在那個包里,沒有帶著了?
最后,還是忍不住去想了那個被飛車黨捅傷的路人。奇怪得很,明明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以為都忘干凈了,這會兒卻能清晰地回想起當時的畫面,最后聚焦滿目的腥紅。
止不住抖起來。
霍遠琛覺到了,問“怎麼了?”
溫黎就把國那件事說了。末了,心有余悸地說“我那時候剛去沒多久,就遇上這種事,我被嚇壞了,哭著求我爸媽讓我回國。可我爸媽不肯,非要我留在國,你能想象到我當時有多害怕嗎?”
霍遠琛收了抱著的胳膊,聲哄著,讓快點睡覺。
后來迷迷糊糊將睡未睡的時候,也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好像聽見他說了一句。
“要是我那時候陪著你就好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50 章

八零媳婦又甜又颯
【雙潔,一對一,先婚後愛,甜寵爽文】 前世的楚翹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任勞任怨,難產時躺在手術台上,婆婆丈夫繼子都放棄了她,一屍兩命。 回到21歲,還沒嫁給自私狠毒的前夫,但她那後媽想方設法逼她嫁過去謀取利益,楚翹想自立門戶,先得在城裡把戶口上了,可後媽一天天地逼她嫁人,走投無路之際,前夫那個火爆脾氣的親叔叔顧野跳出來求婚了。 “嫁給我,讓那死犢子管你叫嬸兒!” 楚翹心動了,一想到前夫平白矮了自己一輩,在她面前永遠都抬不起頭來,她就莫名地爽,結個婚也無妨啊。 顧野從小就是霸王,對女人愛搭不理,大家都說他這輩子估計是打光棍的命,顧野也這麼覺得,可有一天,他撞到了楚翹,乾涸了二十七年的心,湧出了甜蜜的愛情之泉。 楚翹的每個細胞都長在了他心坎上,是老天爺給他量身打造的媳婦,說什麼都得拐回家,其他男人有多遠滾多遠!
172.6萬字8 77750 -
完結169 章

盛寵之權少放過我
她千不該萬不該就是楚秦的未婚妻,才會招惹到那個令人躲避不及的榮璟。從而引發一系列打擊報復到最后被她吃的死死的故事。
45.5萬字8 11480 -
連載555 章

億萬老公寵妻無度
(書籍暫停更新,站內搜索《億萬老公寵妻無度(蘇瓷沈之衍)》閱讀全篇文章) 蘇瓷被迫嫁給快斷氣的沈二爺,整個S市都等著看她下場凄慘。 然而半年後,蘇瓷治好了沈二爺,被沈家寵上天。 神醫聖手的親傳弟子,頂級黑客,賽車手,火遍全球的葯妝品牌創始人都是她。 跨國集團CEO蕭逸洲、鬼才導演陸銘琛、電競大神anti紛紛站出來:「蘇瓷是我們最疼愛的小師妹」 那個傳聞中陰冷暴戾的男人將蘇瓷堵在牆角,咬牙切齒:「你還有多少我不知道的身份?」 蘇瓷莞爾一笑,吻上男人的唇,「還有最後一個,沈太太」
98.3萬字8.25 342841 -
完結313 章

踹掉渣男閃婚!被神秘老公寵的麵紅耳赤
江若曦愛了付明軒十年,為他犧牲一切,斷絕親情,成為一個人人嘲笑的大舔狗。可他,卻在她被綁架後,不痛不癢的冷嘲一句,“撒謊要有個限度,我很忙,不要再來騷擾我!”後來,江若曦慘遭撕票,死無葬身之地。重生後。她腳踹渣男,手劈白蓮,瀟灑扔出一份離婚協議。卻不料,前夫先生幡然醒悟,玩命追妻。而前世那個疑似殺害她的綁匪頭目,竟秒變瘋狂追求者,一哭二鬧三上吊,隻為做她的最強保護神!付渣:“老婆,求你了,咱們複婚好不好?”夜狗:“你好前輩,不好意思,曦曦是我的!”
28.3萬字8.18 39186 -
完結14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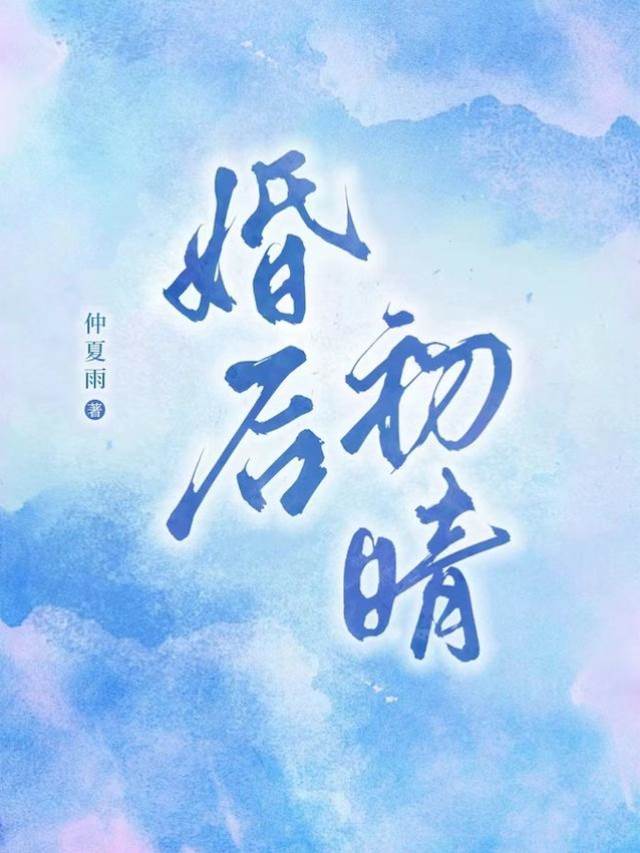
婚後初晴
沈頤喬和周沉是公認的神仙眷侶。在得知沈頤喬的白月光回國那日起,穩重自持的周沉變得坐立難安。朋友打趣,你們恩愛如此有什麽好擔心的?周沉暗自苦笑。他知道沈頤喬當初答應和他結婚,是因為他說:“不如我們試試,我不介意你心裏有他。”
27.2萬字8 4900 -
完結117 章

潮濕天氣
第n次相親失敗後,周尤開始擺爛了。 她在朋友圈大膽開麥:「重金求相親對象,希望對方身高185、身材棒、活兒好,最好有房有車,工作體面……」 本意是吐槽,沒想到這條朋友圈被人截圖轉發給了別人。 周尤沒想到這麼苛刻、變態的要求,竟然有人應了。 她倒是想去看看,對方是何方神聖。 周尤想破腦袋也沒料到她的相親對象竟然是程禮—— 「對方不僅是當年因顏值一炮而紅的理科狀元,還是高考結束那天被她堵在樓梯間強吻的孽緣!」 周尤自覺這場相親怕是以失敗告終,爲了維持體面,她設了個鬧鐘遁走。 男人一眼看穿她的把戲:“你鬧鐘響了。” 周尤羞愧不已,破罐子破摔道:“咱倆不合適……” 男人瞥她兩眼,反問:“哪兒不合適?” 周尤閉眼,“你技術不行。” 程禮沉默兩秒,平靜道:“你別污衊我。” 不久後,周尤反水。 還沒醞釀好說辭,男人便誘哄道:“去民政局,跟我結婚。” — 小劇場: 閃婚沒多久,程禮就開始忙碌,經常出差。 出差去美國期間,周尤剛好完成新作。 跟好友約了去川西自駕,結果因爲某些意外取消了。 周尤閒着無聊,天天在家上網。 某天刷到一條特有意思的彈窗廣告,她像往常一樣隨手發給了好友。 誰知道這次半天沒等到回覆,她點進綠軟查看才發現她誤發給了她的新婚老公! 想要撤退卻已過時效,周尤只好顧左右而言他地發了幾條無聊資訊。 卻不知,男人早已看到這條廣告—— 「女人還是要看這些纔有力氣討生活啊」 廣告內容是各式各樣的肌肉男模,底下還留了聯繫方式,可以說是選妃也不爲過。 遠在美利堅的程禮看完廣告內容,撥通周尤的電話,辛辣發問:“你在家寂寞難耐?” 周尤心虛狡辯:“……我說我是不小心刷到的,你信嗎?” 程禮頭疼,他吸了口氣,在電話裏說:“我明天回國。” 周尤:“你不是要出差半個月?” 程禮:“再不回來要被男模偷家了 — 程禮十八歲生日當天,偷偷寫下了三個目標。 第一,考上北京協和醫學院「臨床八年制」 第二,蠱惑周尤一起去北京讀大學 第三,跟周尤結婚。 第二個計劃失敗後,程禮終於按捺不住,開始攻略第三個目標。
29.8萬字8.09 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