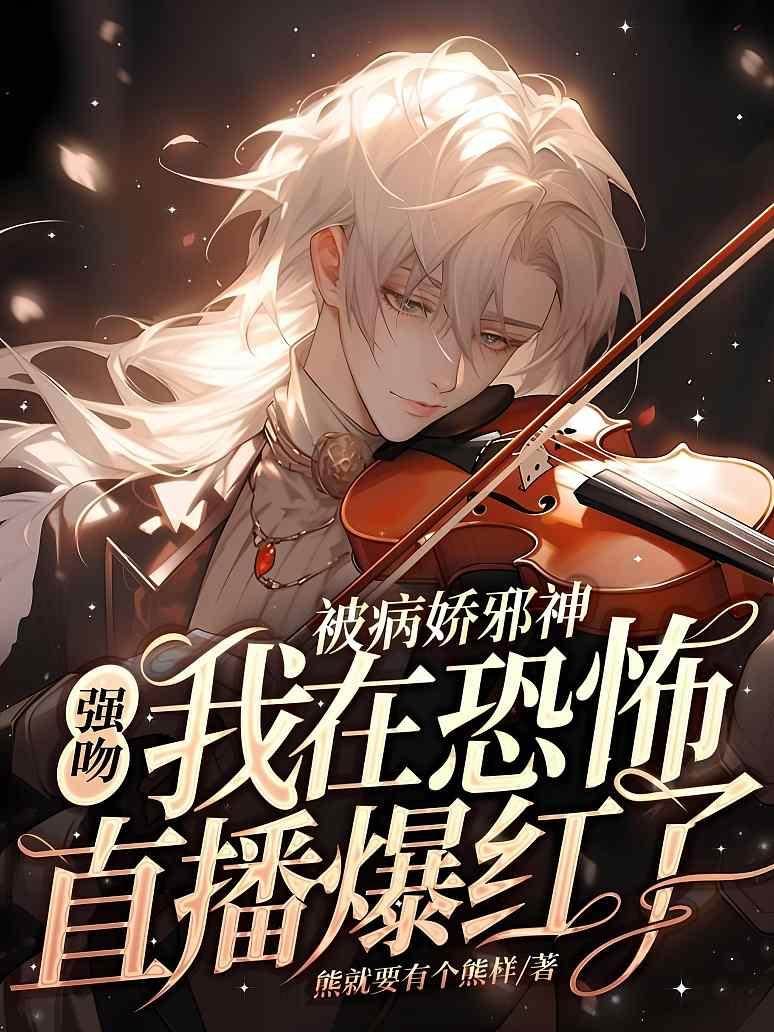《不知星河向你傾》 第69章 別難語(一)
顧平蕪從來沒有天真地以為隻要在池以藍麵前將自己剖開來坦陳一切,就能夠獲得諒解。
可當池以藍麵對的坦誠,角輕抿,出一點弧度時,又疑心自己是否早就得到了寬宥。
始終心存奢。
池以藍沉默了很久,最後輕描淡寫地說了聲“知道了”,算是對解釋的回應。
他沒有說“沒關係”,可麵上又都是毫不放在心上的淡漠。
顧平蕪就沒有辦法再說下去,沉默地笑了笑。
吃完飯後,他們逛了街,看了夜景,還在心齋橋附近拍了傻乎乎的遊客打卡照。
表麵上是普通的日常,可卻有隨時都會一腳踩空的不真實,並沒有放鬆地去過哪怕是一分鍾。
步行回酒店時已經疲憊至極,生理和心理上都已經超出負荷,卻還強撐著不表現出來。
一側是車水馬龍,華燈未央,一側是走時偶爾會到的他的手。
顧平蕪恍惚地想,這到底是什麽走向,哪種劇。
我們明明是在分手。
難道其他人的分手也是這樣子嗎?
可電視劇裏那些撕心裂肺的嚎啕和歇斯底裏的爭吵又是什麽?
想起顧平謙有次分手後約見麵吃飯,整個人都瘦了一圈的樣子,可分明一個月前還見過他。
當時想,分手真是件傷筋骨的事,連三哥這樣在眼裏無所不能的人都栽了跟頭。往後可千萬不要經曆。
Advertisement
那之後的確沒有經曆分手,卻經曆了比分手而言對更殘酷的事。
可今天,真的在麵臨一場分手,一切卻和想象中天差地別。
以至於走著走著習慣地扣住他手腕,接著在他過來的冰涼的眼神裏又驀地鬆開,忍不住站住腳確認:“我們……已經分手了對嗎?”
他以眼神告訴的確如此。接著淡淡反問道:“你確定你搞清楚狀況了?”
很快避開了視線,垂眸道:“搞清楚了。”頓了頓,又說:“抱歉。”
回去酒店,顧平蕪在臥室等了很久很久,都沒有等到池以藍進房。
出去找人,才發現他不知什麽時候已經離開了。
一切落到實,才發現自己本不是原以為的那樣可以從容接。
接不了。
在那場最後的約會裏,一切都太冷靜克製,又太鄭重其事,麵得不似兩個彼此相的人在分手。
控製不住地猜測,他真的過我嗎?有過哪怕一點點嗎?
如果過,怎會毫不表心碎。可如果沒過,他又為何在分別時和同行過夜旖旎的長街,恍如人拖手。
無法不抱著僥幸將這場“分手”隻當做他給予的一次懲罰和警告,於是順從地聽他的話,道歉,接,以為會有所好轉。
可當偌大套房裏空隻剩下一個人,而他連離開都不必再和打一聲招呼的時候,終於明白,原來自己做不到好聚好散。
Advertisement
不願意。
在第十二次撥給池以藍之後,對方終於接通了電話,開口第一句話是:“已經淩晨一點了,顧小姐。”
哽住呼吸,背靠沙發蜷在地毯上,才能克製著心髒的不適,一開口就帶了哭腔。
“池以藍對不起,對不起。”說,“我不想分手。”
像是徒勞經過這一天,什麽都沒記住,此刻才後知後覺反應過來究竟發生什麽的孩子一樣,和他一聲聲道歉,用全然不像的口氣哀求,中心思想隻有一個,不分手好不好。
那頭始終靜靜地聽一再解釋,道歉……直到聲音啞了,再也說不出什麽有用的話,窘迫又絕地停下來,問:“你在聽嗎?”
池以藍靜了很久,才輕笑一聲,帶了嘲諷似的。
“顧平蕪。”他用很沉冷的嗓音喚,說道,“決定已經做了,不能反悔的。”
“那是你的決定!”
攥著手機,極力克製著語調,盡量平靜地接著道:“可我不是殺人放火,難道就不配得到原諒嗎?池以藍,你不能否認我們在意彼此的事實,你還在意我,否則你幹嘛要為了我最初接近你什麽居心而生氣呢,又幹嘛又為了這個就提分手。”
“我有我的原因。”
“我不明白。”抬手撐著額頭,眼底充滿,幾乎是要流淚的樣子,可那一頭看不到,也不知道就算看到的淚,他如今又會不會心疼。
Advertisement
“阿蕪。”他說,“睡吧,一會兒心髒該不舒服了。”
口道:“不要你管,你已經不是我未婚夫了。”可話一出口就已經後悔。
果然,那頭笑了一聲,說:“你知道就好。”就掛了電話。
隔天金伯南和傅西塘要飛去其它國家玩,臨別的聚餐自然不了。
當晚吃壽喜燒。
傅西塘從發現顧平蕪和池以藍是分別到場,就嗅出不對勁,當發現倆人居然沒坐在一邊時,更像是發現了什麽重大新聞一樣很誇張地瞪大眼睛。
“你們……”他來回指著顧平蕪和池以藍,說還休。
池以藍沒吭聲,低頭攪拌生蛋。
顧平蕪拿起杯子喝水,裝作沒聽見。
金伯南竟然打破沉默開了尊口,問池以藍道:“你這幾天都沒住在酒店?”
池以藍頭也不抬,漫不經心“嗯”一聲,接著又用警告的口氣道:“別問了,分了。”
席間一下子氣氛凝滯。
金伯南下意識看向顧平蕪,見臉煞白,從榻榻米上起,極力自然地說道:“我不太舒服,先回酒店。”
池以藍目送出門,隨後吩咐在暗的保鏢把人跟好,安排得細致妥帖,不像是人分手常有的怨懟的樣子。
傅西塘咋舌道:“不是,你這是圖啥呢?”
明明還很關心對方,怎麽就突然分了?難道就因為吃蔣行的飛醋?池以藍已經小心眼到這種程度了嗎?沒道理啊。
似乎看出兩位好友的困,池以藍終於抬眸道:“聽過一句話嗎?”
“世上最骯髒的,莫過於自尊。”
他是池以藍。自尊心大過天的池以藍。
這樣的他,要怎麽才能心平氣和接自己被當作替代品的事實。
他會忍不住複盤過去的每一個細節,思索每一個他曾珍視的時刻,然後無法阻止自己去反反複複地問一個問題:在那個時候,又把我當誰?
當他已經無法篤定相的某一刻心裏的人是自己還是別人,那就是自尊心滾落泥濘裏的至暗時刻。
聶魯達在詩裏寫,為什麽我們花了那麽多時間長大,卻隻是為了分離?
他想,這或許才是長大的本質所在。
猜你喜歡
-
完結123 章

七十年代漂亮女配
別名:七零之漂亮小裁縫 阮溪是一名優秀服裝設計師,不想一覺醒來,她成了一本年代文里的同名女配。原主從小被父母不得已放在鄉下,跟著爺爺奶奶一起生活長大,而女主則是她父親戰友的遺孤,被她父母在軍區親自撫養長大。…
53.7萬字8 17265 -
連載1089 章

權總,夫人的前任們來搶人了!
“可以和我結婚嗎?”“我不要彩禮,不要房子,不要車子,只要一本結婚證!”出獄后的云慕為了阻止爸媽將她嫁給殘疾毀容的權家三少,不惜當街找人結婚。不抱希望的她,卻找到了一個帥氣逼人的老公。老公說,他只是一個普通人。老公還說,愛他沒有結果。云慕恪守他的要求,不動心也就不會心痛。可是漸漸的某個男人卻不安分起來。一場舞會。云慕看了一眼多年的青梅竹馬,驚覺再無從前心動的感覺。可是某人卻醋了一晚上。作為壓軸出場的大佬,他穿越人群,挽住云慕的腰。“愛我,一定會有結果!”
184.8萬字8.18 668944 -
完結574 章

離婚后,總裁天天跪求復婚
霍璟琛不愛沈南歌天下皆知,婚姻生活水深火熱,勢不兩立,直到霍璟琛的心上人死而復生,沈南歌遞上離婚協議書準備離開。霍璟琛將她逼入墻角:“想甩了我,做夢!”后來沈南
52.5萬字8 5822 -
完結128 章

孕吐!嬌氣包被前任小叔圈占誘寵
薑幼晚聲名狼藉,除了那張漂亮臉蛋,一無所有。聽說她不僅勾搭上了頂級豪門的霍家大少,還故意早早懷孕,肚子裏揣了霍家金尊玉貴的小金孫,想要借機上位。一眾人嫉妒得紅了眼睛,掰著手指頭數著她能落下多少好處。可沒多久,圈裏傳來兩人分手的消息,霍大少另尋新歡,薑幼晚慘遭拋棄。慈善晚宴,多少人擠破腦袋等著看薑幼晚的笑話,倨傲的霍大少更是擰眉掃視薑幼晚小腹,一臉被綠後的厭惡。直到某個麵容冷峻的男人將薑幼晚擁進懷中,鳳眸微瞇,壓迫十足。霍大少如遭雷擊,縮著腦袋恭恭敬敬,連大氣也不敢喘,“小、小叔。”他戰戰兢兢,連聲音都在發抖,“我、我不知道她是小嬸,我有眼無珠……”-作為帝都出了名的冷麵閻王,霍臨淵年輕心狠,雷霆手段接掌霍家,撥弄乾坤喜怒無常。沒人覺得薑幼晚這株藤蘿攀附上了大樹,她們隻覺得她不知死活,承受不住那位先生的暴怒。可晚宴間隙,有人看見少女指尖泛粉,緊緊攥著男人衣袖。而那位總是冷著臉的霍先生鳳眸微彎,格外愛憐地啄吻少女的唇瓣。語氣低沉,聲聲繾綣,“寶寶最愛老公嗎?隻愛老公嗎?”“晚晚乖,疼疼老公,再親一口……”-盤踞在深淵的惡龍,終於得到了他覬覦已久的寶珠。
23.7萬字8 11026 -
完結558 章

醫婚
傳聞醫學界翹楚,世家出身的陸家二少高冷,不近女色,至今單身,殊不知他有個隱婚兩年之久的律師妻。你想離婚?”“恩。”“理由。”她噙著抹笑:“根據婚姻法規定分局兩年以上的是可以要求離婚的,這,算不算理由?”
153.6萬字8 8516 -
完結7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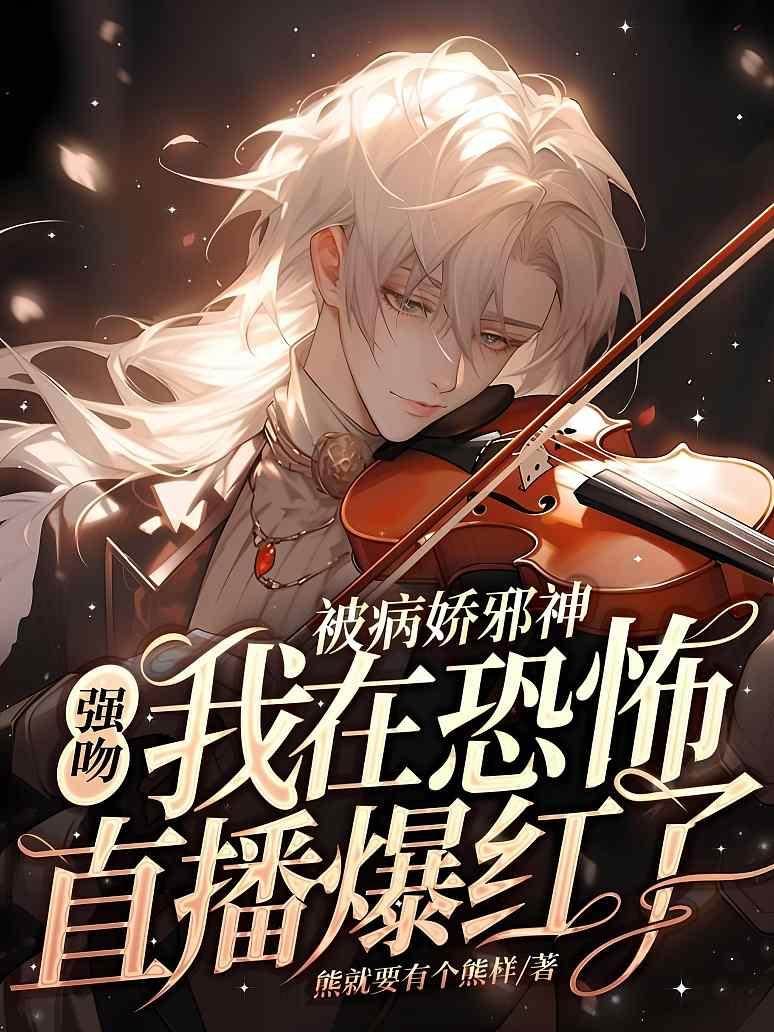
被病嬌邪神強吻!我在恐怖直播爆火了
桑榆穿越的第一天就被拉入一個詭異的直播間。為了活命,她被迫參加驚悚游戲。“叮,您的系統已上線”就在桑榆以為自己綁定了金手指時……系統:“叮,歡迎綁定戀愛腦攻略系統。”當別的玩家在驚悚游戲里刷進度,桑榆被迫刷病嬌鬼怪的好感度。當別的玩家遇到恐怖的鬼怪嚇得四處逃竄時……系統:“看到那個嚇人的怪物沒,沖上去,親他。”桑榆:“……”
123.3萬字8.18 19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