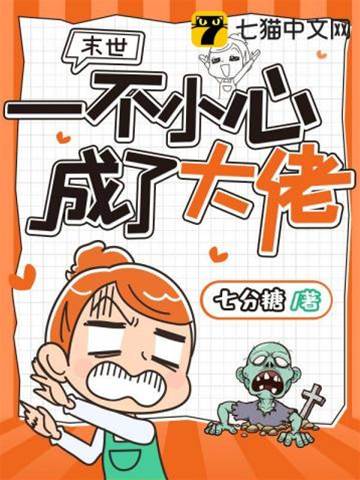《經過海棠》 第116頁
他找個借口服給看。
找個借口看他服。
但紀珍棠的視線太急切,盯著他被微微起伏的撐起的襯部位,嚨口做了一個十分明顯的吞咽作。
鐘逾白微不可察地挑了下角。
扣被他慢條斯理地解完,輕輕一掀,好而壯的男士便不加遮掩地撞進眼簾。
紀珍棠坐在床沿,視線混沌地出了紙和筆,握著筆桿的手巍巍,突然油然欽佩泰坦尼克號上那倆人。
的定力還不夠,從第一秒鐘起,就開始心猿意馬,思緒不在畫上。
鐘逾白到臺,找了個位置坐下,臺天,沒有窗,從夜空深洶涌卷起的風帶臥室里的綿帷幔,輕一下重一下地將之拍在墻面。
一場濃烈的雨又在醞釀,布景夜闌雨疏,春雷頻頻。
他穿西,坐在藤編沙發上,慵懶后靠,上不著毫遮掩,廓健,恰到好的脂率,讓筋骨與看起來均勻而實。
旁邊的綠植沙沙,微妙地掩映著他干凈的子。
夜幕之下,鳥月朦朧,男人仿佛一道修長的,虛虛的影。
Advertisement
“我要怎麼做。”鐘逾白打斷的凝視。
紀珍棠一本正經:“你……坐著就好。”
他點頭,于是便坐在那里看,表現出人.模特的滿分修養。
在課堂上幻想的時候,下筆如有神,此時此刻,卻頓著筆尖,不知道從哪里開始,五分鐘后,鐘逾白淡聲問句:“怎麼樣了。”
鬼知道,為什麼的筆落下去半天,才描了一個廓?
紀珍棠終于忍不住,把紙和筆丟了:“不行了,我一定要親你。”
自責,天底下怎麼會有這樣不專業的畫師?居心叵測!/模特!
但是對著這樣的一幅畫面,是真的一點都畫不出來。
而好心的模特只是略意外地揚起眉梢,無奈微笑一下,隨后大度地說:“請便。”
男人對人的寵,表現在即便天平失衡,他不能一換一,也淪陷于一而再再而三的祈求。
這次不談換,他舍己為人,甘愿被擺弄。
地毯致綿,鋪在藤編沙發之下,傷不到的膝蓋。
紀珍棠低眸,如愿以償,吻在他的那顆痣上,盡管看不清男人的表,但到下的青筋在微妙地鼓,僨張。
Advertisement
他驟然高升的溫像熱浪,拍到的上。
原來最殘酷的、被桎梏的覺,不是因為到迫,而導致心理或者緒上的失控,反而是最直觀的,一種彈不得,又不想束手就擒的難耐。
百爪撓心的難耐。
“可以了。”鐘逾白聲音沙沙的,企圖打斷咬住皮革的沖。
但紀珍棠已經打開了齒,哪里有就此善罷甘休的道理。
第一次,如此鮮明地到一個人的秩序在摧毀,深的某一道防線在緩緩坍弛。
線條輕微的繃,住后腦的手稍稍用力,勾纏著發的手指在竭力地克制,怕傷到,又迫切地想要制止。
纖弱的指下,是比那一天的心跳更是蓬百倍的跡象。
紀珍棠難得覺自己贏了一回,但又不可遏止溫,隨他一起發燙。
鐘逾白擰著眉,一只手托住的整個下頜,將拗不過他力氣的一張臉撥起。
“可以了,寶貝。”
第41章 第 41 章
◎的愉悅◎
不知道鐘逾白眼下在想什麼, 或許是懊悔草率地把自己給,以至不可收拾,游刃有余的局面被攪得稀碎, 壞了他運籌帷幄的優雅。
Advertisement
總之,他晦著雙目,在仰頭的瞬間跟視線相, 紀珍棠看到了一汪比平常還要深邃無垠的冷潭,深得讓人無法辨析。
只不過,對他所有的猜, 都只是猜。
紀珍棠的腦海里, 想到的卻是一句不應景的, 足以一秒殺死曖昧的話:玩火者終究被火焚。
這話是很久之前鐘珩對說的,一句重重的警告。
警告言猶在耳, 可即便如此, 想想還是刺激的。
滿意地笑起來, 出幾顆牙。
他的肩膀上落了點斜打進來的雨, 給深藏不的那一面添。
鐘逾白的泛紅,被吻過的地方落了個鮮明的印。
是故意烙上的。
他去肩上幾滴越界闖的春雨,隨后提腰, 披上襯衫, 作一氣呵。
卻沒掉那片印。
不是忘了,他分明也是故意不。
“笑什麼。”他看著, 低磁的聲線恢復了幾分理智。
自然是笑他甘心當了一回敗將,在愿賭服輸的棋局里。
紀珍棠傻笑不止,沒接話, 隨后便看見他抬指點了點自己的皮帶一隅, 看著的眸意味深長。
一個展現出固執不肯松口的痕跡的牙印, 分外清晰地陷進他價值不菲的皮革里。
讓剛才心思里的貪婪和不盡興一覽無余地顯現。
“啊,怎麼會這樣?”驚慌失措地托著臉,又可憐楚楚看向他,“你這皮帶肯定很貴吧,完了,我賠不起。”
鐘逾白失笑。
想不到,第一個念頭竟然是這個。
“那就賠點別的。”他云淡風輕地說著,把扣穿好,語氣很淡,也沒真的想讓賠點什麼。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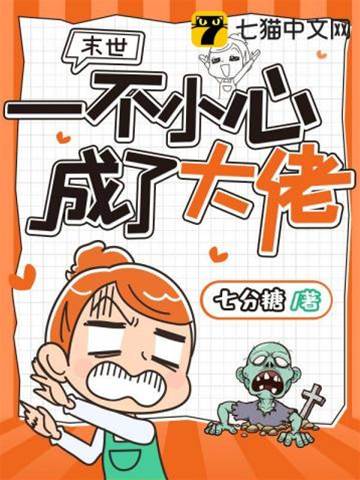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519 章

重逢后大佬盯上了她的崽
被雙胞胎渣妹算計謀害,懷孕后被迫遠走國外。四年后,她帶著一雙天才寶貝回國。重逢后。男人盯著兩個縮小版的自己,強硬的把她堵在角落,“女人,偷生我的崽是要付出代價的!”姜黎心虛,“……你想怎樣?”“我記得你罵我弱雞。”男人冷笑,“那就再生一個,證明一下我的實力!”“……”
90.3萬字8 87349 -
完結186 章

婚后偏寵
圈中好友都知道,盛苡喜歡程慕辭喜歡得不得了 她追他許久,好在終於得償所願 但她怎麼也沒想到,會在期待甚高的生日這天跌墜谷底,摔得慘烈 也是這時,謝問琢突然出現 現場聲音漸漸弱去,全都看向了這位謝家的掌權人 也是最惹不得的人物 - 在盛苡的印象裏,謝三哥對她就跟妹妹一樣 可是那一天,她在他的眼裏,看到了最認真、也最灼熱的眸光 那分明……是看愛人的眼神 - 婚前,謝問琢徵詢過她的意見:“結婚嗎?” 得她答應後,他頷首,遞出一份結婚協議 很久以後,盛苡纔讀懂——他當時到底有多“假模假樣”:) - 盛苡是個知恩的姑娘 幾個月後,她就提出了離婚,擔心耽擱了他 卻不曾想,他不緊不慢地折起袖口,一步一步朝她壓來,眼眸危險地眯起: “不好意思,忘了告訴你,謝家的門,只能進,不能出。” 盛苡:“……” 這是法治社會吧?是的吧?
29.3萬字8 98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