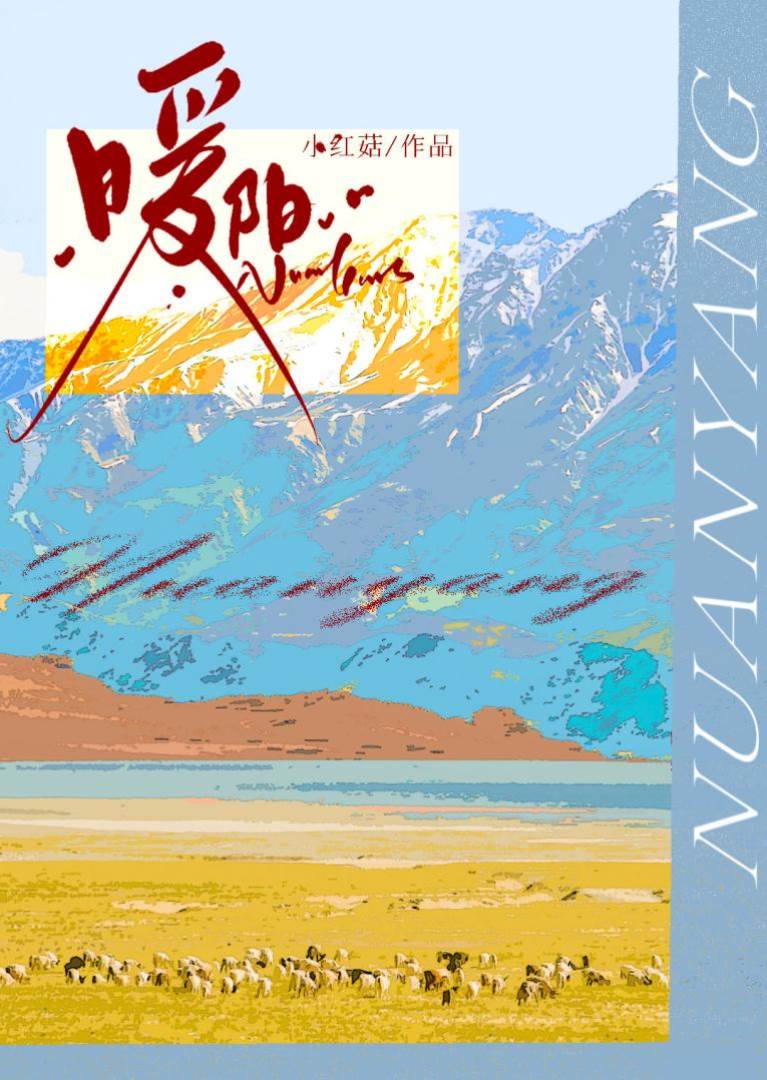《廢墟有神明》 第89章 我們現在,是什麽關係?
沒人能一直帶刺生活,再狂妄的人也有為某個人、某件事、某個想法融下來的一天。
“我跟你說啊,”徐茵低聲音,“擇言哥和許星池都跟傅司九一個高中啊,前段時間我想著幫你打探一下,就從擇言哥那裏套了套話。”
李擇言跟許星池一屆,都比傅司九高一級。
許星池不問世事,李擇言就不同了,他玩鬧,又八卦的很,到傅司九這麽一個人,不可能不多聽兩耳朵。
“傅司九來珠城時,邊還跟了兩個兄弟,”徐茵說,“後來那兩個兄弟憑空消失了。”
馮蕪:“......”
這麽恐怖的事,為什麽選在庫房說。
徐茵瞅:“一個死了,一個回港區了。”
“......”
“傅家鬥本來就厲害,”徐茵接著說,“傅司九被送來時年紀又小,總比他大哥大姐好拿,便有人想從他這邊下手,到底是大家族裏出來的,心計手腕沒得說,再加上許多事鞭長莫及,人家不著他,就設計到了他兄弟上。”
說到這,徐茵搖頭惋惜:“有些專門給富二代設的局,能一夜之間讓他們傾家產,連祖產都搭進去,細節沒人知道,傅司九明,不人家的局,可他一個兄弟著了道,後來跳樓死了。”
Advertisement
馮蕪怔忡:“跳樓?”
“嗯,”徐茵說,“就通達路那棟廢樓。”
馮蕪突然被揪了下。
上年某天夜晚,一個人去墓地看媽媽,恰好又在廢墟那裏見了傅司九。
傅司九告訴,他有個朋友死這兒了,馮蕪驚的嗆住,傅司九又改口,說是條狗。
馮蕪還以為他在惡作劇,故意講這些嚇。
“他兄弟死後,”徐茵說,“傅家著,那樓就停工了,一直荒廢到現在,後來,傅司九混了好長一段時間,逃課啊,跟一群混混玩在一起啊這些,反正也沒人敢管他。”
抿抿,言又止。
馮蕪看著:“說啊。”
徐茵眼神複雜,不知道該不該講。
遲疑了會,還是選擇說:“他這樣混,也不惜自己,傅家能不著急嗎,就把一個生送了過來。”
“......”
“那生,是他死去兄弟的妹妹,”徐茵覷,“跟傅司九差不多大,聽說念書、生活的費用都是傅司九給的,連畢業後進傅家企業,也是傅司九安排的。”
這個生,不由得讓馮蕪想起今天往咖啡館二樓看時,遙遙一見的人。
Advertisement
徐茵指尖點點下:“還有,方才,我聽你爸和你後媽的意思,是在撮合你和許星池?”
馮蕪沒反應:“不清楚。”
“你哪是不清楚,”徐茵氣笑了,“你分明是在裝傻。”
可理解馮蕪,當著許星池的麵,馮蕪沒辦法挑明白了說。
馮厚海和林素模棱兩可,不挑明,馮蕪就跟著裝,不接話不搭腔。
“刨去許星池作死的那些事,”徐茵歎,“他是真適合你,人穩重,事業有,知知底,阿姨的眼其實是沒錯的。”
馮蕪抱著文件夾往外走:“別提他,我回家了。”
徐茵上頭的臉:“我喝多了,臉燙。”
“司機送你,”馮蕪說,“我打車。”
見們兩人出來,許星池和李擇言紛紛起。
幾人都喝了酒,沒辦法開車,徐茵和李擇言的家在同個方向,馮蕪司機送他們,自己用手機了個車。
馮厚海皺眉:“你星池哥哥家的司機送一送你,孩子家的...”
“不用,”馮蕪略顯疏離,“我喜歡打車。”
許星池神不明:“在家裏住一晚,明天我送你上班。”
Advertisement
馮蕪抿抿,搖頭:“謝謝星池哥。”
不知何時起,最依的家,最知近的親人,為一心一意想逃離的沉屙。
一頓飯的功夫,能破壞掉砌築已久的保護牆,呼吸是滯悶的,也是堵塞的。
再不離開,怕裝出來的平靜會發。
“下個月你23周歲的生日,”馮厚海忽然說,“幫你備了個酒宴,記得參加。”
馮蕪回眸:“生日?”
“怎麽,”馮厚海說,“自己的生日,自己都不記得了?”
馮蕪倏地笑了:“我15歲後就沒過過生日,您現在給我過什麽生日?”
父倆之間硝煙再起,林素連忙圓場:“就是家宴,家宴,到時候茵茵和擇言都來。”
“不用了,”馮蕪說,“我不喜歡過生日。”
馮厚海眉間一凜:“馮蕪!”
許星池古井無波的眼神掠了過去:“伯父。”
他說話不輕不重,卻總能很好的製止馮厚海的壞脾氣。
“伯父您別生氣,”徐茵連忙道,“我們跟說,我們來說,嘿嘿...”
馮蕪麵無表,恰好的車到了,一步都沒停留,瞬間消失在夜中。
幾人先後離開。
許星池高高地站在庭院中,言辭淡淡:“伯父,您把這些年的份給了阿蕪,真的是因為我的話嗎?”
馮厚海看不出表,一張臉上全是老謀深算:“我說是,那就是。”
他拍拍許星池的肩,語重心長:“我是在幫你搶老婆。”
許星池不明顯地勾了勾。
幫他?
嗬。
-
出租車開到小區大門外停下。
下車後,出於本能,馮蕪往四周掃了一圈,許是太過敏,總覺得有一雙眼睛在暗悄悄地監視。
小區綠化一般,幾叢背竹倒長得旺盛。
快走到樓道口時,一束暖燙的猝然掃了過來。
馮蕪恰好在線中央。
瞇了瞇眼,手半遮住刺目的遠,回頭。
那輛眼的大G不知何時停在灌木旁邊。
太亮,看不見車人的表,馮蕪短暫地頓了頓,隨即像完全沒看到,邁步往樓道裏走。
傅司九皺眉,抬手摁了下喇叭。
喇叭聲在夜中回,孩子這次連頭都沒回。
“......”傅司九氣極反笑,推門下車,長著大步,趕在上樓前拽住。
“你這是沒瞧見,”傅司九給認錯的機會,“還是故意的?”
連理由都幫想好了,說一句沒瞧見,他就算了,不跟生氣了。
馮蕪手了,沒:“你怎麽來了?”
傅司九長眸裏的笑漸漸斂淨:“你什麽意思,我不能來?”
場麵沉默著定格。
“馮蕪,”傅司九嗓音沒有溫度,“你跟我說說,我們現在,是什麽關係?”
猜你喜歡
-
完結1638 章
新婚嬌妻寵上癮
(桃花香)一場陰謀算計,她成為他的沖喜新娘,原以為是要嫁給一個糟老頭,沒想到新婚之夜,糟老頭秒變高顏值帥氣大總裁,腰不酸了,氣不喘了,夜夜春宵不早朝!「老婆,我們該生二胎了……」她怒而掀桌:「騙子!大騙子!說好的守寡放浪養小白臉呢?」——前半生所有的倒黴,都是為了積攢運氣遇到你。
245.9萬字8 30971 -
完結256 章

別和我撒嬌
痞帥浪子✖️乖軟甜妹,周景肆曾在數學書裏發現一封粉色的情書。 小姑娘字跡娟秀,筆畫間靦腆青澀,情書的內容很短,沒有署名,只有一句話—— “今天見到你, 忽然很想帶你去可可西里看看海。” …… 溫紓這輩子做過兩件出格的事。 一是她年少時寫過一封情書,但沒署名。 二是暗戀周景肆六年,然後咬着牙復讀一年,考上跟他同一所大學。 她不聰明,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認識溫紓的人都說她性子內斂,漂亮是漂亮,卻如同冬日山間的一捧冰雪,溫和而疏冷。 只有周景肆知道,疏冷不過是她的保護色,少女膽怯又警惕,會在霧濛濛的清晨蹲在街邊喂學校的流浪貓。 他親眼目睹溫紓陷入夢魘時的恐懼無助。 見過她酒後抓着他衣袖,杏眼溼漉,難過的彷彿失去全世界。 少女眼睫輕顫着向他訴說情意,嗓音柔軟無助,哽咽的字不成句:“我、我回頭了,可他就是很好啊……” 他不好。 周景肆鬼使神差的想,原來是她。 一朝淪陷,無可救藥。 後來,他帶她去看“可可西里”的海,爲她單膝下跪,在少女眼眶微紅的注視下輕輕吻上她的無名指。 二十二歲清晨牽着她的手,去民政局蓋下豔紅的婚章。 #經年,她一眼望到盡頭,於此終得以窺見天光
45.4萬字8 21446 -
完結1693 章

離職后我懷了前上司的孩子
作為總裁首席秘書,衛顏一直兢兢業業,任勞任怨,號稱業界楷模。 然而卻一不小心,懷了上司的孩子! 為了保住崽崽,她故意作天作地,終于讓冷血魔王把自己給踹了! 正當她馬不停蹄,帶娃跑路時,魔王回過神來,又將她逮了回去! 衛顏,怒:“我辭職了!姑奶奶不伺候了!” 冷夜霆看看她,再看看她懷里的小奶團子:“那換我來伺候姑奶奶和小姑奶奶?”
165.2萬字8.18 38138 -
完結201 章

雙時空緝兇
【01】南牧很小的時候就遇到過一個人,這個人告訴他:絕對不要和溫秒成為朋友。 日長天久,在他快要忘記這件事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個女生,那個女生叫做:溫秒。 【02】 比天才少女溫秒斬獲國內物理學最高獎項更令人震驚的是,她像小白鼠一樣被人殺害在生物科研室,連頭顱都被切開。
38萬字8 179 -
完結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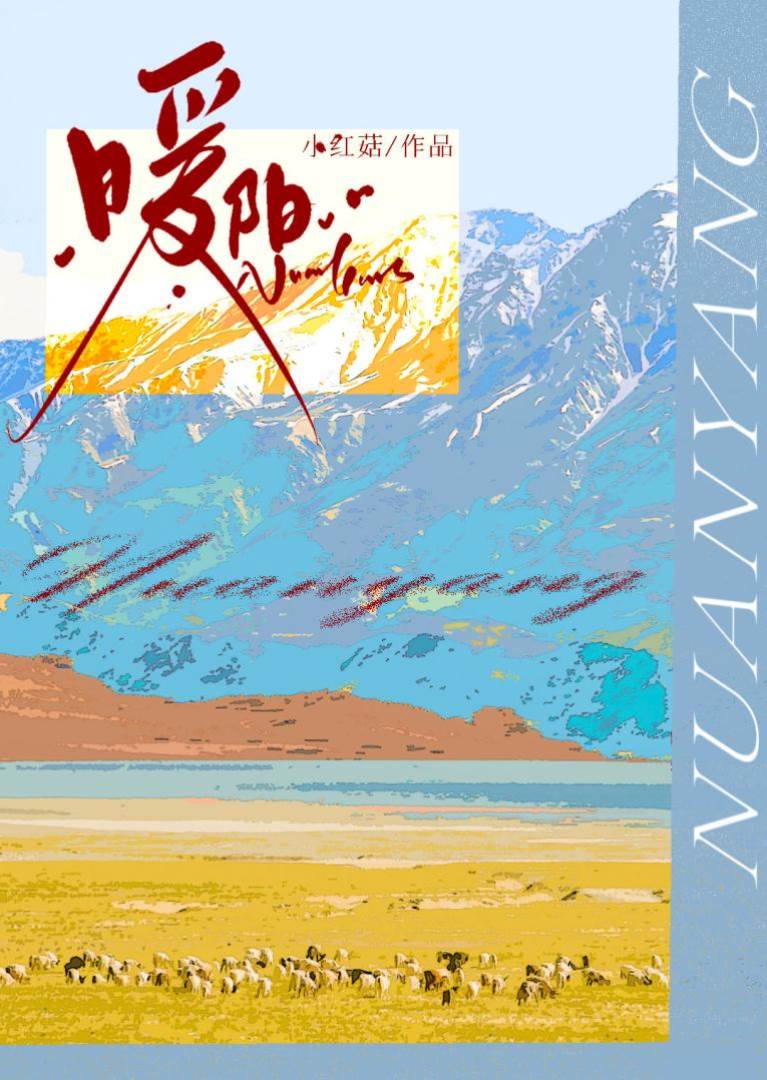
暖陽[先婚後愛]
文冉和丈夫是相親結婚,丈夫是個成熟穩重的人。 她一直以爲丈夫的感情是含蓄的,雖然他們結婚這麼久,他從來沒有說過愛,但是文冉覺得丈夫是愛她的。 他很溫柔,穩重,對她也很好,文冉覺得自己很幸福。 可是無意中發現的一本舊日記,上面是丈夫的字跡,卻讓她見識到了丈夫不一樣的個性。 原來他曾經也有個那麼喜歡的人,也曾熱情陽光。 她曾經還暗自竊喜,那麼優秀的丈夫與平凡普通的她在一起,肯定是被她吸引。 現在她卻無法肯定,也許僅僅只是因爲合適罷了。 放手可能是她最好的選擇。 *** 我的妻子好像有祕密,但是她不想讓我知道。 不知道爲什麼他有點緊張,總覺得她好像在密謀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他卻無法探尋。 有一天 妻子只留下了一封信,說她想要出去走走,張宇桉卻慌了。 他不知道自己哪裏做得不夠好,讓她輕易地將他拋下。 張宇桉現在只想讓她快些回來,讓他能好好愛她! *** 小吳護士:你們有沒有發現這段時間張醫生不正常。 小王護士:對,他以前除了工作之外,基本不發朋友圈的,現在每隔幾天我都能看到他發的朋友圈。 小吳護士:今天他還發了自己一臉滄桑在門診部看診的照片,完全不像以前的他。 小劉護士:這你們就不知道了吧,張醫生在暗搓搓賣慘,應該是想要勾起某個人的同情。 小王護士:難道是小文姐?聽說小文姐出去旅遊了,一直還沒回來。 小劉護士:肯定是,男人總是這樣的,得到了不珍惜,失去了纔會追悔莫及。
22.5萬字8 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