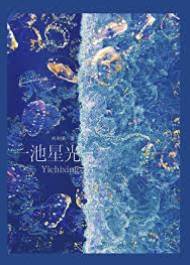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廢墟有神明》 第105章 許總,你快輸了。
珠城育館位於城江環繞中心,四周蓊鬱的紫薇和合歡在夏日大片大片盛放,是市民周末節假日最喜歡待的地方。
深深淺淺的與紫如雲如霞,連天邊雲都跟著溫了。
一樓半封閉式臺球館,球撞擊、伴著球落袋的聲音,除此之外,別無它響。
斯諾克較之起來規則複雜,計算細,也需要花費超出平常的心力,擊球時要求更加細心和準。
盧行添方想拍手好,單州和張以辭一邊一個摁住他,怒其不爭:“瞧瞧人家對麵的人,別他媽跟個猴子一樣上躥下跳,穩重點,總不能被人家比下去吧。”
這場球賽以切磋為名,但兩方人馬都不約而同嗅出了硝煙與戰爭的味道。
相比於邊人的張,傅司九波瀾不驚,臉上沒有表,拿著球桿繞了半個球臺,俯,修長嶙峋的手搭出眼手架,球桿穩穩架在指中,遊刃有餘地擊中目標球。
好歹是參加流會,他難得穿了件白襯衫,俯彎腰時,肩胛骨骼鋒利,熨的黑西包裹著一雙長,勾勒出完的線。
許星池握著球桿拍手:“百聞不如一見。”
傅司九鼻息了輕哂:“別惡心我,真不了你們這些正人君子言不由衷的誇讚。”
Advertisement
盧行添噗嗤笑了。
許星池麵不改,找準位置後,拿著球桿擊球。
“小九爺,”他銳利的目盯著目標球,淡淡道,“叮叮麻煩你長時間了,是不是可以還給我了?”
傅司九把球桿當拐杖,整條胳膊拄著,恨不能別人抬張沙發給他躺的慵懶。
“怕是不行呢,它姐姐小脾氣厲害得,我可不敢隨意送人。”
話落,許星池的桿“咚”一聲,撞擊的稍失了準頭。
“多謝許總送分,”傅司九笑,“斯諾克呢,眼睛作尺,還要穩,手穩,桿穩,心穩。”
這番話別有深意,落到旁人耳中又像嘲諷。
許星池慢慢斂了視線,看不出任何波:“小九爺別不是認錯人了吧,我家阿蕪向來好脾氣。”
傅司九不跟他爭辯:“嗯,許總說什麽就是什麽。”
“......”
許星池多明白外界對傅司九|評論是怎麽來的了。
這人隨意敷衍的言行中,沒把任何人放進眼裏過,那種天然的蔑視與矜傲,就像人類在麵對一地大白菜似的覺。
一種不在同個維度的優越與漠視。
Advertisement
偌大的場館雀無聲。
傅司九彎腰,一雙冷白的手支在球臺,手背皮青的筋脈與綠的球臺相輝映,蓬出一莫名的張力。
“許總,”他嗓音得很低,像是要把注意力放在球上,“男人的事,咱們自己解決,傷著小姑娘可就不好了。”
說完,他肘部後移,蓄力的作,幹淨利落地擊打。
許星池扯出一點笑:“我不明白小九爺的意思,可否直言?”
傅司九直起後背,與他互視。
兩個男人高不分伯仲,氣質卻截然不同,在周圍十幾人的圍觀下,如同鶴立群。
無形的硝煙在場彌漫開。
“君子藏,以鋒策己,”傅司九不避不讓,淡而疏離,“以鈍示人,我沒念過什麽書,還想請許總幫我解釋一下。”
許星池:“小九爺謙虛。”
傅司九:“比不上許總。”
旁邊的盧行添抓抓腦袋,不解:“他們兩個在打什麽太極。”
“閉吧你,”張以辭沒好氣,“一張就暴了你文盲的氣質。”
盧行添:“你懂?”
張以辭:“不懂。”
盧行添:“你|他|媽不懂還這麽囂張?”
Advertisement
張以辭:“總比你怯好。”
“你們倆都閉,”單州無語,“君子用高標準要求自己,而不是去束縛別人,小九這是嘲諷許星池對妹妹不好呢。”
場麵定格良久。
館的冷氣仿佛有了實,凍的人瑟瑟發抖。
傅司九半邊勾了下,角拉出壞的笑弧:“許總,若是缺個端茶倒水的人,我倒不介意伺候您。”
“......”許星池眸子像冰,“小九爺有話請直說。”
傅司九:“許總能願意直說才好。”
“聽說阿蕪的那輛新車是小九爺買給的,”許星池盯著他,“年紀小,心思恪純,以為別人為花點錢便是對好了,家裏對管教頗嚴,倒忽略了已經長大,該財務自由了,但還是多謝小九爺好意,車款隨後奉還。”
傅司九表不明,將落袋的彩球擺回原位:“原來你們的家教頗嚴,就是對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許星池指骨忽地攥。
傅司九了下眼皮,看著他:“許總玩得一手好綁架。”
“......”許星池猝然戾,“小九爺,別人的家事,你逾矩了!”
“家事?”傅司九平靜道,“許總有所不知,令堂出事那晚,阿蕪是被我拖住了回家的腳步,若有怨怪,許總怕是怪錯了人。”
許星池一僵。
“若不是被帶去做了筆錄,”傅司九說,“阿蕪會提早到家,再不濟,也會在家門口跟令堂上,我奉行人各有命,厭煩誰欠誰那一套,可這事說破天去,責任也該歸我。”
他目深邃平靜:“雖然於事無補,但許總若有想要的補償,或者缺個順手的小弟,幫許總朋友拎個包、付個款什麽的,傅某義不容辭。”
許星池腔中湧現出一控製不住的怒火與焦躁。
傅司九把態度放的這樣卑微,真是前所未有,他是想一力攬下所有的責任,隻為了把馮蕪摘出去。
在場眾人皆語塞住。
這是傅家最寵的老幺,他們連麵都輕易見不得的,許多小道消息都是傳聞。
可這個傳聞中高不可攀的男人,竟然願意俯首。
許星池口腔咬破了,腥味充斥進味蕾,他極力忍下異狀,直白道:“我自家兄妹如何相,就不勞小九爺心了,再怎麽鬧,也總比外人心來拿當個樂的好。”
傅司九沒什麽表,沒針對他這句話給出反駁。
你永遠不醒一個裝睡的人。
他指尖點點球臺,像是在描述一個事實,嗓音淡漠如霜:“許總,你快輸了。”
猜你喜歡
-
完結500 章

陌路婚途
結婚四年,老公卻從來不碰她。 她酒後,卻是一個不小心上了個了不得的人物。 隻是這個男人,居然說要幫她征服她的老公? excuse me? 先生你冷靜一點,我是有夫之婦! “沒事,先睡了再說。”
89.4萬字8 73159 -
完結2312 章

有孕出逃:千億總裁追妻成狂
夏時是個不被豪門接受的弱聽聾女,出生便被母親拋棄。結婚三年,她的丈夫從來沒有承認過她這個陸太太。他的朋友叫她“小聾子”,人人都可以嘲笑、侮辱;他的母親說:“你一個殘障的女人,就該好好待在家裏。”直到那一天他的白月光回國,當著她的麵宣誓主權:“南沉有說過愛你嗎?以前他經常對我說,可我總嫌棄他幼稚。我這次回來,就是為了追回他。”夏時默默地聽著,回想著自己這三年和陸南沉在一起的日子,才驚覺發現,她錯了!結婚三年,夏時愛了陸南沉十二年,結果卻深情錯付。種種一切,讓夏時不堪重負。“陸先生,這些年,耽誤你了。”“我們離婚吧。”可他卻把她關在家裏。“你想走,除非我死!”
207.6萬字8.33 330489 -
完結380 章

插翅難逃之督軍請自重
她,是為姐姐替罪的女犯。他,是殺伐果決、令人生畏的督軍。相遇的那一刻起,兩人命運便交織在了一起。顧崇錦從來沒想過,一個女人竟然成為了他最大的弱點。而偏偏那個女人,卻一心隻想逃離他。宋沐笙也沒有料到,一心隻想保護姐姐的她,早已成為了男人的獵物。他近乎瘋狂,讓她痛苦不堪。為了留住她,他不顧一切,甚至故意讓她懷上了他的孩子,可誰知她居然帶著孩子一起失蹤......她以為她是恨他的,可見到他一身軍裝被血染紅時,她的心幾乎要痛到無法跳動。那一刻她意識到,她已經陷阱這個男人精心為她編織的網裏,再也出不來......
64.9萬字8.18 8586 -
完結8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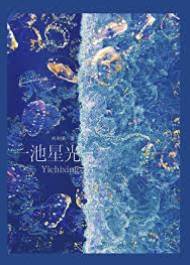
一池星光
夏星曉給閨蜜發微信,刪刪減減躊躇好久,終於眼一閉按下發送鍵。 食人星星【不小心和前任睡了,需要負責嗎?】 閨蜜秒回【時硯池???那我是不是要叫你總裁夫人了?看了那個熱搜,我就知道你們兩個有貓膩】 原因無它,著名財經主播夏星曉一臉疏淡地準備結束採訪時,被MUSE總裁點了名。 時硯池儀態翩然地攔住攝像小哥關機的動作,扶了扶金絲鏡框道,“哦?夏記者問我情感狀況?” 夏星曉:…… 時硯池坦蕩轉向直播鏡頭,嘴角微翹:“已經有女朋友了,和女朋友感情穩定。” MUSE總裁時硯池回國第一天,就霸佔了財經和娛樂兩榜的頭條。 【網友1】嗚嗚嗚時總有女朋友了,我失戀了。 【網友2】我猜這倆人肯定有貓膩,我還從沒見過夏主播這種表情。 【網友3】知情人匿名爆料,倆人高中就在一起過。 不扒不知道,越扒越精彩。 海城高中的那年往事,斷斷續續被拼湊出一段無疾而終的初戀。 夏星曉懶得理會紛擾八卦,把手機擲回包裏,冷眼看面前矜貴高傲的男人:“有女朋友的人,還要來這裏報道嗎” 時硯池眸底深沉,從身後緊緊地箍住了她,埋在她的肩膀輕聲呢喃。 “女朋友睡了我,還不給我名分,我只能再賣賣力氣。” 夏星曉一時臉熱,彷彿時間輪轉回幾年前。 玉蘭花下,時硯池一雙桃花眼似笑非笑,滿臉怨懟。 “我條件這麼好,還沒有女朋友,像話嗎?”
29.5萬字8 1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