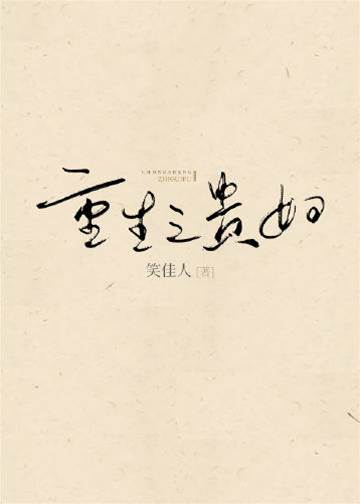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和離后,她被渣王叔叔嬌寵了》 第496章 苗疆奇毒
「到了這個節骨眼,兒臣真不知母后是哪來的底氣對兒臣大呼小。」
皇帝的臉也沉了下來,「母后莫非是想怪朕不念親?如果為一個君王,不以黎明百姓的利益為先,那麼這大好河山朕恐怕坐擁不了多久。」
「哀家從未說過讓你罔顧百姓的利益,你想做一個好君王,哀家自然是要支持你,哀家只不過是想你饒恕他們這一回,哀家跟你擔保他們以後不會再犯錯了,你就非得用他們的鮮來警示他人嗎?」
太后的語氣裏帶著央求,「自你繼位以來,十分勤政,連後宮都甚走,你已經足夠聖明了,沒有誰敢說你一句不好,更何況林家人所犯的過錯只不過是你私下從宮人們口中審問出來的,若是有人在你上朝時舉證,那你自然無法徇私,可眼下事態還不嚴重,你分明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又何必做得那麼絕呢?」
「因為他們屢屢犯錯,本不配朕的寬恕。」皇帝不假思索道,「朕知道,這份名單上面有朕的舅舅,還有朕的姨母,他們都是曾經幫過朕的人,正如母后所言,為了讓朕能夠順利繼位,他們曾明裏暗裏幫朕打朕的對手,所以朕後來也給過他們不賞賜了,朕自以為沒有對不住他們的地方。」
「如果曾經的功績能作為挑釁朝廷律法的籌碼,那豈不是顯得律法太過可笑?更何況他們當初的相助,也只不過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罷了,林家人是您的娘家,您坐上太后之位,他們自然要跟著福,所以他們不餘力地幫助我們母子,如今這日子越過越好,野心和胃口卻越來越大了,朕若是再不打擊他們,只怕他們哪天就要做出更荒唐的事來了。」
Advertisement
「胡說!」太后厲聲反駁道,「哀家知道歷代皇帝都忌憚外戚攬權,所以哀家早就警告過他們,絕不會賦予他們權利和軍隊,他們只不過是拿了幾個不大不小的職,沒有實權在手,你本不必擔心他們會對你不利,他們的確是做了錯事,貪了些錢財,可這和犯上作比起來還差得遠,你本不必為了發泄怒氣就給他們扣多大的罪名。」
太后說到後頭,語氣已經難掩激。
在過去那些年裏,皇帝即使對外手腕冷酷,在面前也從不聲俱厲。
以為作為皇帝的母親,想保幾個自家人,皇帝多多也會給些面子。
可眼下的形卻告訴,皇帝已經不再是從前那個能由訓斥、聽教誨的孩子了,他甚至在的面前直言要殺了的兄弟姐妹。
「所以在母后的眼裏,只要他們還沒走到冒犯朕的那一步,其他行為都可以容忍嗎?」
皇帝起注視著太后,目中是道不明的失,「朕平日裏專註於政務,忙起來的時候,好幾天都未給母后請安,朕原本還覺得有些愧疚,可母后總說您能夠諒解朕的辛苦,朕不出時間陪伴您,但林家人可以,所以朕在心底深也是對他們有幾分激的。您平日裏誇他們的話,朕也都全信了,可他們和您都辜負了朕的信任。」
「皇兒,就當是母后求你了行不行。」太后垂下了頭,聲線有些悲戚,「你日理萬機,與他們沒有什麼集,可他們是與我脈相連的親人啊。」
「您為太后,本該與朕站在同一陣線,可您卻非要為了他們跟朕翻臉,既然您如此不清醒,那我們母子二人也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皇帝毫不搖立場,起便要離開。
Advertisement
「站住!」太后在他的後呵斥一聲,「你要去做什麼,你就這麼迫不及待地要去下旨誅殺母后的親人嗎?」
皇帝腳下的步伐頓了頓,「如果母后因此而覺得朕冷酷無,那朕也沒有什麼好辯駁的。」
「別殺他們,放過他們一條生路。這樣,該革職的革職,該驅逐的驅逐,母后現在也不要求別的了,只要留他們的命就好。」
「他們犯的是死罪。在母后眼中就只有他們的命珍貴,那被他們欺的平民又該找誰說理去?如果朕不是皇帝,朕或許可以違背原則饒他們命,可朕偏偏坐在皇位上,那就要做朕應該做的事。」
皇帝背對著太后,聲線頗為堅決,「自作孽不可活,朕希母后不必再干涉朕做出的任何決定,朕會對外宣稱母后您生病了,即日起,沒有朕的允許,您不得離開寢宮半步。」
「你怎麼能這樣對待自己的母親?」太后又驚又怒,「哀家是生你養你的人!」
「正因如此,所以朕只是將您囚了而已,朕僅有的一點私心要用來保全您,至於旁人,無論是犯上作還是欺百姓,都是罪該萬死,死不足惜。」
說完,他大步流星地踏了出去。
太后著他的背影漸行漸遠,面如死灰地癱坐在椅子上。
的家人就要被的兒子死了,該如何是好……
「來人!來人!」大聲朝空氣吶喊著。
很快便有宮跑進了寢殿,「太後娘娘,陛下剛才走的時候下令了,說是沒有他的允許,您不得離開寢宮。」
「哀家知道,無需你再提醒!」太后厲聲道,「皇帝今日為何會突然來此對哀家的宮人嚴刑供?他在宴會結束之後,都去了哪些地方?你速速去打聽。」
Advertisement
宴會上的那齣戲唱的只是德妃與婉妃,皇帝沒理由會想到要去查林家人。
定是有人在私底下和他告發了。
……
「今夜註定要有許多人睡不好覺了。」
幽靜的園林小道上,溫玉禮牽著蕭雲昭的手緩步行走,一陣習習涼風從耳畔拂過,不打了個哈欠。
「困了麼?」蕭雲昭挲著的手心,「馬車就在前邊不遠,你若是困了,就先趴在我肩上睡一會兒。」
「還好。」溫玉禮朝他勾了勾,「最近的睡眠相當穩定,一到了這個點兒就想打哈欠。」
自從懷有孕之後,就一直保持很好的作息和生活習慣。
行走之間,二人忽然聽見前邊不遠傳來一陣孩的嬉鬧聲。
「好像是小孩在玩鬧的聲音。」溫玉禮道,「都這麼晚了,哪來這麼多小孩?」
懷著好奇心,拉著蕭雲昭走向了聲音來源,拐了個彎,便看見前邊一空曠的平地上,蕭謹恆正和五個與他年歲相差不大的孩子們蹴鞠。
「是雜技團的小孩們。」溫玉禮雙手環,說道,「太子平日裏裝得還沉穩,可上同齡的小孩們,還是平易近人的嘛。」
蕭謹恆雖說有著比同齡人更高的天分以及智力,可終歸還是擺不了孩子的天,難以拒絕好吃的以及好玩的。
若按照嚴格的宮規,這些平民出的小孩是沒有資格與太子一同玩的,此刻他們能夠與蕭謹恆打一片,顯然是蕭謹恆自己放下了架子邀請他們的。
聽說皇后平日裏管他管得可嚴,他也沒有什麼玩伴,但他心深總會著有一些同齡的孩子能夠與他一同玩耍吧。
「太子殿下,時辰真的不早了,您該回去歇息了。」
負責照料太子的嬤嬤嘆著氣道,「若是被皇後娘娘知道您這個時辰還在寢宮外玩耍,您明日肯定要挨訓斥。」
「只要嬤嬤不跟母后說實話,母后就不會知道了。」蕭謹恆樂呵呵地笑道,「本宮再玩一會兒就回去了,今日是本宮的生辰啊,晚點兒回去睡覺,也不至於罵我的。」
說話間,有一名個高的孩子已經把木鞠傳到了他的腳下,蕭謹恆抬腳一踢,傳到了另一個孩子的腳下,可那孩子或許是踢得太急了,腳下一個打,竟把木鞠踢出了規定範圍——
溫玉禮眼見著圓滾滾的木鞠飛到了自己面前,抬便將木鞠踏於腳下。
蕭謹恆看見,面上展了一抹笑容,朝小跑過來,「姑母這麼晚了還沒回去嗎?你會不會玩蹴鞠?要不要與我們玩一會兒?」
「我這麼大個人了,跟你們這群小孩玩,那不是欺負你們嗎?」溫玉禮低笑了一聲,「更何況我是有功夫在的,和你們玩這個,贏了也不彩。」
「那你就別用力。」蕭謹恆接過話,「咱們就比腳下的功夫還有靈敏速度,若是你用了力,那你就是耍賴,若不用力,你還真不一定踢得過我們。」
「你這是要跟我玩激將法?」溫玉禮輕挑了一下眉頭,「那就……」
「不準玩。」蕭雲昭出聲反對道,「時辰不早了,你剛才不是還打哈欠嗎?咱們該回去歇著了。」
說著,他手了溫玉禮的手心,「可別忘了,你如今不能像從前那樣蹦蹦跳跳,還是安靜些好,你若想玩蹴鞠,明年我一定陪你玩到盡興。」
溫玉禮了鼻子,「那好吧,今夜就不玩了。」
說著,便將腳下的木鞠輕輕一踢,還給了孩子們。
「姑母如今怎麼變得這麼老實?他說不讓你玩,你就真不玩了?」
蕭謹恆仰頭著溫玉禮,眼珠子轉了轉,「有個詞怎麼說的來著,懼,對,好像是這麼形容的。」
「胡說八道什麼?懼是形容男人怕媳婦的,別知道一個詞就在這用。」
溫玉禮輕了一下角,「我才不是怕他呢,只不過他是為了我好,因為我最近有點不適,司徒大夫說了,讓我盡量做些大幅度的運。」
「原來是這樣。」蕭謹恆撇了撇,「好吧,既然姑母子不適,我也就不邀請你加了,話說回來,近日天氣是越來越熱了……」
蕭謹恆一邊說著,一邊挽起了袖子和,想讓自己能涼快一些。
而他挽起袖子的時候,蕭雲昭卻看見他手腕上有一抹淡紅的圖案。
他當即敏銳地擒住了蕭謹恆的手腕。
蕭謹恆不明所以地著他。
「別,我看看。」
蕭雲昭將蕭謹恆的手腕翻轉了過來,看清他上的圖案形狀后,目當即一凜。
他手腕上的那抹淡紅圖案,呈現出了花朵的形狀。
「這是什麼?」溫玉禮面帶疑,「刺青麼?這未免也太淡了。」
「應該是蚊子之類的飛蟲咬的,形狀還怪好看。」蕭謹恆說道,「我上也有幾個包,一撓就,不撓就沒覺了。」
蕭雲昭卻沒多說什麼,而是轉頭朝一直跟在後的司徒彥說道:「你來看看。」
司徒彥也看清了那抹圖案,面上浮現了一異樣的神。
「太子殿下,能否讓我看看你上的包?」
蕭謹恆聞言,把管掀得更高了些,「嬤嬤說,點葯,過一兩天就能好。」
司徒彥查看了他上的幾紅腫,的確是蚊蟲叮咬的,可他手腕上那抹印記卻不是。
溫玉禮見二人的神都有些古怪,可二人卻都不明著說,彷彿是顧慮到什麼,也就沒直接追問。
蕭雲昭神如常地朝蕭謹恆說道:「現在天氣越發熱了,尤其是在花草叢林中,蚊蟲居多,你要警惕那些昆蟲來咬你,你的嬤嬤方才你早點兒回寢宮休息是對的。」
此話一出,旁邊的嬤嬤連忙接過了話,「寧王殿下所言甚是,太子殿下,您看您都出了不汗了,還是和奴婢回寢宮歇息去吧。」
蕭謹恆撇了撇,「也罷,今夜玩得也夠久了,那咱們回去吧。」
說著,他瞅了一眼旁邊站著的五個小孩,「這麼晚了就別讓他們出宮了,讓他們在宮裏留一夜,明早再讓人將他們安全送出去。」
「那我們也先回府去了,太子殿下,改日再見。」
溫玉禮道別之後,便拉著蕭雲昭迅速離開。
「你們二人方才的臉是怎麼回事?我都沒看明白,太子手腕上那抹淡紅的圖案是代表了什麼嗎?」
反正絕對不會是被蚊蟲叮咬出來的形狀。
「那是苗疆奇毒,是以一種罕見的毒花,午夜沙華所製,從中毒到毒發要經過三個階段,以太子手上的形狀來看,如今是第一階段初綻,過幾天會進第二階段盛開,等到了第三階段,那便是枯萎。」
司徒彥的神有些凝重,「枯萎階段,標記會由紅變黑,屆時全的都會凝固,到死的時候,渾都會泛黑,死狀極其難看。」
猜你喜歡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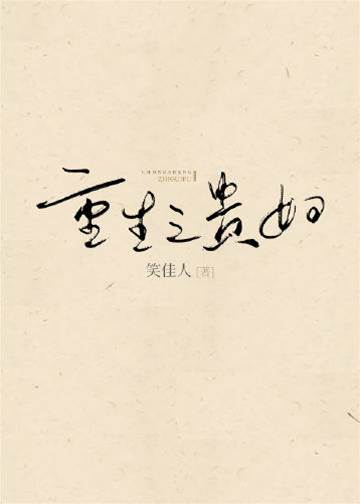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1 195765 -
完結693 章

修仙女配拒絕炮灰劇本
(非傳統修仙文,想看傳統修仙文的請繞路,不要在評論區打差評,謝謝) 女主許桃意外穿進一本修仙小說裡,成了青嵐宗太上長老的獨生愛女。 除了有個牛逼到不行的親爹,她的師父還是青嵐宗最年輕的化神修士。 這樣的出身,怎麼樣也得是個女主配置吧? 可惜並不是! 許桃知道在她築基成功這天,師父會帶回一名清純得有如白蓮花一般的小師妹。 小師妹會奪走她所有的機緣,會害她眾叛親離,最終她還會死於痴戀小師妹的眾多男配手中,不得善終。 回憶著書中自己的悲慘下場,許桃堅定的撕掉了手上的砲灰劇本。 只見許桃冷冷一笑,想讓她做炮灰,問過她爹了嗎!問過她男人了嗎! 她爹是誰?修仙界戰力天花板了解一下! 至於她男人是誰,許桃得意一笑,就是那個書裡面那個小師妹求而不得的白月光啊~
127.3萬字8 32170 -
完結245 章

重生將女狠囂張
她舉全族之力扶持新皇,卻被他陷害至死,靈魂永禁在皇宮祠室內,眼睜睜看著滿門被屠戮。她發誓要將那些作踐她的真心、傷害百里家的人,親手送進地獄,卻在重生歸來的第一天,就被楚王夏侯樽狠狠捏住了下巴。“你就這麼愛他?為了他可以不惜一切,甚至向本王下跪?”這一次,她挺起了脊梁,笑靨如狐:“別人的生死與我何干,我只想問,楚王殿下對皇位是否有興趣?”夏侯樽輕輕靠近:“皇位與你,我都想要。”
69.6萬字8.17 139990 -
完結262 章

侯府主母
翁璟嫵十六歲時,父親救回了失憶的謝玦。 謝玦樣貌俊美,氣度不凡,她第一眼時便傾了心。 父親疼她,不忍她嫁給不喜之人,便以恩要挾謝玦娶她。 可畢竟是強求來的婚事,所以夫妻關係始終冷淡。 而且成婚沒過多久永寧侯府來了人,說她的丈夫是失蹤許久的永寧侯。 情勢一朝轉變,怕他報復父親,她提出和離,但他卻是不願。 隨他上京後,侯府與京中貴眷皆說她是邊境小城出身,粗俗不知禮,不配做侯府主母,因此讓她積鬱。 後來謝玦接回了一對母子,流言頓時四起,她要謝玦給她一個說法。 可恰逢他要帶兵剿匪,他說回來後來後再給她一個交代。 可沒等到他回來給她交代,卻先傳回了他戰死的消息。 她心有疙瘩的守寡了多年後,卻莫名重生回到了隨他初入侯府的那一年。 * 謝玦近來發現妻子有些怪異。 在他面前不再小心翼翼。且吃穿用度也不再節儉,一切都要用好的貴的。打扮更是不再素雅,而越發的嬌豔。 就是對他也越來越敷衍了。 這種奇怪的跡象不得不讓謝玦警惕了起來。 他的妻子,莫不是移情別戀了……?
41萬字8.09 53794 -
完結216 章

美人與獵戶
齊繡婉是刺史千金。 本該錦衣玉食,高枕無憂一世的小姑娘,卻因爲偷聽到惡毒大嫂密謀害人的事情,所以被惡毒大嫂毒啞了嗓子和折斷了手,最後又被賣到了封閉的鄉野山村中。 小姑娘爲了爹孃不被惡毒嫂子加害,更爲了在爹孃的面前拆穿惡毒嫂子的真面目,她忍辱負重,不敢輕易尋死。 可逃離之日卻是遙遙無期,沒有任何的希望。 就在感到絕望之時,有一個沉默寡言,體魄強壯的男人在市集上用了三兩銀子把她買了下來。 開始的時候小姑娘怕這個男人怕得要死,巴不得男人離她遠遠的,可後來卻是男人讓她離得遠遠的,小姑娘卻反而越發的黏人。 【落難美人x沉默寡言身強體壯獵戶】
34.2萬字8.25 140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