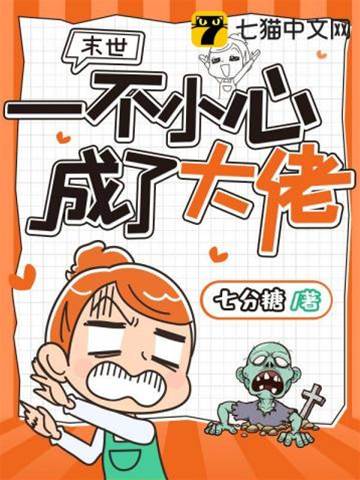《病態占有》 第135章 梁朝肅:雪夜浪漫,你是人間
梁朝肅五廓濃度高,立深邃,近看比遠看更有沖擊力,特別面無表時,只剩一雙寒冰雪的眼睛。
盯著人時候,鷙,痛擊人心,有直達靈魂的震。
連城直面這種目久了,生出抗。
梁朝肅就算把皮拆骨,也想不到會向死而生。
畢竟這四年,不管境地如何,頑抗到最后一秒,只字不提一個死。
頂多料定,是發現離開契機,準備離開。
可船上不走,他留在胡薩維克創造機會,稍微出端倪,他又氣憤惱怒。
仿佛是,你快走,卻不能雀躍,不能小跑,但還是要快走。
連城爬起來,細碎雪粒沾滿子,扭去拍,男人制止,扣著肩膀,俯一點點拂去雪珠,有部分雪粒化水,飛濺起來,洇他袖口。
風雪中路燈迷蒙,一片片雪花綴滿他頭上線帽,也綴滿了的,莫名的氛圍。
連城躲開他鉗制,繼續往下走。
梁朝肅幾步追上,從背后攬,風聲、雪聲、咯吱腳步聲,在這雪夜長街,一種吵鬧的靜謐。
他聲音近在耳畔,沉穩的穿力,“有沒有想過孩子名字?孩的,男孩的。”
Advertisement
連城口袋里的手無意識攥,“你冷不冷?” 梁朝肅注視側臉,皮細又薄,在風雪中凍出驚心魄的紅暈,“不冷。”
連城立即打哈哈,“我也不冷,就是有點哆嗦。”
梁朝肅沉默,他眼底翻來覆去深濃的涌,此時此刻顯得空寂,荒蕪,像塌陷了一片,涌又流回里,流回心臟。
他清楚,逃離機會在即,有希,便不想與他談論任何深的,關于孩子的話題。
兩人骨融,孕育一個神圣奇妙的生命,千方百計瞞著,不肯讓他知曉,一心帶著孩子,奔赴遠離他的未來。
決然的、狠心的剝離掉他跟孩子的聯系,直白將他歸到敵人那一行。
“你假裝聽不懂的話,我不會再重復。”
連城心弦繃一線。
這話聽來酸,仿佛對無可奈何,退讓了,摻著忍耐,遷就。
可連城了解梁朝肅,這是一個預告,也是警告。
四年親眼目睹,梁朝肅這個人一旦設立目標,那種堅定堅決,毫不含糊,一往無前,不達目的永不罷休的偏執兇狠,是獵最恐懼的那種兇。
他還有掌控,梁父這次他到絕境,唯一破局的方式,是放縱帶著孩子,離開他視線范圍。
Advertisement
以梁朝肅的自尊、為人,絕對難以容忍,所以他憋屈,氣惱,稍有苗頭,就催生他怒火,又不愿驚嚇到,讓產生懷疑,一時不跑了。
連城猜他真正之意,是不管聽不聽懂,他不重復,也不罷手。
“我聽懂了。”
連城仰頭他。
一向如此,幾次逃離下來,在梁朝肅眼中,必定是個有希就昂揚,在急關頭大膽,絕不順別人套路走的混蛋人。
眼下一言不接茬兒,反而不符合以往人設。
“風雪夜,長無一人的街道,人或多或環境影響,你是不是也覺得浪漫?想的自然就多,都想到孩子上去了。”
梁朝肅驀地停下腳步,撥開臉頰雪花,鼻尖雪化了,細細的水珠,淹沒了那顆小痣,他拇指一點一點抹掉,力道輕的不可思議,半晌重新找準那顆痣,珍重落下吻。
“確實浪漫。”
連城一哆嗦。
因為那個吻,也因為他今晚格外的神經。
梁朝肅是凌冽的,迫的,他適合步步相,風霜刀劍,不適合三分,兩分寵溺,人忍不住恐懼他剩下那五分,是否是狡詐,險,吞的人尸骨無存。
Advertisement
“雪夜浪漫,你是人間。”
連城面皮不自搐,胃里直沖一酸水到間。
雪是小浪漫,他是真間。
一句話打穿的防,心理抗拒尚且能忍,能演,生理抗拒實在無法抵擋,連城吐完一口,連忙用紙掉角,當做什麼都沒發生過。
梁朝肅眼底涼森森一片,格外幽邃,又仿佛一無形的東西,在沖擊他冷漠的軀殼,皸裂出隙,窺見他忍的晦暗、浪。
連城覺他隙里,要延出看不出的線,在孩子不足以為羈絆時,粘連,環繞,扎進皮,骨,連接的斬不斷。
“這枚玉扣是我親手刻的。”
他十指扣住連城右手,舉起來,手套扎進袖,過于嚴實,什麼都看不到,卻實實在在的存在,炙烤著。
“從靛省出差回來,并非沒有給你禮。”
連城全繃,只覺這樣的場面,比逃離被抓后,第一次見面,還難以應付。
料想,這就是梁朝肅剛才不點威脅‘大棒’后,跟的甜棗。
一張一弛,恩威并施,是他馭下,收復人的手段。
脈最難斬斷,卻表現的過于冷酷無。
人是敏思的,,親,友,都沾帶一個字,終生是命脈,梁朝肅抓不住后面兩個,挾住前一個,也算握住心臟。
讓老老實實留在他邊,滿足他旺盛野蠻的占有。
梁朝肅靜默幾息,等待問一句,手上的傷是否跟玉扣有關。
連城就如同這四年中的每一次,是角探測到危險的蝸牛,進殼里,一言不發,斂去伶俐,留給他一副僵麻木的表象。
梁朝肅目始終傾注在臉上,仿佛倒灌的黑沉海水,從詭譎莫測的神里傾覆而出,沖掉厚厚的抵抗,親會他的。
“這個孩子我盼了很久。”
還是為了孩子。
連城微不可察松懈,沒文化可以學,長得丑可以整,心眼壞是真的沒法治。
男人有時候實在是一種可笑的生,他們仿佛永遠學不會如同尊重他們自己一般,尊重異。
在他們心底,世界只有他們這一種別是人,只能歸為附屬品。
是孩時期欺負的玩,青春期追逐的獵,長大后這種追逐愈加愈烈,演變調教,改造,用,進一步用婚姻,合法合理的收獲一個奴隸。
猜你喜歡
-
完結1125 章
偏執薄爺又來偷心了
“再敢逃,我就毀了你!”“不逃不逃,我乖!” 薄煜城眼眸深邃,凝視著曾經試圖溜走的妖精,當即搞了兩本結婚證,“現在,如果你再敢非法逃離,我就用合法手段將你逮回來。” 女孩小雞啄米式點頭,薄爺自此寵妻成癮,護妻成魔。 但世間傳聞,薄太太癡傻愚笨、身世低賤、醜陋不堪,根本配不上薄爺的寵愛。 於是,全球的十億粉絲不高興了,“誰敢嗶嗶我們家女神?” 世界級的醫學研究院跳腳了,“誰眼瞎了看不上我們的繼承人?” 就連頂級豪門的時大少都震怒,“聽說有人敢瞧不起我們時家的千金?” 眾人問號臉,震驚地看著那被各大領域捧上神壇、身份尊貴的女孩。 薄爺旋即將老婆圈回懷裡,緋唇輕勾,“誰再敢惹我老婆……弄死算了。”
176.2萬字8 141276 -
完結49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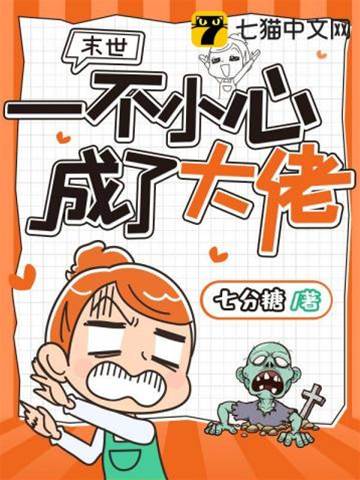
末世一不小心成了大佬
她在末世掙扎五年,殞命瞬間卻回到了末世剛開始,恰逢渣男正想推她擋喪尸。她踹飛喪尸,準備再掀一次渣男的天靈蓋!囤物資,打喪尸,救朋友,她重活一次,發誓一定不會讓任何遺憾再次發生。不過周圍的人怎麼都是大佬?殊不知在大佬們的眼里,她才是大佬中的大佬。
75.3萬字8 11226 -
完結2925 章

影后的嘴開過光
「江小白的嘴,害人的鬼」 大符師江白研製靈運符時被炸死,一睜眼就成了十八線小明星江小白,意外喜提「咒術」 之能。 好的不靈壞的靈?影后的嘴大約是開過光! 娛樂圈一眾人瑟瑟發抖——「影后,求別開口」
524.2萬字8 15366 -
完結486 章

離婚後,虐她上癮的京圈大佬腰酸了
閃婚一年,唐軼婂得知她的婚姻,就是一場裴暮靳為救“白月光”精心策劃的騙局。徹底心死,她毅然決然的送去一份離婚協議書。離婚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裴總離異,唯獨他本人矢口否認,按照裴總的原話就是“我們隻是吵架而已”。直到後來,有人告訴他,“裴總,您前妻要結婚了,新郎不是您,您知道嗎?”裴暮靳找到唐軼婂一把抓住她的手,“聽說你要結婚了?”唐軼婂冷眼相待,“裴總,一個合格的前任,應該像死了一樣,而不是動不動就詐屍。”裴暮靳靠近,舉止親密,“是嗎?可我不但要詐屍,還要詐到你床上去,看看哪個不要命的東西敢和我搶女人。”
86.8萬字8 3415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