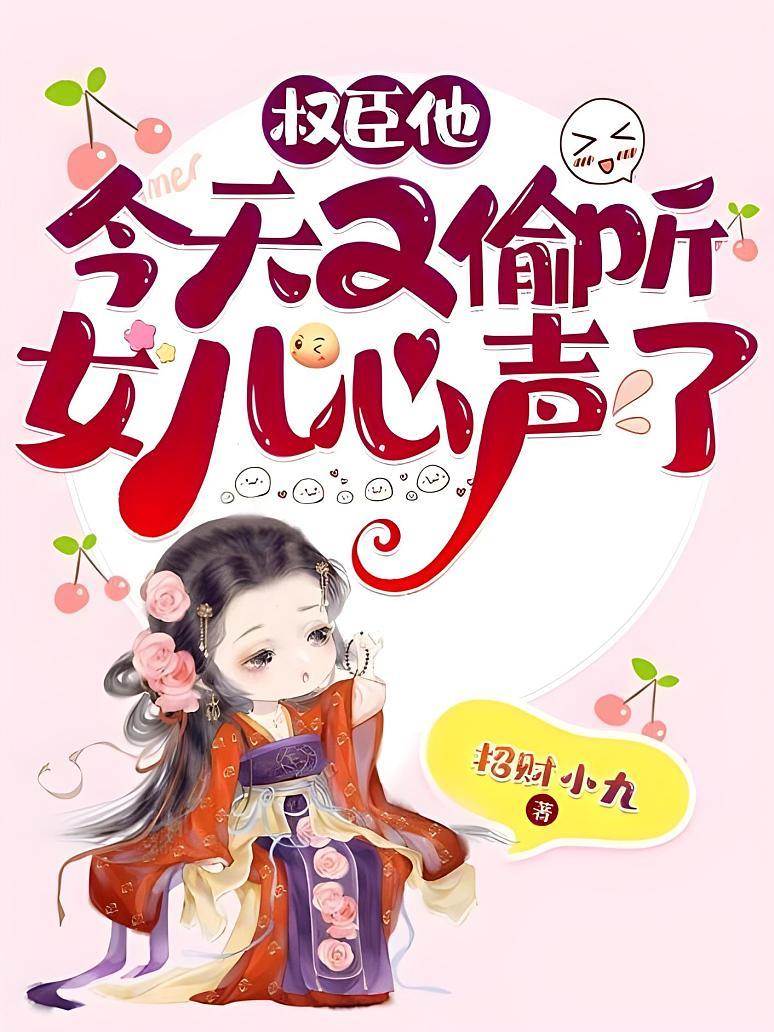《燈花笑》 第一百一十章 風雪來賓
陸瞳把油燈放到桌上,平靜道:“人還沒走遠,需要我將他們回來?”
他不置可否地一笑,瞥了小佛櫥前白玉觀音一眼,意有所指道:“你都是這麼騙人的,人前菩薩人後羅剎?”
陸瞳回敬:“人前天子近衛,人後宮中逃犯,裴大人與我也不過半斤八兩而已。”
可沒忘記,剛才申奉應說的是,宮中有刺客逃出來了。
陸瞳聞得見裴雲暎上極淡的腥氣,有些事不難猜出端倪。
裴雲暎怔了怔,隨即笑了,走到窗下桌前坐下,嘆道:“早知道陸大夫這麼厲害,先前就不得罪你了。”
陸瞳沒說話。
申奉應來搜查醫館時,因裴雲暎出來得匆忙,沒辦法,只能讓裴雲暎藏進寢屋裡那間堆滿了服的黃梨木櫃子後。
銀箏和另一間空房被鋪兵們搜得仔細,但申奉應因為之前那一次的關係,對陸瞳的閨房搜得倒是比較糙。
為了遮掩裴雲暎上那腥氣,故意與銀箏把幾隻大瓷缸推出來吸引申奉應注意。瓷缸裡的毒嚇了申奉應一跳,一驚一乍間,申奉應認定自己多想之下,反倒不會再繼續懷疑仁心醫館。
誠然,能順利矇混過關,也有裴雲暎自己藏得蔽的關係。
他見桌上有茶與乾淨的空杯,便自己手提壺斟茶,不過作比起之前些微遲滯,這變化很微小,但陸瞳立刻察覺到了。
陸瞳抬眼看他:“你傷了?”
裴雲暎倒茶作頓了頓,並未否認:“有藥嗎?”
陸瞳轉就走:“賣完了。”
對當活菩薩沒什麼興趣,尤其是對面前這個深夜不請自來的在逃刺客。今夜實在兇險,一個不小心,就要被裴雲暎連累,日後籌謀毀於一旦。
Advertisement
實在很難不遷怒。
“陸大夫。”裴雲暎坐在桌前,笑著喚,“你不是說,治病救人的時候,你就只是個大夫。”
“現在這個時辰,你應該還是大夫吧?”
陸瞳腳步一頓。
這是在文郡王府,替裴雲姝接生時說過的話。
那時候尚在生產中裴雲姝的掙扎與期令想到了陸,於是難得心了幾分,這心也連帶上了裴雲暎,為稍稍平他的焦躁,才說出這麼一句。
沒想到會在這時被裴雲暎提起。
沉默片刻,陸瞳走到屋中櫃子前,找出醫箱,從裡取出一隻藥瓶,走到裴雲暎跟前往桌上一頓。
“五十兩銀子。”
裴雲暎:“……”
他抬頭:“你這是坐地起價啊,陸大夫。”
“求醫問藥,明碼標價。”
“我以為你要向我討個人。”裴雲暎搖頭笑笑,好脾氣地從懷中掏出一張銀票放在桌上。
陸瞳接過銀票,一百兩銀子的銀票,這人倒是很大方。
從匣子裡取來銅稱,稱了把散碎的銀兩,湊齊五十兩還給裴雲暎,語氣平淡無波:“殿帥的人不太值錢,不如銀子實在。”
裴雲暎著桌上那把碎銀,沉默一刻,評點:“陸大夫很是務實。”
陸瞳站在桌前,蹙眉看著他,再次提醒:“外面人已經走了,殿帥什麼時候離開?”
裴雲暎“嘶”了一聲,認真開口:“眼下你我在他們眼裡是同夥,出去撞上人,陸大夫也逃不了。還是再等等。”
他語氣隨意,彷彿與陸瞳間有很深的一般,毫不見外,卻讓陸瞳心中登時騰起一層薄怒。
因自己所行之事蔽,陸瞳一向不與人過分牽連,當初夏蓉蓉住進小院,都想法子讓夏蓉蓉搬離出去。
Advertisement
偏裴雲暎如今進了的寢屋,還不知要逗留到幾時。
這人明明心機深沉,卻總能找到最無辜的理由,義正嚴辭的模樣看著就讓人生氣。
陸瞳按捺住心中冷意,走到另一邊榻邊椅子上坐下。
院中風雪夜寒冷,屋中如春溫暖,北風攜卷大雪從窗前經過,可見漫天碎玉飛瓊,屋中人卻在花窗上投下剪燭斟茶的暖暗影。
靜謐而溫。
陸瞳看向他。
他坐在窗前,低頭喝茶,不笑時有些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漠,一漆黑箭乾淨利落,在燈火下出些濡溼的痕跡。
似是察覺到陸瞳目,他轉過頭,微微一笑,於是剛剛的漠然倏爾散去,彷彿只是錯覺。
他問:“怎麼這樣看著我?”
陸瞳靜了片刻,漠然提醒:“不上藥嗎?”
裴雲暎一黑,無法看清上傷痕。但陸瞳能聞見他上的腥氣越來越濃烈,這意味著他上的傷口在不斷往外滲出跡。
沒有在屋子裡薰香的習慣,如果申奉應突然帶領鋪兵們殺個回馬槍,都不必搜捕,這屋中的腥之氣就會出賣裴雲暎的行蹤。
裴雲暎要是死在這裡,還得負責理,很是麻煩。
最好別死,死也別死在這裡。
裴雲暎不知陸瞳心中思慮,只拿起桌上藥瓶,藥瓶不大,瓶緻,他拔掉塞子,猶豫一下,灑在肩上。
陸瞳:“……”
蹙眉:“你上藥隔著服?”
行醫這些年,陸瞳不曾見過有人這樣上藥。裴雲暎這幅遮遮擋擋的模樣,不知道的會以為他在下毒。
裴雲暎作一頓,道:“你屋子太小。”
“那又如何?殿帥上藥還要跑著上不?”
裴雲暎噎了一噎。
Advertisement
半晌,他向陸瞳,提醒:“我在你寢屋上藥,陸大夫不怕有損閨譽?”
“別忘了,你還有個未婚夫。”
他故意咬重“未婚夫”三字。
陸瞳皺眉看著他。
沒想到裴雲暎想得這般瑣碎,忽而又想起在遇仙樓時,為避戚玉臺懷疑主抱裴雲暎,裴雲暎微微僵的,和刻意拉開的距離。
思及此,陸瞳的語氣裡就帶了一諷刺:“裴大人多慮。”
“在我眼裡,你和當初埋在樹下的半塊豬沒有任何區別。”
裴雲暎:“……”
他平靜朝陸瞳看去,陸瞳神冷淡,以至於讓人難以分辨這話是認真還是在玩笑。
昏暗燈下,二人對視良久。
過了一會兒,裴雲暎低頭,看著面前的茶盞,淡淡開口:“你說話真難聽。”
陸瞳心中冷笑。
這位昭寧公世子大半夜被滿城追查,以此人手段,未必找不到辦法,偏偏闖進仁心醫館躲避追兵。很難讓人不懷疑他是故意的。
裴雲暎就是故意拉一道下水,或許是出自他某種惡劣的趣味。
既然他們已看穿彼此的虛偽與假象,就沒必要在表面上裝作客氣與禮貌。現在是不能將裴雲暎怎麼樣,可能讓這人心裡不痛快一點,也好過什麼都不做。
陸瞳懶得掩飾自己的冷漠與不耐。
許是因為陸瞳那句拿他與豬相比的諷刺,再遲疑下去反坐實了他忸怩,裴雲暎不再踟躕,手撕開肩頭被利劃開的料。
料撕開的瞬間,裴雲暎皺了下眉。
陸瞳抬眸看去。
目所及,這人右肩至小半個背部鮮淋漓,像是箭傷。不見箭勾,只有翻起的皮,看著就目驚心。
陸瞳心中暗忖,帶著這樣的傷口,此人還能談笑風生,裴雲暎的忍倒是比想象中更強。
他拿起桌上藥瓶,像是要灑上去,忽又覺得似乎太潦草了些,遂問陸瞳:“有水和帕子嗎?”
陸瞳點頭:“有。”
似是沒料到這次這樣好說話,裴雲暎愣了愣,隨即笑道:“多謝……”
下一刻,陸瞳打斷了他的道謝。
“加銀子就行。”
裴雲暎:“……”
陸瞳起,找到銀水壺,找到花架上的木盆,往裡倒了些熱水。又找了方乾淨帕子浸在其中,端著熱水走到裴雲暎跟前,把木盆放到桌上。
裴雲暎看了看眼前的熱水,想了想,把剛才陸瞳還給他的五十兩碎銀往陸瞳面前一推。
“夠嗎?”
陸瞳把銀子收起來,重新放回匣子裡裝好:“勉強。”
他搖頭笑笑,沒計較陸瞳坐地起價,手拿起水盆裡的手帕,擰去多餘的水。
手帕是子的款式,淺藍的帕子,上面繡了木槿花枝,子手帕常灑香,或是薰香,這帕子卻只帶淡淡藥草味,與陸瞳上的清苦藥香如出一轍。
裴雲暎握住手帕,反手拭肩上的傷痕。
跡被一點點拭淨,出猙獰的傷痕。陸瞳看得清楚,箭傷從斜後方向上,他應當是背後中了箭。
裴雲暎完傷口,放下手帕,拿起藥瓶往肩上灑藥。他一隻手不太方便,藥一半灑到傷口上,還有一半灑到了地上。
陸瞳倚著桌沿,冷眼瞧著他作,突然開口:“暴殄天。”
裴雲暎:“……”
他又好氣又好笑,道:“陸大夫,你我雖然算不上朋友,至也是人。”
“這樣對一個傷的人,不太好吧。”
窗外風雪漸濃,朔風將窗戶吹得更開了一些,簷瓦上漸漸積起一層白霜。過燈籠微弱的暗,可見滿院大雪飛舞。
屋中搖曳的燈下,窗下人影朦朧。一朵雪花順著窗隙飄進裡屋,落在人束起的髮梢,很快消失不見。
陸瞳起,走到裴雲暎後,奪過他手中藥瓶。
裴雲暎一怔。
陸瞳平靜道:“傷藥很貴,你再浪費,就只能另付五十兩再買一瓶。”
裴雲暎手中所持傷藥,原料雖不貴重,製作起來卻也十足麻煩。
一向見不得旁人糟蹋藥。
裴雲暎聞言,這回倒沒說什麼,只轉過頭笑笑:“有勞陸大夫。”
陸瞳站在裴雲暎後,他肩很寬,箭穿在上,勾勒足夠漂亮的型。目所及並不似那些白瘦文弱的公子,許是因常年練武的關係,理勻稱,蘊藏力量。
陸瞳一隻手扶上他肩頭。
裴雲暎子微僵。
下一刻,陸瞳一揚手,“撕拉——”一聲,面前本就撕開的黑被扯了大塊下來,連帶著被黏在一起的皮。
裴雲暎倒吸一口涼氣。
“一點小傷。”陸瞳拿起藥瓶,均勻灑在他傷口,“殿帥何苦大驚小怪。”
裴雲暎回頭,擰眉著陸瞳:“陸大夫這是公報私仇?”
“怎麼會?”陸瞳塞好瓶塞,將藥瓶放到裴雲暎掌心,微微笑道:“上藥總會有點痛,裴大人切勿諱疾忌醫。”
裴雲暎定定盯著半晌,過了一會兒,自嘲般點頭:“好吧,陸大夫說了算。”
陸瞳眸微。
故意下重手讓裴雲暎吃痛,這人卻還能和悅與說話,養氣功夫倒是一流。
上過傷藥還得包紮,陸瞳從箱裡剪了包紮用的白帛,走到裴雲暎後替他包紮。
裴雲暎似乎很抗拒與人過於親接,有意無意微微拉開距離,倒是陸瞳並無此擔憂,手繞過裴雲暎肩臂,從後替他練包裹。
說起來,裴雲暎肩頭傷口不算太深,然而肩頭往下背部一部分另有一道猙獰刀痕,應當是舊傷。新傷舊傷添在一起,應當很難忍耐,但今夜自始自終,裴雲暎都沒出一半點痛楚之。
或許是因為這點傷對他來說不算什麼,又或許,只是他能忍罷了。
陸瞳剪去包紮好的白帛邊緣,順口問:“這裡曾有舊傷?”
裴雲暎頓了頓,道:“是啊。”
陸瞳瞥一眼那道陳舊的刀痕,刀痕極深,不知被什麼人過傷口,然而得七八糟,簡直像是時的紅,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歪歪斜斜,烙印在裴雲暎背後,像一道稽的暗紅墨痕。
道:“像仇人為你的。”
能將人傷口如此模樣,簡直像是故意的。
裴雲暎聞言,像是想起了什麼,角梨渦越發明顯,“算是吧。大夫是個小姑娘,剛從醫不久,醫是不如你,不過報復心倒是和你一樣強。”
桌上油燈快要燃盡,陸瞳起從櫃子裡取出另一盞,邊倒進燈油,邊開口:“你做了什麼,要報復你?”
裴雲暎想了想:“也沒什麼,幾年前我在蘇南被人追殺傷,躲進刑場後的死人堆裡。在那裡,遇到一個的小賊。”
“救了我,給我治傷,不過不太願。”
陸瞳一怔,手上燈油倒進,卻忘記用火石點燃。
一瞬電石火,往事衝破重重雪幕撲面而來,有遙遠畫面自面前浮起,將紛紛雪映亮。
裴雲暎並無所覺,抬眸看向窗外。
盛京風雪夜,窗前一點微弱燈火照得外頭飛雪綿綿,簷上地下妝銀砌,天地一片茫茫,竟生孤寂空涼之。
他的聲音也如雪一般輕寂。
“說起來,遇見那天,也下了一場雪。”
像是為了映襯他說得那般,院中簌簌雪粒順著窗隙飛到桌前,白霜落進花燈,盪出一點泛著冷氣的漣漪。
他轉向陸瞳,笑著開口。
“那可是蘇南十年難遇的大雪。”
陸瞳猝然抬眼。
剎那間,雪花覆住燈芯,最後一點微晃了晃。
燭火熄滅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45 章

火鳳凰
穿越醒來,被X了?而且肚子里還多了一個球?一塊可權傾天下的玉佩掀起亂世風云,太后寵她無度目的不明,皇帝百般呵護目標不清,庶妹為搶她未婚夫狠毒陷害毀她清白?那她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她堂堂影后又是醫學世家的傳人,更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特工身份,她…
73.9萬字8 71033 -
完結275 章

首輔大人的小青梅[重生]
【嬌軟小青梅x表面如圭如璋,實則心狠手辣的未來首輔】 【女主篇】:阿黎九歲那年,隔壁來了位身受重傷的小郎君。小郎君生得眉目如畫、俊美無儔,阿黎偷偷喜歡了許久。十四歲那年,聽說小郎君被人“拋棄”了。阿黎壯著膽子跑去隔壁,對霍珏道:“你別傷心,她不要你,我要的。”話落,她被霍珏丟出門外。明媚春光下,小郎君看她的眼神比開陽湖的冰垛子還冷。姜黎委屈巴巴地走了,沒兩日又抱著個錢袋上門。只是這一次,門後的小郎君卻像是換了個人。他靜靜看著她,深深沉沉的目光彷彿邁過了漫長時光沉沉壓在她身上。良久。他勾住阿黎肩上的一綹發,素來冷漠的眉眼漾起淡淡的笑,柔聲問她:“阿黎那日的話可還算數?”阿黎:“算,算的。”阿黎一直覺著霍珏是自己追回來的。直到後來,她翻開一本舊書冊,裡頭藏了無數張小像:九歲的阿黎、十歲的阿黎、十一歲的阿黎……一筆一畫,入目皆是她。阿黎才恍然驚覺。或許,在她不曾覺察的過往裡,霍珏也偷偷喜歡了她許久許久。 【男主篇】:霍珏身負血海深仇。上一世,他是權傾朝野的權宦,眼見著仇人一個個倒下,大仇終於得報,可他卻後悔了。他只想找回那個在他淨身後仍一遍遍跑來皇宮要將他贖出去的少女。再一睜眼,霍珏回到了十六歲那年。門外,少女揣著銀袋,眨巴著一雙濕漉漉的眼,惴惴不安地望著他。霍珏呼吸微微一頓,心口像是被熱血燙過,赤赤地疼。指尖輕抖,他開口喃了聲:“阿黎。”從不敢想。踏遍屍山血海後,那個在漫長時光裡被他弄丟的阿黎,真的回來了。 【小劇場】:某日霍小團子進書房找他爹,卻見他那位首輔爹正拿著根繡花針補衣裳。小團子一臉驚恐。他爹一臉鎮定:“莫跟你娘說。你那小荷包是你娘給你新做的吧,拿過來,爹給你補補,線頭鬆了。”後來,長大後的小團子也拿起了繡花針。只因他爹下了命令,不能讓他娘發現她做的衣裳第二天就會破。小團子兩眼淚汪汪:長大成人的代價為何如此沉重?嘶,又紮手了。
43萬字8.33 95745 -
完結3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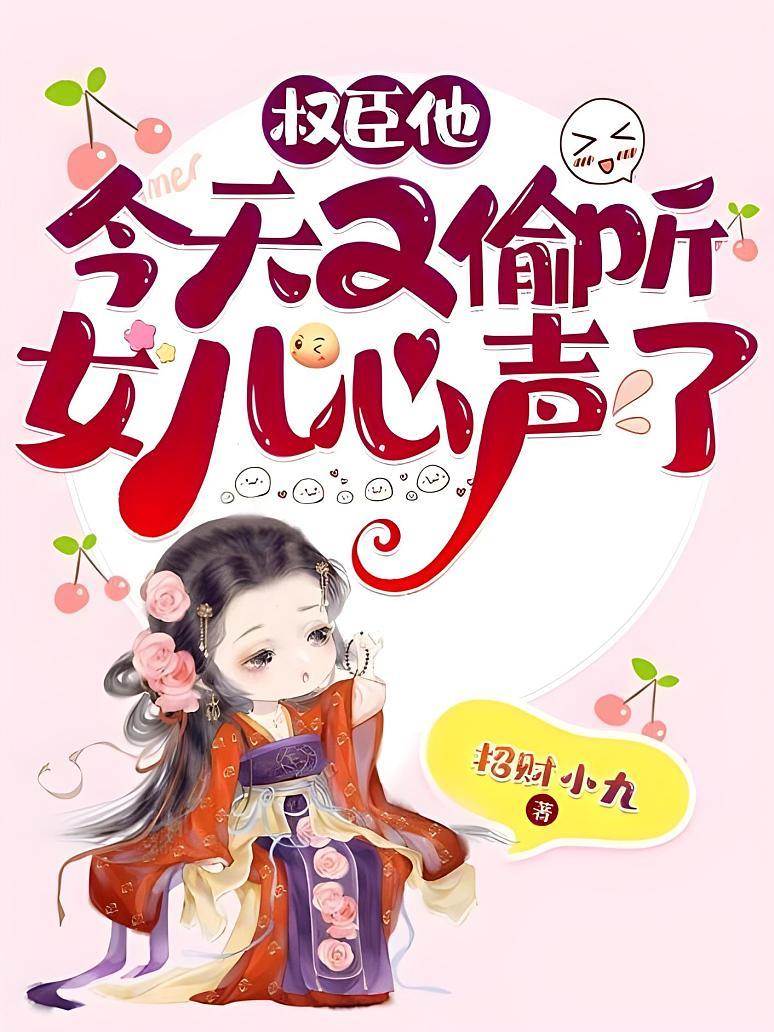
權臣他今天又偷聽女兒心聲了
樓茵茵本是一個天賦異稟的玄學大佬,誰知道倒霉催的被雷給劈了,再睜開眼,發現自己不僅穿書了,還特喵的穿成了一個剛出生的古代嬰兒! 還拿了給女主當墊腳石的炮灰劇本! 媽的!好想再死一死! 等等, 軟包子的美人娘親怎麼突然站起來了? 大奸臣爹爹你沒必要帶我去上班吧?真的沒必要! 還有我那幾位哥哥? 說好的調皮搗蛋做炮灰呢? 怎麼一個兩個的都開始發瘋圖強了? 樓茵茵心里犯嘀咕:不對勁,真的不對勁!我全家不會是重生的吧? 樓茵茵全家:重生是啥?茵茵寶貝又爆新詞兒了,快拿小本本記下來!
69.1萬字8.18 148 -
完結256 章

如果賤婢想爬墻/替身男主:霸道丫鬟必須愛
大公子高大威猛,已有妻室,是個有婦之夫。 二公子心狠手辣,滿眼陰戾,是個不好惹的病秧子。 只有三公子溫潤如玉,文采斐然,是萬千少女的一場美夢。 爲了成功從丫鬟升級爲三公子的頭號小妾,寶嫿想盡一切辦法勾搭主子。 終於某天寶嫿趁虛而入,從此每天快樂得迷醉在三公子身邊。 直到有天晚上,寶嫿難得點了蠟燭,看見二公子敞着領口露出白璧一般的肌膚,陰森森地望着自己。 二公子笑說:“喜歡你所看見的一切嗎?” 寶嫿轉頭朝河裏衝去。 後來寶嫿被人及時打撈上來。 二公子像每個讓她迷醉的晚上一般把玩着近乎奄奄一息的她的頭髮,在她耳邊溫柔問道:“說你愛誰?” 寶嫿結巴道:“二……二公子。” 二公子掐住她脖子森然笑說:“三心二意的東西,誰準你背叛我弟弟?” 寶嫿白着小臉發誓自己有生之年再也不勾搭主子了。 對於二公子來說,遇見寶嫿之後,沒有什麼能比做其他男人的替身更快樂了~
38.2萬字8 1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