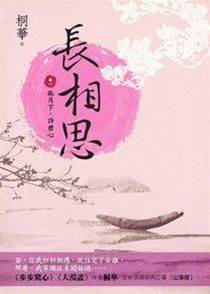《別院私逃後,瘋批權臣怒紅眼》 第139章 “晚晚該清楚,祖母幫不了你”
他聲線低暗,強行按住掙紮的作,牢牢將鎖在懷裏。
薑映晚被他弄得腰作痛,抬頭,忍不住想罵他,卻反被他抬著下頜強行抬起頭看他。
裴硯忱語氣並不重,隻是用最平常的語氣,跟說著最客觀的話。
“夫人自己應當清楚,祖母幫不了你。”
“與其費盡周折跑出府再被為夫親手抓回來,不如夫人自己乖一些。”
說著,他將攏在懷裏,不再看那雙冰冷的眸子,輕拍著的背,仿佛他們之間,什麽都沒有發生過。
沒有與別人談婚論嫁,沒有與旁的男子差一步就步大婚,沒有這一年的兩地分隔,隻是延續著京郊別院那時的短暫溫,繼續自欺欺人。
“夫人不喜歡石室,那我們以後不去了,婚前,夫人就宿在夫君這邊,還有,再有幾日,便是年底了,夫人可有想要的禮品?為夫親自去置辦。”
薑映晚沉沉閉了閉眼。
Advertisement
好一會兒,對他說:
“我不喜這裏,我回碧水閣。”
裴硯忱圈著的力道收,嚨艱滾,“寒冬天寒,我抱著夫人睡,能為夫人暖。”
這便是不同意了。
薑映晚聽得懂拒絕的意思。
沒應聲,片刻後,接著說出真正的目的。
“紫煙陪在我邊多年,如今乍然不在我邊,很是不習慣,你將調回來。”
如薑映晚所料,在搬去碧水閣的要求被拒絕後,讓紫煙回來的要求,他很快同意。
“既然夫人喜歡,為夫調回來便是。”
春蘭帶著人將膳食送了進來,裴硯忱看著薑映晚用完了膳,沒多久,段逾白過來,裴硯忱去書房和段逾白議事,
薑映晚則隨著過來尋的方嬤嬤一道去了紫藤院。
剛一進來廳堂,這次老夫人就屏退了左右的侍婢。
單獨喊薑映晚坐在邊,與說話。
“晚晚,你告訴祖母,方才想說的,是不是離京的話?”
Advertisement
薑映晚沉默片刻,裴硯忱沒來之前,確實是下意識想向老夫人求助。
但冷靜下來後,發現這法子並不妥。
如裴硯忱所說,本逃不掉。
當初他命外出、遠離皇城時,尚且無法從他手中逃掉,何況是再三逃跑被捉回,府中不知添了多暗衛日夜盯著舉的況下。
裴硯忱若不鬆口放離開,這輩子,怕是都不可能隨意這座府邸。
掩下眼底的黯,薑映晚搖著頭,說:
“謝祖母關懷,但我……應當出不去。”
“隻是晚晚,確有一事,想求祖母相助。”
老夫人長長歎息,握著的手,拍了拍手背,慈地說:
“跟祖母客氣什麽,想要什麽,盡管說。”
薑映晚心裏清楚,在裴硯忱那裏,可用來易的籌碼不多。
能將紫煙要回來,不代表也可以將李叔他們要過來。
如今被困裴府,雖悲愴哀涼,但不能不管為們薑家拿命奉獻了大半輩子的老人,也不能,置父母祖輩留下來的基業於不顧,將無數產業棄之腦後,白白看著薑家的家業斷送。
Advertisement
薑家克紹箕裘,不能斷在手裏。
“薑府有幾個忠心耿耿的舊仆,祖母可否幫晚晚暫時尋他們來京城?”
這種小事,老夫人自然不會拒絕。
“祖母立刻就安排下去,讓人去尋,晚晚且放心。”
老夫人拉著薑映晚說著話,說著說著,話題不注意轉到了容家上。
薑映晚傾心容時箐的事,老夫人知。
如今容時箐驟然被下獄的事,老夫人亦聽說了一二。
本想將這個話題掠過,但腦海中卻想起曾經這姑娘決心退掉兩家婚約、跟說早有心上人的那一幕。
老夫人心下歎息,到底是沒掠過這個話題,看著聽到容時箐這幾個字後,角抿垂眸不語的姑娘,主詢問:
“薑家舊案,和容時箐義父的事,祖母多聽說了一二,晚晚可想,去見一麵容時箐?”
薑映晚自然想去見一次容時箐。
鄧漳之事出的倉促荒謬。
從槐臨那晚就想親自找容時箐問清過往的一切。
鄧漳那些年接近們薑家,到底是不是大皇子指使。
還有父母的死,到底跟不跟他們有關。
四年前,鄧漳和父母先後離開鄴城,隨後不久,又接連雙雙傳來噩耗,又到底是不是巧合。
隻是裴硯忱極度不喜提容時箐這幾個字,每每還沒問出口,就被他製止。
聽到老夫人這樣問,薑映晚無疑是驚訝的,驀地抬頭,看向和藹看著的老夫人,“我確實想弄清真相,祖母能幫我嗎?”
老夫人拍了拍手背,作中帶著安。為過來人,太清楚,隻有徹底知道一切,才會有放下過往或釋懷的可能。
而一味躲避與瞞,隻會讓一切,為深埋於心底的一刺。
拔不出,忘不掉。
猜你喜歡
-
完結149 章
將軍家的小娘子
我的相公是侯府嫡子,國之棟樑.沈錦:我的相公不納妾.二姐:我的相公書香門第,家世清貴.沈錦:我的相公不納妾.四妹:我的相公有狀元之才,三元及第.沈錦:我的相公不納妾.五妹:我的相公俊美風流,溫柔體貼.沈錦:我的相公不納妾.
63.5萬字8 46452 -
完結195 章

半城風月
她來自鐘山之巔,披霜帶雪,清豔無雙,於"情"之一事,偏又沒什麼天賦,生平最喜不過清茶一杯,看看熱鬧. 都說她年少多舛,性格古怪,其實她也可以乖巧柔順,笑靨如花. 都說她毒舌刻薄,傲慢無禮,其實她也可以巧笑倩兮,溫柔可親. 不過—— 她·就·是·不·樂·意! 直到那天,她遇見了一個少年. 半城風月半城雪,她一生中的所有風景,都因他而輝煌了起來. …
42.6萬字8 4704 -
完結920 章
催妝
好兄弟為解除婚約而苦惱,端敬候府小侯爺宴輕醉酒後為好兄弟兩肋插刀,“不就是個女人嗎?我娶!”酒醒後他看著找上他的淩畫——悔的腸子都青了!淩畫十三歲敲登聞鼓告禦狀,舍得一身剮,將當朝太子太傅一族拉下馬,救活了整個淩氏,自此聞名京城。後來三年,她重整淩家,牢牢地將淩家攥在了手裏,再無人能撼動。宴輕每每提到都唏噓,這個女人,幸好他不娶。——最後,他娶了!------------------------宴輕:少年一捧清風豔,十裏芝蘭醉華庭淩畫:棲雲山染海棠色,堪折一株畫催妝
199.4萬字8 9283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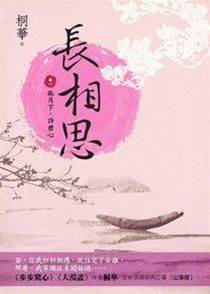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176 章

尚公主
某日修國史,論起丹陽公主與其駙馬、亦是當今宰相言尚的開始,史官請教公主府。 公主冷笑:“我與他之間,起初,不過是‘以下犯上’、‘以上欺下’的關係。” 宰相溫和而笑:“這話不用記入國史。” 宰相再回憶道:“起初……” 起初,丹陽公主暮晚搖前夫逝後,她前往嶺南養心,借住一鄉紳家中。 暮雨綿綿,雨絲如注,公主被讀書聲驚醒。 她撩帳,見俊美少年於窗下苦讀。雨水濛濛,少年眉若遠山遼闊。 公主看得怔忡,她搖扇,俯在他耳後提點他: “只是死記硬背,卻文理不通,氣勢不足不暢;家中無權無勢,你又不去交際。這般讀下去,再過十年,你科考也中不了。” 雨水叮咚下,少年仰頭,被她望得面紅之時,又欣慰這位公主可算做個人了。 得公主提點之恩,數年後,少年入朝堂。 之後尚公主,爲宰相,國士無雙。
98.7萬字8 151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