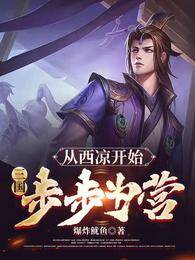《大宋好武夫》 第95章 狄詠,這是怎麼回事?
大理國使節,老人,楊義貞,還有幾個楊家老一輩的人隨同,以楊義貞為主,此來就是要討個公道,還要告狄詠的狀。
大理國與大宋,其實是有一定政治關系的,大理對大宋有時候會朝貢,卻又沒有到附屬國這種關系,但是大理又有“不通于中國”的潛在政策,意思就是各過各的。
大理國以前還表現過求冊封的意思,后來又沒有這種表態了,但歷史上幾十年后,大理國又求了冊封,徽宗還正兒八經給大理冊封了一次。
這個關系其實有些奇怪,卻也不那麼奇怪,主要還是大理太遠,又與大宋沒有實質的接壤,雖然名義上的國土有接壤,但接壤之地,都是所謂“蠻夷”之地,比如四川貴州那邊都是山區部落,廣西這邊的羈縻州,都把兩國事實的區隔開來。
所以在大宋看來,對大理是一種無所謂的態度。在大理看來,自己偏安一隅也好。
狄詠顯然就打破了這種略顯奇怪的關系,也顯得狄詠這一次攻昆明的舉顯得格外自作主張。
但轉過頭來想,這個既不是真正附屬國的大理,又與大宋沒什麼真正來往的大理,純屬泛泛之,就是路邊人,打了一仗,還是個勝仗,其實也沒有什麼那麼大的罪過。
皇帝趙禎頭前不太在意的態度,就是因為這種關系上的無所謂。不過若是狄詠打敗了,那問題就不一樣了。
如果狄詠是自作主張把已經和平了五十年的遼國給打了,那狄詠的問題就真的大了。
Advertisement
但其中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大義的問題,這一點雖然顯得虛偽,但儒家仁義大宋,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是在乎這種虛偽的,這也是所謂天朝上國的臉面。
滿朝文武在場,楊義貞宮而來,這一路上,也是楊義貞長見識的旅程,到得開封汴梁,更是讓他大開眼界,一百多萬人的城池,幾十里地的城池,一眼不到邊的城墻……
所謂八千里江山,眼見為實,大宋的富庶撲面而來,無不在這個年輕的小國二代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震撼。
宮來見皇帝,楊義貞已然不自覺有些戰戰兢兢,文武百聚集的眼神,也讓楊義貞多有些慌。
宮拜見的禮節自然有人教過他,倒也沒有什麼差錯,但是楊義貞開口要說的話語,那就與來之前想好的完全不一樣了。
出發之前,年輕熱的楊義貞義憤填膺地想了好多說辭,比如見到大宋皇帝,一定怒發沖冠質問宋人所作所為,一定要討一個公道,如若不然,還要說一些恐嚇之語,什麼大軍十萬寇邊,戰至一兵一卒,國不可辱,不死不休之類。
倒也不是楊義貞空想,幾十年來遼國使節就經常在大宋說這種話,楊義貞多多也聽過這一類的故事。
此時這些話,楊義貞是一句都沒有說出口,只道:“皇帝陛下,大宋乃仁義之國,我大理無罪啊,何故討伐?”
這一句話,便也是儒家大宋的肋,若是回答不上,那還得給人家大理國道歉。春秋戰國之時,楚國曾經也面對過隨國這麼一問,但楚國的回答是“我蠻夷也”,大宋顯然不能這麼答。
Advertisement
皇帝趙禎直接看向狄詠,意思是該你發揮了。
狄詠也不多等,幾步上前,走到高臺之下,與楊義貞站了個面對面,答道:“我大宋何曾討伐了你大理?若非大理窩藏賊首,我大宋之軍都不會越過千里路到得大理附近,若非爾大理國權柄紛爭,我麾下之軍也不會被人襲擊,以至于被反擊,若非高家人蠻不講理非要約戰,又豈有善闡府一戰?”
;楊義貞其實此時才剛剛看到狄詠,因為狄詠在不說話的時候,列班的位置一直在文武百末尾,在人群之中。
看到狄詠,楊義貞是怒火中燒,指著狄詠就道:“皇帝陛下,就是此人,就是此人出爾反爾言而無信,就是他占了我大理東京,把我家……國主驅趕而出……”
楊義貞這話里也有細節,本來是想說“我家皇帝陛下”,卻改了“國主”。這就是上下之別,在自己家里可以說皇帝,到大宋來就不能說皇帝了,皇帝一詞的分量就在這里。
皇帝趙禎自然得問:“狄詠,這是怎麼回事啊?”
狄詠說詞早已準備好:“陛下,此人口噴人,誰人不知大理段氏乃傀儡國主?誰人不知高楊兩家之勢大?段氏國主對家國之事哪里有一點主見之余地?那段氏國主是走是留,真的是因為國主所想?”
“此語何意?”趙禎還故作不解問了一句。
狄詠再答:“陛下,滿朝諸公,請看這大理國使節,他名楊義貞,乃至隨行而來之人,恐怕多是楊姓。若是諸位記得起,想必上一次大理使團,其中卻多是高姓。那段氏國主,不過是高楊兩家爭奪之鹿爾,誰得國主,誰便主政。那國主當真是驅趕而走?難道不是這楊家人奪了去?”
Advertisement
“你口噴人,你……胡說八道,若非你占了東京,國主豈能離京而走?”楊義貞指著狄詠大聲說道。
“是嗎?若真如此,那這事倒也好說,陛下,臣有一策,可解決大理之事!”狄詠稟告。
“說來!”皇帝趙禎倒是一副看戲的模樣,看著狄詠發揮。
“不若與這楊家約法三章,如若楊家人同意了,那這善闡府還給段氏又何妨?”狄詠挖坑了。
楊義貞聞言,果然有欣喜之,立馬答道:“別說約法三章,只要不割地,哪怕是賠些許銀錢糧餉,那也無妨。”
“好,這一章,爾等把段氏國主送回善闡府,爾楊氏不得朝為,只可在姚州主政。第二章,爾楊氏從此不得豢養超過三千兵馬,且楊氏兵馬從此不得臨近善闡府。第三章,爾楊氏兵馬從此聽段氏國主宣調,不得違背。有此三章,善闡府立馬歸還段氏。如何?”
狄詠說完話語,眼神掃視全場,這表演就是給在場所有人看的。
但是全場之人的眼神卻都看向了楊義貞,對于大宋的臣子而言,這三章哪里作事?家國都淪喪了,就這麼三點可以換回淪喪土地,不說為國為民什麼的,就一個忠字當頭,為臣子,那也得納頭便拜!
卻是楊義貞面微白,久久不語,還左右去看隨行之人,顯然是不知如何是好,慌之間,卻答:“我如何知你說話算話?”
“哼哼……”狄詠斜眼看去,又道:“我大宋皇帝陛下在此,可訂國書,但凡你楊家做得到,把段氏國主送來,大軍立馬退出大理國。若是違背,來日我大宋占有大義,必興大軍再討,如何?”
楊義貞心中所想,這皇帝肯定是不能送走的,更不能答應這種條件,且不說他自己的野心,就說還有一個仇敵高家在側,也萬萬不能這麼做,否則死無葬之地。
猜你喜歡
-
連載26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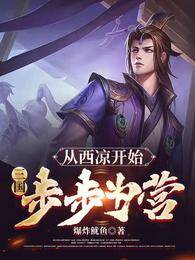
三國:從西涼開始,步步為營
無系統沒有金手指種田文權謀文穿越漢末,依靠領先千年的智慧,廣開田,練精兵。。當群雄還在強征兵丁,他已經精兵無數。當別人的武將還在為一匹赤兔馬互相爭搶,他已經組建數萬赤兔馬軍團。當諸侯還在為錢糧發愁之時,他正在洗劫天下。步步為營,一路橫推,從此再無三國。
384.2萬字8.18 60798 -
完結663 章
少年無雙
天漢八年,冬至時分,北風朔朔,北奴王親帥大軍十萬,攻破雁門關。燕州塗炭,狼煙四起,屍橫遍野,十室九空,骸骨遍地!王命數十道,無一藩王奉昭勤王。龍漢岌岌可危!京師城外,紅衣勝火,白馬金戈。少年立馬燕水河畔,麒麟細甲,精鋼鐵面。長柄金戈,直指長空,目光如炬,視死如歸!一戈破甲八千,五千紅甲盡出行,七萬北奴留屍關中。見龍卸甲,少年歸來。從此龍漢少了一位神勇天將軍,多了一位少年書聖人。
92.6萬字8 90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