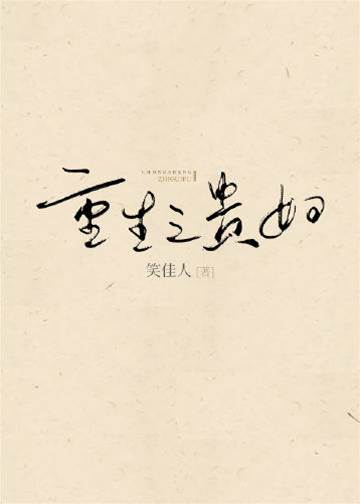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為撮合夫君和他白月光》 第229頁
沈這時沉著臉走上前去,在宮人退讓開後便一把住的面頰,讓疼得眼淚幾乎都瞬間要湧出來。
發覺他眸翳,霎時出些許驚恐,終於停止胡鬧安靜下來後。
沈低下頭,沉聲說道:「你若不喝,這張倒不如直接用針起來,橫豎都用不到了。」
「屆時上養出了針眼,便著人從針眼裡灌進去。」
臉霎時微微發白,仿佛邊上已經到被針出的可怕,連忙驚恐道:「我喝就是了。」
然後才當著天子的面捧起白瓷碗將符水給喝了個乾淨。
只等天子冷著臉離開後,宮人便瞧見虞婕妤淚眼汪汪地趴在了桌旁,面頰被掐過的地方疼的不行。
「他……他也太用力了。」
繃的緒退散後,疼的滋味便地從兩頰浮現。
宮人神複雜地打量著。
這宮人是為數不多做事本分從沈府一起進宮來的。
不管是在沈府還是在宮裡頭,陛下生氣或是不生氣,都不知掐過婕妤多次面頰,可一次都沒有弄疼過。
Advertisement
反倒是一要落淚,陛下再怒也都會收回手。
待婕妤真落了淚,他也會用瓣將淚珠含去。
哪怕兩個人鬧矛盾時,也好似調丨一般,陛下總會惹得婕妤面紅耳赤,接著便要揮退下人才能收場。
可現在,宮人看著婕妤面頰浮起的青指痕,不知陛下是因何失去了那份憐香惜玉,還是因何而生出了遷怒。
好似若不是婕妤上還有什麼讓他忍的地方,縱使將直接弄死,他也一樣會面不改。
翌日知虞面頰還疼,不想吃早膳。
宮人傳話到天子那裡,對方似乎也沒什麼要過問的意思。
只讓人冷聲傳話警告:婕妤若是將那子瘦了,陛下縱使不會傷到的,也一樣會有其他千百種手段磋磨。
換旁人也許只是口頭恫嚇,但換陛下裡說出來的,那就多半是真的了。
知虞自是清楚他的手段,哪裡還敢任,於是宮人送來什麼,便吃什麼。
符水似乎沒什麼效果。
耽擱兩日後,錢道長在古籍中終於又找到了新的方法。
Advertisement
「書中說,有一種火陣可以達到陛下想要的效果。」
宮裡這幾日烏煙瘴氣,都是這錢道長弄出來的靜。
但天子默許他如此,旁人自然也不敢多說什麼。
沈聽他提出這新主意後,便令春喜配合他布置這一切。
知虞這日剛用過膳,便被帶來了外面一片空地上。
聽到錢道長要赤腳走過那火陣,以達到驅除邪祟的效果。
「陛下,我真的不是什麼鬼怪邪祟……」
這樣說的時候顯然都不知,眼前的新君寧願裡是個鬼。
一旁侍春喜上前解釋道:「婕妤莫怕,陛下也都是為了婕妤好,您走的時候,也許擺和腳底都會被火燎到,但只要到了火陣那一頭,便有水桶會立馬幫忙滅火。」
死是定然不會死的,但腳上上會被火灼燒,留下疤痕也都是必然。
「只要經過這麼一遭,陛下便會徹底相信婕妤裡沒有邪祟,否則……」
總之在這春喜的一番勸導威脅下,紅了眼眶問:「只要這樣做,陛下往後就再也不會懷疑了是嗎?」
Advertisement
春喜笑說「是」。
便被迫服帖下來般,被宮人給攙扶過去。
一旁錢道長仍捧著一本爛書,對著沈細細解說。
「此法草民也已經問過了自家的師兄和師叔們了,十個裡面,說有五六個能好,只要是想要奪取他人魂魄的鬼侵,就算不清理乾淨,也能讓它重創……」
沈的目卻落在不遠的背影上。
看著被那宮人牽到了火陣前。
宮人似乎說了許多寬的話,便攥了側的手,似乎真要豁出去時,沈便語氣淡淡地吩咐道:「夠了——」
下一刻,便有侍衛提著手裡的水桶上前去將那火陣給澆滅。
知虞便二話不說將鞋子穿上,被那些宮人攙扶回去。
錢道長略有些驚訝,那可是他布置了一上午的火陣,往裡面可撒了不耗錢的寶貝。
「陛下這是何意?」
他面前的天子徐徐開口問道:「可有將鬼留下,驅除原主的法子?」
錢道長立馬傻眼了。
「這……這法子就算有,那也是邪魔歪道……」
男人黑眸沉凝,語氣冰冷地一字一句道:「倘若,我要的就是邪魔歪道呢。」
錢道長頓時瞠目結舌,磕磕絆絆地跪倒在地上,「這……這真沒有啊陛下……」
「草民雖然秉不正,可道觀是至純至正的道觀,老祖宗流傳下來的東西也只會驅邪,絕無聚邪……」
「那其他道觀呢?」
「普天之下,怎麼會有道觀會庇佑邪……」
錢道長還要反駁,可下一刻,話就堵在了嗓子眼裡。
一滴猩濃的滴答地落在了地面。
他跪趴在地上的視線漸漸上移,便瞧見天子手裡的茶盞不知何時被碎。
碎片扎掌心,男人仿佛都毫無痛覺。
只是目不轉睛地盯著錢道長,「你再想想。」
猜你喜歡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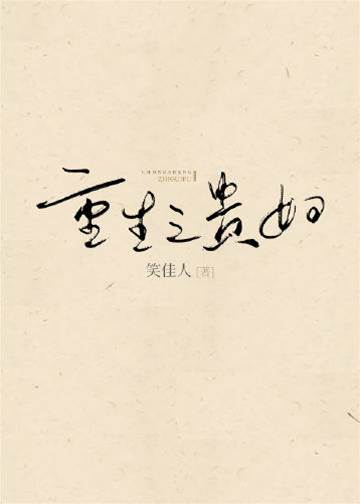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828 章

我是旺夫命
一朝穿越,鐘璃不幸變成了莫家村聞名內外的寡婦,家徒四壁一地雞毛也就罷了,婆婆惡毒小姑子狠心嫂子算計也能忍,可是誰要是敢欺負我男人,那絕對是忍無可忍!我男人是傻子?鐘璃怒起:這叫大智若愚!他除了長得好看一無是處?鐘璃冷笑:有本事你也那麼長。鐘…
170.9萬字8 233467 -
完結149 章

開封府美食探案錄
開封府來了位擅長食療的女大夫,煎炒烹炸蒸煮涮,跌打損傷病倒癱,飯到病除!眾人狂喜:“家人再也不用擔心我的身體!”但聞香識人,分辨痕跡……大夫您究竟還有多少驚喜是我們不知道的?新晉大夫馬冰表示:“一切為了生存。”而軍巡使謝鈺卻發現,隨著對方的…
45.8萬字8 13472 -
完結930 章

毒醫狂妃:誤惹腹黑九王爺
傳聞,相府嫡長女容貌盡毀,淪為廢材。 當眾人看見一襲黑色裙裳,面貌精緻、氣勢輕狂的女子出現時——這叫毀容?那她們這張臉,豈不是丑得不用要了?身為煉藥師,一次還晉陞好幾階,你管這叫廢材?那他們是什麼,廢人???某日,俊美如神邸的男人執起女子的手,墨眸掃向眾人,語氣清冷又寵溺:「本王的王妃秉性嬌弱,各位多擔著些」 眾人想起先前同時吊打幾個實力高深的老祖的女子——真是神特麼的秉性嬌弱!
153.2萬字8 334465 -
完結371 章

惑君
嫡姐嫁到衛國公府,一連三年無所出,鬱郁成疾。 庶出的阿縈低眉順眼,隨着幾位嫡出的姊妹入府爲嫡姐侍疾。 嫡姐溫柔可親,勸說阿縈給丈夫做妾,姊妹共侍一夫,並許以重利。 爲了弟弟前程,阿縈咬牙應了。 哪知夜裏飲下嫡姐賞的果子酒,卻倒在床上神志不清,渾身似火燒灼。 恍惚間瞧見高大俊朗的姐夫負手立於床榻邊,神色淡漠而譏諷地看着她,擡手揮落了帳子。 …… 當晚阿縈便做了個夢。 夢中嫡姐面善心毒,將親妹妹送上了丈夫的床榻——大周朝最年輕的權臣衛國公來借腹生子,在嫡姐的哄騙與脅迫下,阿縈答應幫她生下國公府世子來固寵。 不久之後她果真成功懷有身孕,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嫡姐抱着懷中的男娃終於露出了猙獰的真面目。 可憐的阿縈孩子被奪,鬱鬱而終,衛國公卻很快又納美妾,不光鬥倒了嫡姐被扶正,還圖謀要將她的一雙寶貝兒女養廢…… 倏然自夢中驚醒,一切不該發生的都已發生了,看着身邊沉睡着的成熟俊美的男人,阿縈面色慘白。 不甘心就這般不明不白地死去,待男人穿好衣衫漠然離去時,阿縈一咬牙,柔若無骨的小手勾住了男人的衣帶。 “姐夫……” 嗓音沙啞綿軟,梨花帶雨地小聲嗚咽,“你,你別走,阿縈怕。” 後來嫡姐飲鴆自盡,嫡母罪行昭彰天下,已成爲衛國公夫人的阿縈再也不必刻意討好誰,哄好了剛出生的兒子哄女兒。 形單影隻的丈夫立在軒窗下看着母慈子孝的三人,幽幽嘆道:“阿縈,今夜你還要趕我走嗎?”
61.6萬字8 10053 -
完結136 章

重生之窈窈再愛我一次
謝令窈與江時祁十年結發夫妻,從相敬如賓到相看兩厭只用了三年,剩下七年只剩下無盡的冷漠與無視。在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兒子的疏離、婆母的苛待、忠仆的死亡后,她心如死灰,任由一汪池水帶走了自己的性命。 不想再次醒來卻發現自己回到了十七歲還未來得及嫁給江時祁的那年,既然上天重新給了她一次機會,她定要選擇一條不一樣的路,不去與江時祁做兩世的怨偶! 可重來一次,她發現有好些事與她記憶中的仿佛不一樣,她以為厭她怨她的男人似乎愛她入骨。 PS:前世不長嘴的兩人,今生渾身都是嘴。
27.1萬字8 26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