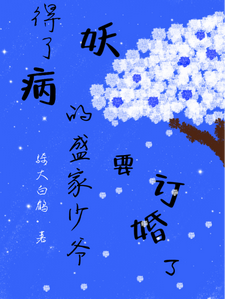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天降竹馬他最撩啦》 第202章 我來找我兒子
終于忙完下班,已經正中午了,鄭卓了把頭上的汗,在食堂領了吃了午飯,跟著工人們一塊走出學校。
他上了一輛公車,有幾個空座位,他沒坐,在下車門旁邊扶著欄桿站著。
車子啟一會兒,旁邊一個年輕士站起來問他:“您坐這兒吧。”
鄭卓搖搖頭,眼睛被帽檐遮擋,下半張臉出一個憨厚的笑,松弛的皮出好幾條褶子,“謝謝,沒事,我會把座位弄臟。”
士又坐回去了。
公車到站,鄭卓手背在后,慢悠悠的下車。
他哼著一首山歌,跟隨人流走進一條人聲鼎沸的巷弄,沒多久,在一個三層小木屋前停下,抬頭看了眼牌匾——陶氏木刻。
門戶大開,正在迎客。
前臺有個戴黑框眼鏡的年輕人坐在搖椅上看電視,鄭卓走進去,門口立馬響起一陣風鈴聲,年輕人立馬從搖椅上起來,看著鄭卓,招呼了句:“大爺,買什麼。”
大爺。
鄭卓心里哼笑了聲,也是,他鬢角皆白,公車上還有人給他讓座呢。
他把頭上破舊的棒球帽取了下來,放在玻璃柜臺上,“我不買東西,我來找我兒子。”
他說。
陶興一愣。
五分鐘后,陶興表復雜又尷尬的敲響了閣樓的門,對走出來的阮愈一指樓下,“阿阮,那個,有人找你。”
Advertisement
“誰。”阮愈言簡意賅。
“他說……他是你爸。”
陶興暫時關了店門,看著客廳里對峙的兩個人,尷尬的撓了撓頭,“我去沏茶。”
封閉的空間里就剩下他們兩個。
鄭卓站直了腰,上上下下的打量著眼前的年,目驚嘆的像在打量一件藝品。
“你簡直是米開朗基羅都雕刻不出來的作品。”半晌,他真誠的開口。
這句話從一個看起來風燭殘年的老人里說出來過于不搭。
阮愈也在打量他,說不清的燥郁又開始在他眉間凝聚,他吐出兩個字:“鄭卓?”
阮愈知道當年的事,知道自己的生父是個邪.教分子外加殺人犯被自己的生母舉報去獄里呆了十七年。
也是他被扔走的源。
這麼算下來也是,兩年前他就出獄了。
鄭卓點點頭,他的聲音不再是為了不引人注意而故意卡著嗓子的嘎,而是渾厚的甚至還有些溫良的屬于中年人聲線。他激的看著他,眼中甚至有淚:“你長這麼大了。”
阮愈看著他忽然笑了一下,眼底倒還是一片淡漠,“裝了,真這麼激兩年前就來找我了。”
鄭卓用手背了眼淚,“不不不,你誤會我了,我去年才知道你的存在,我一直不來找你是因為不好意思空手就來見你,我用一年的時候給你準備了見面禮,最近才準備好,你媽媽不要你是嗎?沒關系,孩子,跟我走吧,以后我會對你好的。”
Advertisement
他的表可謂是老淚縱橫,阮愈看了他一會兒,漸漸疑慮起來,喃喃自語著:“真奇怪,明明你沒有對我做什麼,為什麼我第一眼看到你還是覺得好惡心。”
鄭卓又哭又笑的表一頓。
他了把眼睛,上前走了兩步,更震撼的仔仔細細的打量著他。
阮愈任他打量。
“哈!”鄭卓笑出來,“哈!”
“你果然是我兒子!”鄭卓的臉上是比剛剛激一萬倍的神采,“你不愧是我兒子,我們是一樣的人!”
他說完,又忽然上前幾步抓住阮愈的肩膀,作間敞開的清潔工外套下寒一閃,被阮愈捕捉到。
“我們是一樣的人!”鄭卓還在激的吶喊,阮愈忽然一抬手臂猛然掐住鄭卓的脖子,用力推著他砸在墻上,墻邊的桌子被兩人到,上面的東西乒乒乓乓摔了一地。
“安靜的生活不好嗎?”阮愈湊近看著他漲得通紅卻還仍然狂熱的臉,低著聲,循循善勸導似的:“別再讓我看到你了好嗎,像前兩年一樣,安靜的生活,不要來找我。”
他們的靜引來了待在廚房的陶興,陶興掀開廚房和客廳之間簾子一看,嚇到大:“阿阮!!!使不得!!!”
陶興慌慌張張的跑過來勸架,阮愈已經掐著鄭卓的脖子把他擲在地上,然后松開了手。
Advertisement
阮愈這樣對他,鄭卓反而捂著脖子在地上一邊咳嗽一邊狂笑,陶興生怕這老爺子出事,想過去扶他,卻被阮愈拉在了后不讓去。
鄭卓的外套大開,腰間的匕首刀柄了出來。他卻渾然不怕人看見,咳夠了,自己慢慢的扶著地站起來。
陶興也看見了,站在原地越來越搞不清狀況。
“我太喜歡你了,你是上帝賜予我的藝品,阮愈……阿阮,只有我懂你,也只有你會懂我,我回去給你準備最后的禮,我會再來的。”鄭卓說完,把外套合上,大笑著從店里走出去了。
“這大爺誰啊……不是,我剛剛看錯了?他腰上是別了把刀嗎?”陶興傻愣愣的看著門口。
鄭卓已經走了,門口懸掛的風鈴晃晃悠悠的發出清脆的響。
“瘋子。”阮愈甩了甩手,淡漠的說:“陶哥,下次他真敢再來你就我,我不在,直接報警。”
阮愈說完,就要往樓上走,陶興仍然沒回過神,不可思議的問了句:“他真是你……啊?”
“不是。”
阮愈沒回頭。
陶興只知道阮愈是從福利院出來的,不知道他世,怕說錯什麼也沒敢再追問。他蹲下來收拾地上的狼藉,回憶著剛剛的場面,越想越覺得脊背發寒,決定一會兒就去網購個自報警裝置。
鄭卓從文化街離開后,沒坐公車,而是步行著找到一個公用電話亭,從兜里找出一張高一十班信息表。
第一行就是蘇恬的名字,后面跟著個母親:白晶,再往后是一串數字。
他笑著在電話上把這串數字一個個按了出來,話筒在耳邊。
過了會兒,電話通了。
里面傳來一個端莊的聲:“喂?”
“白晶。”鄭卓捧著話筒,他覺得自己渾上下的都在沸騰,他重復了一遍:“白晶。”
“你是?”
對方顯然沒聽出來他是誰。
鄭卓語氣埋怨起來:“也就是十九年沒見而已,白大小姐這就忘了我啦?”
猜你喜歡
-
完結204 章

藏夏
17歲那年,向暖轉學到沈城,和分開11年已久的童年夥伴駱夏重逢。她第一眼就認出了他,而他卻早已將她遺忘。 彼時的向暖清秀內斂,並不惹眼,而駱夏卻猶如盛夏的太陽耀眼奪目,被很多女生暗戀喜歡着,向暖也成了其中之一。 只可惜,直到高三結束,她和他依然只是普通同學。 畢業前,向暖鼓起勇氣讓駱夏幫自己填了張同學錄。他在同學錄上留給她的祝願和留給別人的並無兩樣:“前程似錦。” 在駱夏眼裏,向暖沒有什麼特別,她就和學校裏的其他女孩子一樣,只是這夏日的微末一角。 多年過去,向暖和駱夏在醫院再次重逢。此時的他是外科醫生,而她成了他的病人。 向暖本以爲這個不止佔據了她整個青春的男人會和原來一樣,轉頭就會忘記她。 可是這次,駱夏卻將向暖烙印在了心底最深處。“向暖,能不能給我個機會?” 我曾偷偷擅自給過你很多機會,只是你視而不見。 後來,駱夏終於把向暖追到手。同居後的某日,駱夏在書房無意翻到向暖的高中同學錄。男人找到他寫的那頁,卻也將向暖塵封多年的祕密掀開。 那句“前程似錦”後面,寫的是屬於少女整個青春歲月的暗戀——“我偷偷把有你的夏天藏在我的每一天。” 那年求婚時,駱夏單膝跪地,鄭重認真地對向暖說:“暖暖,你願不願意,讓我成爲你的夏季?”
29.7萬字8 15442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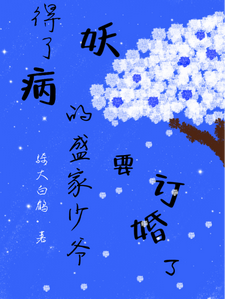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
完結217 章

別惹他的小可憐
[已簽出版待上市]【狂拽痞撩的京圈貴公子x弱美堅韌的學霸小可憐】 【校園x救贖x學霸x雙向奔赴】 唐雨是清遠高中的學霸,卻長期遭受校園暴力。 逼到絕路的那一天,她鎖定了新來的轉校生。 此人夠拽、夠狂。 那天她一身青紫,鼓起勇氣,“幫我三個月,我什麼臟活累活都能做。” 少年眉梢一挑,姿態慵懶,似笑非笑的,“什麼都能做?” 從那天開始,新來的轉校生成了令人聞風喪膽的校霸。 而校霸身后跟了個小尾巴。 可外人不知道,小姑娘名義上是他的小跟班,實際上就是他祖宗。 “下雨天拖地,虧你想得出來。”把拖把丟開。 “這些都吃完,不吃完就是浪費。”變著花樣的喂她。 “這麼瘦,以后多吃一碗飯好不好?”他頭疼。 連自己都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把小跟班當成心肝肉捧著了。 哪是找了個小弟,簡直給自己供了個祖宗啊。 —— 愛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教她不自卑,送她到遠方,燦烈如驕陽。 邊煬啊,是熾烈的陽光,降臨在她的雨夜。
45.8萬字8 126 -
完結108 章

閨蜜小叔他又撩又寵
【甜文+教授+6歲年齡差+校園】【叛逆沙雕少女X禁欲腹黑小叔】 聞厘十七歲那年喜歡上了閨蜜的小叔,那是整個宜大出了名的高嶺之花 男人皮膚冷白,臉戴銀絲框眼鏡,一襲白衣黑褲襯得他儒雅矜貴。初見時,聞厘爬墻逃學被困,為了下墻,鼓起勇氣撩了眼前的男人 誰料事后發現,對方竟是閨蜜口中教學嚴苛到變態的小叔! 聞厘嚇得遁走,結果被男人從后一手拎起:“小朋友,上哪兒去?” 從那后,聞厘每日行為都被他監督 她爬墻逃學,男人罰一萬字檢討 她染發中二,男人罰她把發染回 她成績凄慘,男人為她備課補課 - 她失去親人痛苦悲慟,男人奔來她身邊,為她拂去淚水:“別怕,小叔在。” 后來她開始變好,偷偷寫下“考上宜凌大學”。 在十八歲生日那晚,她滿心歡喜地戳破喜歡,卻得到男人一句“聞厘,你還小,我們現在不合適”。 聞厘臉色煞白,喜歡的心思碎一地 那晚,她撕掉所有跟他有關的東西,決定忘記他,隨親人遠居國外。 - 得知聞厘消失的那天,傅彥禮發了瘋找她 不管他打多少電話,發多少短信,怎麼尋找,他都找不到她 直到四年后那天,她突然以講師身份出現在宜大演講臺上 男人思念如潮,在她下臺后把她拽進懷里,眼眶猩紅。 “厘厘,小叔后悔了。” “你不要走了好不好? “我好想你…”
22萬字8.18 5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