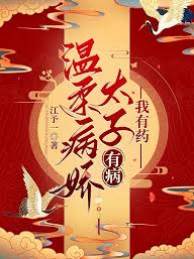《奉旨成親》 第076章 第 76 章
第076章 第 76 章
謝清崖心裏的那點腹誹, 自然只有他自己知道。
徐端宜未曾察覺。
何況這會也重新轉移了視線,朝梅雪征看去。
只四目相之時,徐端宜看著梅雪征眼中那點了然般的笑意, 不由一怔。
但也不過眨眼間的功夫, 那點了然的笑意便消失了。
徐端宜眼中的梅雪征,微低著頭,語氣溫和,還是那副謙遜和氣的模樣。
就和平時一樣。
“微臣沒意見,全憑殿下吩咐。”
徐端宜見此, 便也只當自己是瞧錯了, 也未做多想, 只笑著與二人說道:“那明日我便恭候兩位大人大駕了。”
說罷。
與兩人略一頷首施禮, 便轉過頭同謝清崖聲說道:“王爺,我們先回去吧。”
謝清崖看一眼,沒說話。
只點了點頭。
而後兩人便先離開了這邊。
李文高還保持著躬的姿勢, 恭送徐端宜離開, 等腳步聲走遠, 他才站直子。
餘瞥見側梅兄還看著前面, 一副心很好的樣子, 不由奇怪問道:“梅兄, 何故這般高興?”
梅雪征睜眼說瞎話:“哦,不過是覺得, 這般有幸,竟能被長公主請客吃飯。”
他這話顯然是正好中了李文高的心。
李文高本就格外敬重徐端宜,此時自是立刻變得與有榮焉起來, 一并誇贊起徐端宜。
言辭之間,只差把徐端宜說得天上有地上無了。
王伏新卻是知曉明日況的。
早在夜裏, 王妃便先與他商量過了,他笑著未言,同兩人施禮告退。
而另一邊——
走出一段距離之後,謝清崖那因離別而升起的那點小心緒,也漸漸放平了許多。
“剛去看翠婆婆他們了?”
他跟徐端宜閑話家常,說完又忍不住皺眉:“怎麽也不知道帶上時雨他們?大晚上的,你也不怕出事。”
Advertisement
徐端宜聲回道:“剛喬主簿也在,我想著左右離得也不遠,何況時雨他們這會也有事。”
“他們能有什麽事?”
謝清崖低眉看向徐端宜。
不知道那兩人能有什麽事,別又是在比試了。
要真是如此。
他看令吉這幾個月的月俸,也就別想要了。
徐端宜卻只是,笑著同他說了聲“小事”。
謝清崖聽這麽說,便也沒有多問。
不過等回到院子的時候,謝清崖便也知曉,徐端宜說的有事,究竟是什麽了。
還沒進院子。
才到門口,他就聞到一子濃郁的味道,從裏頭傳出來。
“這什麽味道?怎麽這麽熏?”
聞著有些悉,但謝清崖這一時半刻的,也沒能立刻辨認出來。
又見裏頭煙霧繚繞的,他還以為是什麽東西燒著了。
他下意識的,先把徐端宜,拉到了自己的後。
未曾注意到徐端宜此刻向他時,那毫無掩飾的,藏著意的眉眼。
謝清崖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
“我先去看看。”說著,謝清崖把人往旁邊拉開一些,而後便松開手,皺著眉,先往裏頭看去。
走到門口,瞧見時雨和令吉各拿著一把不知道什麽的東西,在院子裏揮舞著,看著就跟跳大神似的。
“做什麽呢?弄那麽大煙。”他邊說,邊揮著眼前的煙霧。
語氣有些不大好。
不過確認不是著火,他也就放心了,只沖著令吉冷聲發話道:“還不滅了!”
“王爺,這不能滅。”
後卻傳來徐端宜的聲音。
謝清崖回頭看去,見朝他走來。
因為不解,他的眉心依舊微微皺著,他看著徐端宜,沒問人為什麽。
心裏卻已然明白,這大概就是先前說的有事。
只是他不明白,這是在做什麽。
“這是艾草,點著後,有驅蚊的作用。”徐端宜跟謝清崖解釋。
Advertisement
謝清崖一聽這個解釋,剛剛還有些因為不高興而繃的臉,立刻就變得有些僵住了。
也虧得這會煙霧大,夜又深。
要不然他這點不對勁,徐端宜怕是肯定早就發現了。
“主子,王妃,你們回來了!”令吉看到他們回來,這會便樂呵呵的,笑著先朝他們跑了過來。
倒也知道熏。
沒拿著東西,直接對著他們,而是藏在自己後。
聽到王妃這番話,他也連忙跟著附和道:“別說,王爺,王妃這法子真的好的!我聞著這味道都嗆得厲害,那些什麽蚊蟲螞蟻的,絕對是不敢靠近了的。”
“以後回去,蚊蟲多了,我也這麽搞。”
“我這一晚上,就一只都沒瞧見。”
自然是瞧不見的。
謝清崖暗自腹誹:這原本就是他隨口扯出來的瞎話。
謝清崖也的確沒想到。
他不過隨口一句,徐端宜私下竟然做了這麽多,又是送膏藥,又是拿艾草驅蚊,也不嫌麻煩。
“你……”
他看著徐端宜,目一時變得有些複雜起來。
徐端宜也看著他。
接收到謝清崖的眼神,徐端宜卻只是笑著與他說了一句:“王爺今晚能睡個好覺了。”
說完,見那邊時雨還在到揮舞,便出聲阻止:“時雨,夠了,別揮了,放在廊下的銅盆裏就好。”
“是!”
時雨笑著應道。
徐端宜又與謝清崖說了一句:“我先進去。”說完,略與謝清崖一點頭,又跟令吉招呼了一聲,便先進去了。
令吉跟謝清崖說了一聲,也屁顛屁顛跟著過去,打算把手裏的艾草,也一并放到那銅盆裏去。
謝清崖依然未。
他站在原地,目送徐端宜離去的影。
直到時雨和令吉往他這邊走來,謝清崖聽到前方傳過來的靜,方才回過一些神。
Advertisement
沒讓自己的異樣,被他們瞧見。
眼見時雨走在前面。
謝清崖知曉這丫頭的脾,以及對他的不滿,也沒準備說什麽,只想著囑咐令吉一聲,讓人走的時候把門帶上,便也準備進去了。
卻見那丫頭,在快要與他肩而過的時候,忽然停下步子,沖著他的方向,一臉嚴肅地看著他。
這冷不丁的。
謝清崖還以為,這是又有什麽不滿,要與他說。
謝清崖也沒多想。
剛想等人開口,便見這丫頭忽然別扭的,跟他拱了拱手。
這一幕——
不僅謝清崖到吃驚,就連令吉也是一臉不可思議的模樣。
直到時雨施完禮,大步出去。
令吉這才匆匆回過神,朝著人喊了聲:“時雨,你等等我啊!”
他說著,也想拔追過去。
但想到什麽,又突然止步,跟謝清崖說了一句:“對了王爺,有件事,屬下還是得跟您說下。”
謝清崖皺眉著時雨離開的方向,還于“這丫頭發什麽瘋”的狀態中,聽到這話,便又朝令吉看了過去。
“什麽事?”
……
片刻功夫後。
令吉和時雨都已經走了,大門也已經關上了。
但謝清崖還站在院子裏,未曾。
耳邊似乎還環繞著,先前令吉說的話。
“今日和您分開之後,王妃并沒有立刻回衙門。”
“他吩咐屬下,先回衙門,跟王師爺說了一聲今日外邊發生的事,囑咐王師爺叮囑衙門裏的兄弟,不要太意外,免得您日後在這待得不自在。”
“而王妃——”
“我聽時雨說,王妃帶著回到了巷子裏,找到了之前那位和您說話的老人家,也跟他說了同樣的話。”
怪不得今日城中那些人,明知道他的份,卻還是表現得和從前一樣,并沒有與他生疏。
他那會就覺得有些怪怪的。
沒想到……
可真的是沒想到嗎?
其實也并不全是意料之外,他心中豈會一點都沒有察覺?他只是沒想到,徐端宜能為他做這麽多。
廊下銅盆裏的艾草,依舊無窮無盡的燃燒著。
謝清崖目怔怔地看著那點火星。
好像總是把他隨口說的話,放在心上。
然後不求回報的付出著。
……真是個傻子。
月清涼。
謝清崖在院中駐足許久,眼睛看著那點火星,都開始泛酸了,他這才眨了眨眼,重新擡腳往屋中走去。
屋中。
徐端宜已經洗漱完畢。
大約是怕兩人單獨相時,彼此尷尬,這會已經在床上了。
聽到腳步聲。
謝清崖是隔著屏風,才聽到的聲音。
“熱水還有,冷水,剛才令吉也已經打好了,王爺可以在裏間洗漱,我今日累了,便先睡了。”
徐端宜說完。
遲遲未聽到謝清崖的聲音,不由又遲疑著,喊了他一聲:“王爺?”
謝清崖這才找回自己的聲音:“……好。”
徐端宜聽到他的聲音,心明顯放松了一些:“那我先睡了,王爺洗漱完,也早些睡。”
謝清崖又說了一聲好。
然後他聽著裏頭一陣窸窸窣窣,便再也沒有出現過徐端宜的聲音了。
謝清崖怕徐端宜到不自在,便如平時一般,先去洗漱。
只是作明顯放輕了不。
等他一應收拾完,合上房門,留下一盞燭火過去的時候,徐端宜倒是真的已經睡著了。
大概是真的累了。
徐端宜此時睡得很香,呼吸聲,也明顯要比平日重上一些。
這會倒是睡得十分老實,全然看不出,昨晚睡覺時那副折騰人的樣子。
燈火在謝清崖的後。
謝清崖穿著一中,坐在床沿上。
燈花跳了幾下。
屋中的時明時滅。
但謝清崖還是保持著原本的作,未曾變過,他就這麽靜靜地看著床上已經安睡過去的人。
他眼中的緒是複雜的。
不止。
還包括著許多。
骨節分明的手,朝人了過去。
和昨晚一樣。
但這回,謝清崖是清醒的,并且理智的。
他的手,在半空短暫地停留了一瞬,之後便又毫不猶豫地朝人了過去。
指腹輕輕的眉眼,與臉頰。
把那擾人的頭發,就跟昨晚一樣,繞到的耳後。
可即便做完這一切,他也未曾舍得把手收回。
這一刻,他的心中,閃過無數念頭,甚至想著,若是此時能醒來,那就好了。
就可以知道。
他對究竟懷揣著,什麽樣的心思。
可天不遂人願。
今夜的徐端宜,竟是睡得格外的好。
即便覺到臉頰旁,那不一樣的,也未曾有什麽靜,只是拿臉頰,輕輕蹭了蹭他的掌心,就跟黏人的小貓似的。
倒是惹得他掌心生,心跳又莫名加速了許多。
卻還是舍不得收回。
就這麽任人黏著、靠著。
他也只有,在這樣的夜半無人時,方才敢這樣的放縱自己。
“徐端宜……”
他在夜裏,目迷茫,他輕聲喊徐端宜的名字,以及一句似問似慨的低語聲:“我該拿你怎麽辦呢?”
黔驢技窮。
他好像真的,拿一點法子都沒有了。
沖冷臉,讓離他遠些?
恐怕他自己就最先舍不得了。
可難道要跟,徹底坦自己的心扉嗎?
表哥的心思,他不是不知道。
對他而言,若徐端宜徹底上他,必定會對他們有利。
事實也的確如此。
可就連他自己,都還不知道,前路究竟會如何,難道真的要把拉進這個暗流之中,讓為難痛苦嗎?
他舍不得。
謝清崖不知何時上了床。
他弓著,膝蓋著床。
額頭卻輕輕抵在徐端宜的額頭。
他的嗓音,迷茫,沙啞,重複著,呢喃著,和一個此時本不會回答他的人,不住說道:“徐端宜,我們該怎麽辦?”
他已經完全不知道,該怎麽辦了。
他想讓他。
他實在太想跟相了。
無人能抵擋得住徐端宜的意,他想日日擁抱,親吻。
無論他怎麽跟自己說,不要靠近、不要上……可就算重複百次千次,只要出現在他面前,甚至都不需要說什麽、做什麽,那一切的自我警戒,就再次變了廢墟。
他本做不到。
所以一次次的妥協、回顧、停留,以至于落到如今這樣的田地,想走走不掉,想留又不敢留。
可他又希,別他。
他太痛苦,徐端宜不應該這麽痛苦。
“徐端宜……”
他輕輕抵著徐端宜的額頭。
在燭火的映襯下,薄紗屏風之後,他們倆就像兩頭互相依偎的小一般。
猜你喜歡
-
完結1482 章

皇後天天想和離
他是手握重兵,權傾天下,令無數女兒家朝思暮想的大晏攝政王容翎。她是生性涼薄,睚眥必報的21世紀天才醫生鳳卿,當她和他相遇一一一“憑你也配嫁給本王,痴心枉想。”“沒事離得本王遠點,”後來,他成了新帝一一“卿卿,從此後,你就是我的皇后了。”“不敢痴心枉想。”“卿卿,我們生個太子吧。”“陛下不是說讓我離你遠點嗎?”“卿卿,我帶你出宮玩,”
139.7萬字8.33 514932 -
完結250 章

愛卿,龍榻爬不得
魏無晏是皇城裏最默默無聞的九皇子,懷揣祕密如履薄冰活了十七載,一心盼着早日出宮開府,不料一朝敵寇來襲,大魏皇帝命喪敵寇馬下,而她稀裏糊塗被百官推上皇位。 魏無晏:就...挺突然的。 後來,鎮北王陶臨淵勤王救駕,順理成章成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攝政王。 朝中百官紛紛感嘆:奸臣把持朝政,傀儡小皇帝命不久矣! 魏無晏:好巧,朕也是這麼想的。 慶宮宴上,蜀中王獻上的舞姬欲要行刺小皇帝,攝政王眸色冰冷,拔劍出鞘,斬絕色美人於劍下。 百官:朝中局勢不穩,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朝局。 狩獵場上,野獸突襲,眼見小皇帝即將命喪獸口,攝政王展臂拉弓,一箭擊殺野獸。 百官:前線戰事不明,攝政王還要留小皇帝一命穩定軍心。 瓊林宴上,小皇帝失足落水,攝政王毫不遲疑躍入宮湖,撈起奄奄一息的小皇帝,在衆人的注視下俯身以口渡氣。 百官:誰來解釋一下? 是夜,攝政王擁着軟弱無骨的小皇帝,修長手指滑過女子白皙玉頸,伶仃鎖骨,聲音暗啞:“陛下今日一直盯着新科狀元不眨眼,可是微臣近日服侍不周?” 魏無晏:“.....” 女主小皇帝:本以爲攝政王覬覦她的龍位,沒想到佞臣無恥,居然要爬上她的龍榻! 男主攝政王:起初,不過是憐憫小皇帝身世可憐,將“他”當作一隻金絲雀養着逗趣兒,可從未踏出方寸之籠的鳥兒竟然一聲不吭飛走了。 那便親手將“他”抓回來。 嗯...只是他養的金絲雀怎麼變成了...雌的?
40.5萬字8.18 12559 -
完結23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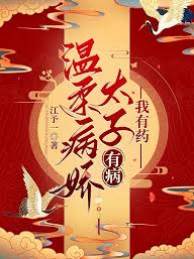
溫柔病嬌太子有病,我有藥
【古言甜寵 究極戀愛腦深情男主 雙潔初戀 歡快甜文 圓滿結局】 謝昶宸,大乾朝皇太子殿下,郎豔獨絕,十五歲在千乘戰役名揚天下,奈何他病體虛弱,動輒咳血,國師曾斷言活不過25歲。 “兒控”的帝後遍尋京中名醫,太子還是日益病重。 無人知曉,這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夜夜都會夢到一名女子,直到瀕死之際,夢中倩影竟化作真實,更成了救命恩人。 帝後看著日益好起來,卻三句不離“阿寧”的兒子,無奈抹淚。 兒大不中留啊。 …… 作為大名鼎鼎的雲神醫,陸遇寧是個倒黴鬼,睡覺會塌床,走路常遇馬蜂窩砸頭。 這一切在她替師還恩救太子時有了轉機…… 她陡然發現,隻要靠近太子,她的黴運就會緩緩消弭。 “有此等好事?不信,試試看!” 這一試就栽了個大跟頭,陸遇寧掰著手指頭細數三悔。 一不該心疼男人。 二不該貪圖男色。 三不該招惹上未經情愛的病嬌戀愛腦太子。 她本來好好治著病,卻稀裏糊塗被某病嬌騙到了手。 大婚後,整天都沒能從床上爬起來的陸遇寧發現,某人表麵是個病弱的美男子,內裏卻是一頭披著羊皮的色中餓狼。 陸遇寧靠在謝昶宸的寬闊胸膛上,嘴角不禁流下了悔恨的淚水。 真是追悔莫及啊~
42.5萬字8 7922 -
完結212 章

將軍她又美又颯,權臣甘拜裙下
【女扮男裝將軍vs偏執權臣】人人都說將軍府那義子葛凝玉是上趕著給將軍府擦屁股的狗,殊不知她是葛家女扮男裝的嫡小姐。 一朝被皇上詔回京,等待她是父親身亡與偌大的鴻門宴。 朝堂上風波詭異,暗度陳倉,稍有不慎,便會命喪黃泉。 她謹慎再謹慎,可還是架不住有個身份低微的男人在她一旁拱火。 她快恨死那個喜歡打小報告的溫景淵,他總喜歡擺弄那些木頭小人兒,還次次都給她使絆子。 起初,溫景淵一邊操著刻刀一邊看著被五花大綁在刑架上的葛凝玉,“將軍生的這樣好,真是做人偶的好面料。” 后來,溫景淵將她圈在懷里,撥弄著她的唇,“姐姐,先前說的都不作數,姐姐若是喜歡,我來做你的人偶可好?” 葛凝玉最后才知道,昔日心狠手辣的笑面虎為了自己賭了兩次,一次賭了情,一次賭了命。 排雷:1、女主穿越人士,但沒有過多的金手指,情感線靠后 2、作者起名廢 3、架空西漢,請勿考究
39.9萬字8 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