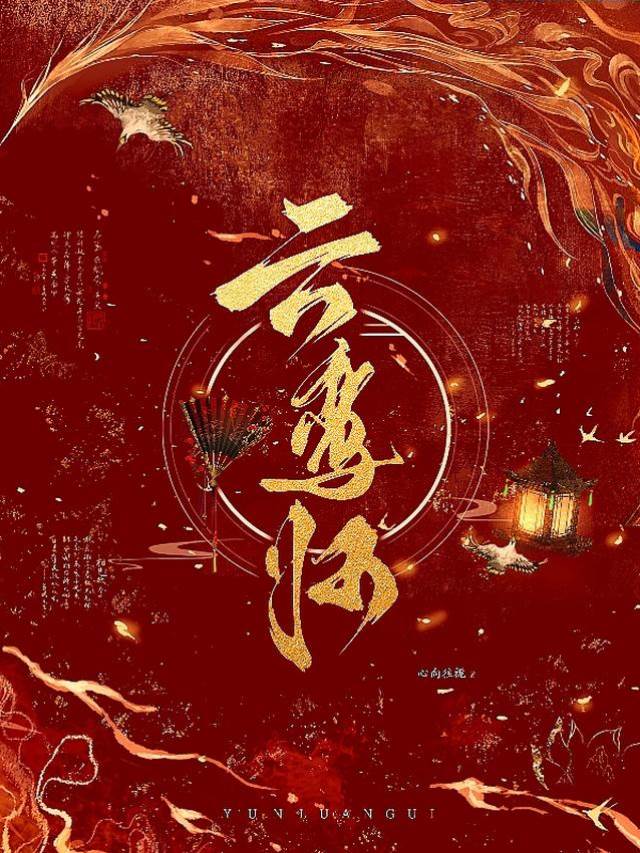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侯府在逃小妾》 隔閡
隔閡
鮫紗質地輕盈, 用薄如蟬翼來形容最是恰當,經外力一撕扯,恍似書頁般從中裂開。
縷斜自未闔的檻窗悄然爬了進來,映照在碎條狀的面料上, 掠起生影, 宛若五彩糖。而大片雪原頂峰, 開出兩株不畏嚴寒的梅花, 抖擻聳立,令見者險些忘記呼吸。
衛辭似是乘興而歸,卻誤藕花深的酒鬼。
視線被夜幕攫取, 為免踩空踏錯, 只得用劍柄撥開沿途遮眼的枝葉,小心翼翼地往前探去, 確認可以通行,方邁出下一步。
他膛劇烈起伏兩下, 終究不舍得莽撞,即便慍怒與快要臌脹至炸裂,理智也一點一點流失。
宋死死抓著下榻沿,擡足去踢他的肩,卻被輕易反握住。指腹因習武形了薄繭,清晰, 帶著別樣的刺激, 蜿蜒直上。
纖細筆直的小在半空晃了晃, 又帶了不滿去蹬他。
衛辭終于施舍了一個眼神,且當著的面兒極盡靡麗地了。
“你發什麽瘋。”宋憤加, 小臉漲了蝦,偏偏語調了所, 半點氣勢也無,倒像求不滿的婉轉哀鳴。
他三下五除二將長衫徹底撕碎片,天散花般扔落一地,而後欺上前,發狠地碾過敏的珠,冷笑道:“發瘋又如何,我真想把你關起來,誰也不許靠近半步。”
男子息聲裹挾著濃重,細聽之下卻有一委屈,稍縱即逝,令宋難以捕捉。
霎時,心間竄出一電流,麻麻,帶起前所未有的暢快。
宋後知後覺地領悟,既不喜過分卑微的男子,也不喜盛氣淩人的男子。唯有衛辭,介于二者之間。
明明似一頭渾蘊含著攻擊力的兇,可就是能夠篤定,爪落在上時,鋒利長甲會倒收回去,只餘虛張聲勢的墊。
Advertisement
“啪噠”撞擊。
非但不疼,反倒像某種趣。
既到驚懼又全然信任,矛盾得很,也實打實地勾得心澎湃,雙止不住發。
這不是男妖是什麽?
衛辭忽而腰運力,打斷的走神,惡聲惡氣地威脅:“不許想別的男人。”
宋無辜地回他發紅的眼,噙著淡淡笑意,仰頭胡吻了一通,在衛辭滿目疑中擡膝輕蹭,聲道:“可是,我分明在想你呀。”
見他不信,宋嘟起,索要親吻。
本能驅使著衛辭輕輕地垂首一,旋即似是被自己的好脾氣嚇到,不可思議地扯開距離。
宋眼中笑意愈深,烏黑眸子往高脹瞥去,略帶了些別扭道:“你不是一直想試麽,咳,去洗洗,洗幹淨些。”
“當真?”他微微怔愣,表極速緩和,周氣質都隨之改變,像是饜足的雄獅,依然威風凜凜,卻收起了爪牙,喚大膽靠近。
“……好話不說第二遍。”
衛辭下不斷上揚的角,捧著的臉深深一吻,而後大步繞過屏風進了浴房。
宋心中忐忑,又忍不住懊惱,懊惱自己竟被男勾到了這種地步。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遂起用青鹽細細了牙。
回至裏間,衛辭正雙大開,略帶松弛地坐上人榻,如玉長指撚起巾,一不茍地著水珠。
視線不可避免地掃了一掃,宋佯作鎮定:“先說好了,我不曾做過這樣的事,怕是不一定能令你滿意。”
“一回生二回。”
衛辭扔掉巾,反手撐著榻沿,大度道,“我不也吃了好幾回才索到訣竅。”
……
他還自豪。
宋豁出去了,出舌尖探試地一,像是夏日散學之後,人手捧著一個解暑雪糕。
Advertisement
衛辭面上的表出現了一瞬空白,薄自然張啓,勁瘦軀眼可見地繃著,仿佛張到極限的弦,輕輕一撥,便會“砰然”炸開。
他竭力不去領略其間的,白皙的紅一片。戾氣未褪的眉眼原是有幾分冷淡,配著灼熱目,別有一番割裂的。
宋自他眸中窺見了溺死人的意。
忽而明白過來,為何衛辭會熱衷于對自己做這種事。此刻,心底的滿足鋪天蓋地襲來,又似一簇一簇煙火,在腦海中轟轟烈烈地綻開。
總之,奇妙得。
衛辭無法再游刃有餘地掌控,息急促低沉,比以往都來得激。餘瞥見宋癡癡著自己,強勁的愉悅和赧齊齊湧上了臉。
他罕見地到難為,脖頸後仰,用掌心覆住眼,只餘一雙滴耳尖在外頭。
雖是如此,衛辭明顯十分,不得一直不停歇。甚至,克服了害以後,輕輕上烏黑的發,眼神失焦,好似靈魂升天一般。
察覺到的不適,衛辭終于良心發現,低頭問:“累不累?”
宋實話實說:“累死了。”
衛辭也不舍得維持著跪姿,便托住纖細的臂:“今日足夠了,先起來。”
此話好巧不巧,中了宋心窩深的叛逆。充耳不聞,揮開衛辭t,繼續隨心忙碌。
他周繃。
兩刻鐘前尚能帶著殺氣挽出漂亮劍花,如今命脈了脅迫,整個人散發出脆弱不堪的。
宋瞧得心神漾,咽了咽口水。
“呃啊……”
衛辭在關鍵時刻離開的,免得某人清醒過後要發難,不忘聲誇贊,“很棒。”
“咳,那是自然。”
短暫頸相擁,倏爾,衛辭複又垂首舐起的,宋茫然:“你不會還要……”
Advertisement
他理所當然地“嗯”一聲,反問道:“尚不曾喂飽你,不是麽?”
“不要了。”宋漲紅著臉掙紮。
此時樓船已經行至海上,風浪作響,站立時難免搖搖晃晃。衛辭托著起,失重令宋不得不攀附著他,後者出神,恬不知恥道:“這般便不會傷及你的膝蓋了。”
/
沒沒臊地過了兩日,大船駛停至湘府,而後換乘馬車,所幸道平坦,不必什麽罪便順利回到錦州。
宋分乏,只好差香茗與香葉四送信,告知衆人自己已平安歸來。
關于鋪子,也有了新的決斷。
從前,宋不曾想過衛辭的新鮮會這般持久,非但親自南下“捉”,還態度堅決地要帶上京,是以一門心思盼著發家致富、招攬贅婿。
如今看來,有生之年再難踏足錦州,經營鋪子一事也是鞭長莫及。
既如此,不若將鋪子轉贈給兩位姐妹,兩的利存作小金庫,以備不時之需。
其實,此番去龍雲,宋何嘗不曾思量過遠走高飛。
是良籍,手裏頭又有充足銀錢,再尋個民風淳樸的好地方,盤下鋪子快活一生,豈不妙哉?
偏偏殺出個祁淵,令幡然領悟,自己一路行來之所以能安然無恙,只因邊跟了個武功高強的蒼杏。否則,早被生吞活剝不知多次。
這世道,子原就不易,手無縛之力的子更加寸步難行。
可蒼杏是衛辭的人,難以策反,保護自己的同時,何嘗不是一種監視?宋深信,若執意離開,不出百步,定要被灰溜溜地拎回來。
前有豺狼後有猛虎,左思右想,暫也尋不出“上京”以外的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細細謀劃過後,宋尋人寫了新的契約書,將大致形和玉蕊、桃紅解釋一番,并列了幾條自己路途中琢磨的點子,譬如繡樣可制些生辰限定的款式、譬如妝面也可效仿龍雲時興的樣式。
衛辭只給了兩日時間歇腳,當真是忙得暈頭轉向,連散夥飯也顧不上張羅。
倒也有兩件喜事。
其一,楊勝月與心上人訂了親,齊齊了京,將來有的是機會面。其二,畫本名氣漸漸傳開,不但回了本,還有上京之後重舊業。
……
待到月上枝頭,宋辦妥了各項事宜,匆匆忙忙趕回府中。
因著隔日便要遠行,衛辭有意令養蓄銳,夜間,兩人難得平靜地抵足談天。
宋擁著衾被,冷不丁發問:“公子喜歡我麽?”
聞言,衛辭神僵了僵,心道過于麻。可見亮晶晶地向自己,又不忍拂了興致,遂惱怒地“嗯”一聲,側轉過去。
誰知,宋魚兒般依附上來,桃腮著他結實有力的臂膀,輕聲道:“可我不想要孩子。”
“那便不要。”
衛辭答得爽快,順勢擡手與十指相扣,語調慵懶地解釋,“過了弱冠之年再議,且在那之前需得先尋個正妻,屆時將我們兒子記在名下,那便是名正言順的嫡子——未來的小小侯爺。”
正妻。
宋心下一涼,突兀地回手,整張臉埋進衾被,蓋住自己難以掩飾的複雜神。
的確念衛辭當初的搭救,若沒有他,自己或許早已被王才富納後宅,又或許不堪辱,懸梁結束這一生。
但人心向來貪婪。
更何況,宋的芯子經歷過自由自在的後世,很難再毫無芥地接古代的一切。縱然,衛辭方才所言,在世人眼中已是天大恩賜……
輕籲一口氣,像是做了重大決斷,緩緩鑽了出來,迎上衛辭疑的目低低地問:“公子一定要娶妻麽?”
猜你喜歡
-
連載200 章

團寵小醫妃,攝政王又犯病了
21世紀中西醫學鬼才,稀裡糊塗穿越異世,遇到洪水瘟疫?不怕,咱彆的都忘了但老本行冇忘。 皇子染怪病,將軍老病沉屙,宰相夫人生小孩也想她出馬? 冇問題!隻要錢到位,啥活俺都會! 楚雲揚:吶,這是地契,這是王府庫房鑰匙,這是…… 葉青櫻:等等,相思病我醫不了的! 楚雲揚:怎會?我思你成疾,自是唯你可醫~
18.3萬字8 8865 -
完結690 章

穿越后被迫登基
一朝穿越,葉朔成了大周朝的九皇子。母親是最得寵的貴妃,外祖父是手握重兵的鎮國公,他剛出生就一躍成為了最熱門的皇位爭奪者前三,風頭直逼太子。最關鍵的是,母親同樣有奪嫡之念。寵妃+兵權+正直壯年的皇帝,這配置一看就是要完,更何況,他前面還有八個…
106.4萬字8 8694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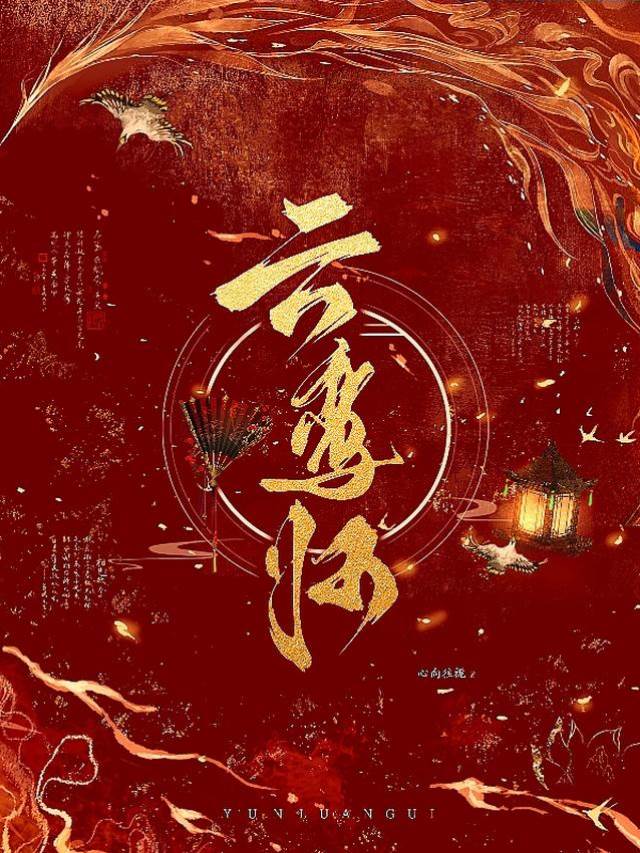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
完結213 章

位高權重的夫君傲嬌霸道,得哄著
【古言 無重生無穿越 先婚後愛 寵妻甜文 虐渣 生娃 女主成長型】薑元意容色無雙,嬌軟動人,可惜是身份低微的庶女。父親不喜,嫡母嫌棄,嫡姐嫡兄欺負,並且不顧她有婚約,逼迫她給奄奄一息的景國公世子爺衝喜。拜堂未結束,謝容玄暈倒在地。當時就有人嘲笑她身份低、沒見識、不配進景國公府。她低頭聽著,不敢反抗。謝容玄醒來後,怒道:“誰說你的?走!罵回去!”他拖著病體教她罵人、給她出氣、為她撐腰、帶她虐渣……她用粗淺的醫術給他治療,隻想讓他餘下的三個月過得舒服一些。沒想到三個月過去了。又三個月過去了。……謝容玄越來越好,看見她對著另一個男人巧笑嫣然,他走上前,一把將她摟入懷裏,無視那個男人道:“夫人,你不是想要孩子嗎?走吧。”第二天薑元意腰疼腿軟睡不醒,第三天,第四天……她終於確定他病好了,還好得很,根本不是傳言中的不近女色!
39.4萬字8 2051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