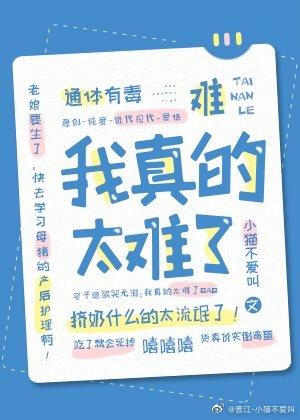《追你時無情,不愛了你反變舔狗》 第61章 君子動手不動口
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覺。
一個深骨髓的東西,悉了、習慣了,幾乎要為生命的一部分,突然有一天這個東西失去了,大腦不斷告訴自己“已失去”的事實,可理智像是被麻痹一般,總覺得生活沒有任何變化,仿佛只要自己回頭,那東西仍在自己的目之所及。
沈徹腦子如同宕機,他的瞳孔有些渙散,薄張了張,最終還是抿一條直線。
他在試圖理解江嶼山的話,什麼做不要他了?明明他和溫南初是獨立的個,不是彼此的所有,怎麼會用上“不要”這個詞。
江嶼山看他的樣子,無力扶額,他知道沈徹在上很遲鈍,或許是和時的經歷有關,沈徹在方面有所缺失,對所有事的反應都很冷淡。
現在回想起來,溫南初當初居然能夠堅持不懈地喜歡這“榆木”那麼久,真是不可思議。
江嶼山深深地嘆一口氣:“理那些熱搜謠言的時候速度比誰都快,你對的反應要是也有這麼迅速就好了。”
沈徹沒有言語,他現在很混,好像迷霧之中,眼前有一扇門,有一個聲音告訴他,推開門,走進去,一切都會恍然大悟,可是無論他怎麼走,甚至是跑起來,那扇門和他之間的距離始終沒有短分毫。
“行吧,你按照我說的來做。”江嶼山妥協地拍拍沈徹的肩膀,“首先,把你昨晚一直在忙的事告訴溫南初。”
撤熱搜的事?告訴溫南初干什麼?沈徹疑看他一眼。
“邀功啊!”江嶼山加重語氣,他就不明白了,平時沈徹和集團那些合作方談利潤劃分的時候不是皮子很能說嗎,商也不低啊,怎麼就在這事上跟個傻子一樣?!
Advertisement
“沒有什麼功勞。”沈徹不帶任何的平鋪直敘,“我只是做了……”
“我讓你做你就做!”江嶼山聽不得這傻子的發言,直接打斷。
平時一般都是他按照沈徹的建議行事,然后佩服大喊“徹哥厲害”,今天倒是角互換了——翻做主的覺,爽!
沈徹指尖挲,下心底莫名的緒,低低應了一聲:“知道了。”
……
溫南初最近遇到一些麻煩事。
他們學校沒有門,校門的管理也不是特別嚴格,所以同學們可以自由地進出,而校外人員登記份證、掃碼就可以進到校園。
本來這是很不錯的事,如果沒有一些人故意混進來對進行惡意行為。
事的開始是那天早晨,走在去上早八的路上,路過綜合樓的時候突然竄出來一個陌生人,手里舉著一個喇叭大喊的名字,稱是“惡心人的賤”,說盡了難聽至極的臟話。
溫南初表一僵,怔怔地站了幾秒,很快反應過來,那群人的陣地從網絡上轉移到線下了。
正是早八高峰期,路上的學生很多,大家都停下來看熱鬧,一時間議論紛紛。
溫南初面上不見喜怒,眼神古井無波地盯著那個大喊的生,然后拿出手機撥打了學校保衛的電話。
生見似要求助,笑得更是猖狂:“表子!你犯賤的時候他*的怎麼不求救啊?現在知道后悔了!”
“不,該后悔的是你。”溫南初神不變,仿佛只是在說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在幫你打電話。”
“哈?”生角咧開,要繼續辱罵,只是嗓子里一個音節都還沒有發出來,突然——
Advertisement
“嘭——”
一本厚厚的書重重砸在的腦袋上,砸得后撤幾步,頭暈目眩。
溫南初拿著手里磚塊似的教材書,看的眼神像是在看一個沒有生命的件,聲音淬了冰碴子一般:“我向來信奉一個道理,君子手不口。”
生捂著被砸起包的腦袋,懵懵地想,這句話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你,你敢打我?!”河東獅吼經典再現。
溫南初被震得發疼的耳朵,拔高了音量,讓圍觀的吃瓜群眾聽得一清二楚:“我不僅打你,我還要告你!侮辱誹謗我,你已經侵犯了我的合法權益知道嗎!”
“我……我才沒有!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清楚。”似乎是沒想到溫南初這麼核,生底氣瞬間低下去。
“我做的事?”溫南初眼底出毫不掩飾的譏笑,“蠢貨,給你錢讓你來的人有沒有切實的證據啊?”
生一愣,這種給錢鬧事的事,誰會想要什麼證據,又不是張正義。
溫南初一看的樣子,心底又暗罵一聲“蠢貨”,舉起從剛才拿著喇叭大喊就開始錄像的手機,在眼前晃晃:“我有哦,看你的樣子應該不是無業游民吧,你猜你會不會背上案底?”
生臉刷地變了,一下子漲紅,又變青,最后慘白。
“你……你別得意!蒼蠅不叮無蛋,你也不是什麼好人!”留下這句話,生灰溜溜地跑了。
溫南初嗤笑一聲:“什麼年代了,還搞“害者有罪論”那一套。”
本來溫南初以為事就此差不多了,但是背后的人打定主意不想讓好過。
Advertisement
這之后的幾天,溫南初總是在各種地方到不懷好意的目,能明顯聽到那些人惡意的詆毀,然而他們學聰明了,并不指名道姓,而且就算溫南初直截了當正面他們,他們立馬轉就走,讓人有種一拳打倒棉花上的覺。
幾次下來,溫南初在學校里的名聲也傳開了,本來大學生就在網絡沖浪前沿,這下發展到線下更是如星火燎原之勢。
路上、教室、食堂、圖書館……漸漸的,溫南初也分不清,那些不懷好意的眼神與言語,到底是來自校外人員,還是校友的了。
雖說重活一世,心態抗能力較好,但是那并不代表會一直不影響。
不過四五天,溫南初心里的躁意越來越重,像個上躥下跳的小火人,只等著點燃炸彈。
這天午飯時間,看著主找上門的油膩男,溫南初挑眉,真是瞌睡來了有人送枕頭,“引火線”這不就自己來了。
要說那個背后的人也太沉不住氣了吧,試圖用輿論垮,卻一次次給遞上緒的宣泄口,真是個“好人”吶。
油膩男開門見山,摔下一沓鈔票:“聽說你很喜歡勾搭有錢人,有錢就能張開,哥給你個機會,虧不了你!”
溫南初聞言抬起眸子,二話不說抄起桌上的湯碗就扣在他油膩的頭頂:“很久沒洗澡了吧,這麼臭。”
一邊說還一邊往下摁,以前天天干活,力氣比大部分生都大,一時間那個男的竟然掙不開。
真是換了個人就沒了經驗教訓,記不住是個“能手絕不口”的人。
油膩男終于從桌面上抬起自己湯橫流的臉,一臉怒氣,咬腮幫子的牙齒都氣得打:“賤人!老子打死你!”
說著猛地揮起手臂,勢必要狠狠給一掌!
溫南初徹底冷下眉眼,只是不等有所作,忽然被人往后拉了一步,落一個清冽的懷抱。
“你要打誰?”頭頂傳來冰冷徹骨的聲音,像是古井寒潭,人凍起一層皮疙瘩。
溫南初下意識抬頭去,看見沈徹棱角分明的俊臉……真是媧完的作品,這個死亡角度都讓人嫉妒。
沈徹骨節分明的大手死死住油膩男的手腕,發出“咔嚓”一聲。
猜你喜歡
-
完結3818 章

快穿女神,有點甜
蘇葵作為一個有錢有權的千金小姐,居然被劈腿了。於是她果斷將一對狗男女整的身敗名裂! 然而狗急也有跳牆的時候,所以她死了…… “叮!恭喜觸發女配上位係統,是否與本係統綁定?” 再後來,蘇葵開始了她漫漫虐(bao)女(mei)主(nan)的心酸(大霧)曆程。
334.8萬字7.91 31927 -
連載2747 章

暖心甜妻:淩總,晚安!(分頁版)
蘇熙和淩久澤結婚三年,從未謀麵,極少人知。 晚上,蘇熙是總裁夫人,躺在淩久澤的彆墅裡,擼著淩久澤的狗,躺著他親手設計訂製的沙發。而到了白天,她是他請的家教,拿著他的工資,要看他的臉色,被他奴役。 然而他可以給她臉色,其他人卻不行,有人辱她,他為她撐腰,有人欺她,他連消帶打,直接將對方團滅。 漸漸所有人都發現淩久澤對蘇熙不一樣,像是長輩對晚輩的關愛,似乎又不同,因為那麼甜,那麼的寵,他本是已經上岸的惡霸,為了她又再次殺伐果斷,狠辣無情! 也有人發現了蘇熙的不同,比如本來家境普通的她竟然戴了價值幾千萬的奢侈珠寶,有人檸檬,“她金主爸爸有錢唄!” 蘇熙不屑回眸,“不好意思,這是老孃自己創的品牌!”
246.2萬字8.46 385320 -
完結133 章

頂級溺寵!嬌軟小漂亮被病態圈占
【貌美軟糯釣係小嬌嬌x位高權重瘋批大佬】薑杳杳穿書的時候,她正嬌滴滴坐在反派大佬腿上,紅唇貼向男人側臉。軟聲甜氣,媚眼如絲,“裴先生,杳杳仰慕您很久了……”男人垂眼看她,眸底冰冷毫無波瀾。下一瞬,手腕被攥住。原主偷偷握在手裏的匕首暴露在燈光下,寒芒閃動。背鍋俠薑杳杳:“!!!”……書中她有印象,捅刀子失敗後,反派大佬心狠手辣陰鷙冷血,當即就把炮灰女配薑杳杳剝皮削骨,做成了燈籠。反應過來的薑杳杳小臉一白,瞳孔震驚。她又慫又怕,磕磕絆絆地說著解釋的話,反派大佬麵無表情地看著她,薑杳杳差點覺得自己又要死了。可誰料——反派大佬摩挲著刀柄,低沉聲線禁欲又撩人,連氣息都仿佛環繞在她耳邊:“不是說仰慕我,然後呢?”-裴珩其人,涼薄狠戾,偏執冷情。在沒遇見薑杳杳之前,他如高山薄雪,俯視眾生。無數名媛狂蜂浪蝶般爭奇鬥豔,他連一個眼神都欠奉。可後來,他的目光總是不由自主地追隨著那個纖細身影,不厭其煩地哄她吻她,說盡世界上最好聽的情話。他的寶貝杳杳蜷縮在他懷中,烏發紅唇,漂亮小臉眼尾暈開一片薄紅,甜軟嗓音微微發顫,“裴珩……老公……”
26.4萬字8 10821 -
完結166 章

夏日蟬鳴時
“我對自己沒掌握能力 也許有一天 我會需要你 守着你用我這一輩子“
26.4萬字8.18 1148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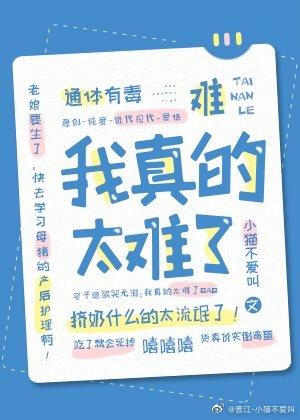
坑過我的都跪著求我做個人
容子隱是個貨真價實的倒黴蛋。父母雙亡,親戚極品,好不容易從村裏考出來成為大學生,卻在大學畢業的時候路被狗朋友欺騙背上了二十萬的欠債。最後走投無路回到村裏種地。迷之因為運氣太差得到天道補償——天道:你觸碰的第一樣物品將會決定你金手指方向所在,跟隨系統指引,你將成為該行業獨領風騷的技術大神。容子隱默默的看了一眼自己手邊即將生産的母豬:……一分鐘後,容子隱發現自己周圍的世界變了,不管是什麽,只要和農業畜牧業有關,該生物頭頂就飄滿了彈幕。母豬:老娘要生了,快去學習母豬的産後護理啊!奶牛:擠奶什麽的太流氓了!最坑爹的還是稻田裏那些據說是最新品種的水稻,它們全體都在說一句話:通體有毒,吃了就會死掉嘻嘻嘻。容子隱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後來,那些曾經坑過容子隱的人比容子隱還欲哭無淚:我真的太難了QAQ,求你做個人吧!1v1,主受,開口就一針見血豁達受vs會撩還浪甜心攻注:1,本文架空!架空!架空!請不要帶入現實!!!文中三觀不代表作者三觀,作者玻璃心神經質,故意找茬我會掏出祖傳表情包糊你。2,非行業文!!!任何涉及各個行業內容,請當我杜撰!!!別再說我不刻意強調了,寶貝們~請睜大你們的卡姿蘭大眼睛好好看看我備注裏的感嘆號好嗎?內容標簽: 種田文 美食 現代架空 爽文搜索關鍵字:主角:容子隱 ┃ 配角:季暑 ┃ 其它:一句話簡介:我真的太難了
32萬字8 870 -
完結123 章

掠她溫軟:港圈大佬的暗夜纏歡
【冷欲系瘋批大佬×純欲野玫瑰設計師 | 甜欲+豪門爽寵+極限拉扯+雙潔】「溫晚,你逃一次,我追一輩子。」 那晚港城暴雨,她逃進電梯,撞上人人畏懼的周家太子爺—— 男人指腹碾過她咬紅的唇,眸色暗沉:“求我,就幫你。” 她倔強搖頭,卻被他抵在鏡前:“嘴硬?那就換種方式解。” 后來全城皆知。 矜貴狠戾的周時凜,為個名不見經傳的設計師發了瘋。 酒會上摟腰深吻,拍賣會擲千萬粉鉆,甚至為她當眾砸了對手賭場。 可當她發現,初見那晚的“意外”全是他布的局…… 溫晚甩下鉆戒消失,只留一句:“周總,游戲該換我主導。” 再重逢時。 她成了國際珠寶展主辦方,對他疏離一笑:“合作請排隊。” 當晚,男人將她抵在展柜前,背后是價值連城的珠寶,眼前是她瀲滟的眼。
20.9萬字8 1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