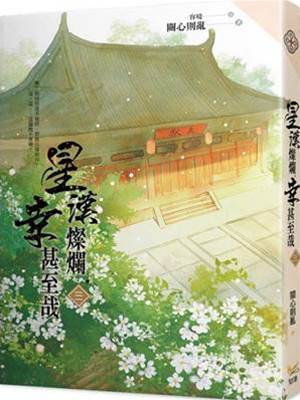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貴妃二嫁》 第64章 第 64 章 婚宴2
韓國公還是沒從震驚中回過神,“陛下這般夜訪,怕是不妥,昭德皇後可知?”
皇帝點頭,“今日表妹出嫁,母後讓孩兒前來送一程,順便替舅舅問安。”
皇帝的份恢複後,便是韓家的親侄子,韓千君的親表哥,遲早會來韓家走一趟,趁著今日韓千君出嫁,掩人耳目,上門再適合不過。
堂堂一國之君來向他問安,即便那人是自己的親外甥,國公爺也不敢當真把人家當外甥看,地道:“臣惶恐...”又緩聲道:“陛下,回來了就好...”
一句回來了,包含了千言萬語。
兩人慢慢地聊起了當初二皇子在那場大戰中,是如何陷害他,皇帝與昭德皇後又是如何忍辱負重,一步一步回到宮中。
驚心魄之,韓國公幾度咽哽,“陛下苦了...”
皇帝難得陪韓國公飲了幾杯。
舅舅和外甥許久,秦漓也陪著韓千君在一旁說話。
Advertisement
皇帝扭過頭突然喚了一聲,“千君。”
韓千君沒想到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名字,茫然擡起頭,“啊?”
皇帝把手邊備好的一個匣子,輕輕推了推,“好好過日子。”
“多謝表哥,”實屬寵若驚,但東西不能要,辛公子養得起,韓千君婉拒道:“表哥放心,辛公子待我很好,我們會好好過日子的,陛下的心意我領了,我不缺...”見鄭氏的目狠狠瞪來,又怕皇帝尷尬,韓千君呵呵了兩聲,解釋道:“我怕辛公子會吃醋。”
韓國公:......
再是親戚,到底與皇帝有過一段婚姻,如今為了將來的夫君,當著皇帝的面要與他撇清關系,確實有些微妙。
皇帝倒沒介意,語氣溫和,真正把當了表妹,“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了,莫要後悔。”
韓千君自然知道要從皇帝手裏拿東西,不容易。
但不後悔。
沒有夫妻緣,親還在,韓千君也不是什麽都沒收,提了提手邊的一個竹筐,“皇後娘娘的兔子,我收下了。”
Advertisement
往日不講理,喜歡去皇帝那銀子,大抵也是仗著知道皇帝不會把怎麽樣,蠻橫之中還帶了一些有恃無恐的撒。
今後不會了,有了辛公子。
蠻橫也好,撒也好,自有辛公子來消。
約莫這就是為人妻的悟。
——
皇帝和皇後離去後,都快到半夜了,韓千君一出來,便被嬤嬤給架回了院子,急急忙忙地替梳妝。
旁人并不知道皇帝和皇後來過,嬤嬤一面忙乎,一面埋怨道:“國公爺明知時辰迫,偏生還在這時候宣三娘子過去敘話,一敘還敘了一個時辰...”
大娘子和二娘子一宿沒睡,立在一旁替嬤嬤打下手,聞言大娘子笑著道:“大伯八是舍不得妹妹出嫁。”
養了十幾年的兒,一朝要嫁去旁人家,父母舍不得乃常理,更何況像韓國公那樣的狂魔。
嬤嬤笑了笑,“舍不得又如何,他不願意放人,明兒早上等姑爺尋上門來,還是得帶走...”
Advertisement
沒工夫再說玩笑話,回頭沖後的一衆仆婦道:“婚服快拿過來,冠,繡鞋,都備好了沒...”
穿婚服前,嬤嬤同韓千君代道:“三娘子最後再去一回淨房,婚服一穿,可就不方便了,得等到明兒拜堂完親,了房方才能更...”
韓千君:......
難怪新娘子出嫁,不能吃東西不能喝水。
憋死人啊。
可奇怪的是,這樣的不方便,沒有哪個新娘子會覺得忍不了。
韓千君也一樣,不吃就不吃,心思全被明日的婚宴勾了去,張又忐忑。婚服已經試過了,第二回穿在上,覺又不一樣,除了驚豔之外,多了一份期待。
天一亮,就要嫁給辛公子了。
想到往後便是他的妻子,兩人會在一起生活一輩子,白日同吃同行,夜裏同床共枕,心頭便不由生出了一子甜,繞繞地纏上來,慢慢地填滿了口,攪著周的,上揚的角怎麽也不住,深深呼出一口氣,眸子底下的興緒蓋不住,溢出來落在眼前的火燭上,照出一抹亮來,滿是期待與向往。
大娘子見差不多了,輕聲問,“千君,明兒夜裏房,可有要問姐姐們的?”
韓千君想說,“我都二嫁了,能不懂?”
突然想起來在船上的那一夜,辛公子是如何對上下其手的,霎時紅了臉,頓了頓道:“姐姐們放心,辛公子,他會...”
很會。
猜你喜歡
-
完結1391 章

醫妃獨步天下
她是當朝帝師的女兒,生父不喜,生母早逝,與當今聖上有婚約,卻被聖上以貌醜失德,無國母風姿為由拒娶。他是手握重權、世襲罔替的異姓王,名震天下、風姿無雙,引無數貴女竟折腰……一紙婚約,她身敗名裂;一場戰爭,他身殘名毀;一道口喻,她嫁他為妻。新婚夜,傳說中命在旦夕、癱瘓在床的男人,將她壓在身下,刀尖抵在她的脖子上,“本王的妻子,本王寧可殺了她,也不會讓人帶走。”“正好,本王妃的男人,本王妃寧可閹了他,也不會讓他碰彆的女人。”有上帝之手美稱的紀雲開,不慌不忙的推開刀,推開身上的男人,卻被男人的反應嚇了一跳!說好的不舉呢?說好的對女人冇有反應呢?男人,你的原則呢?!
250萬字8.18 464089 -
完結17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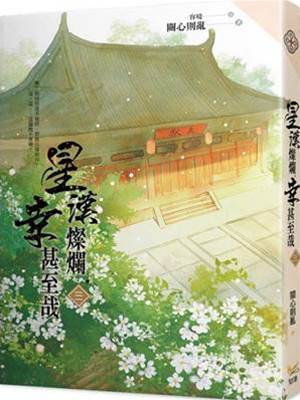
星漢燦爛,幸甚至哉
許多年后,她回望人生,覺得這輩子她投的胎實在比上輩子強多了,那究竟是什麼緣故讓她這樣一個認真生活態度勤懇的人走上如此一條逗逼之路呢? 雖然認真但依舊無能版的文案:依舊是一個小女子的八卦人生,家長里短,細水流長,慢熱。 天雷,狗血,瑪麗蘇,包括男女主在內的大多數角色的人設都不完美,不喜勿入,切記,切記。
90.7萬字8 5631 -
完結137 章

朕的愛妃只想吃瓜
入宮三年,永寧殿美人燕姝未曾見過圣顏。滿宮嬪妃想盡辦法爭寵,唯有她沉浸在吃瓜系統中,無暇他顧。——【臨武侯的世子不是自己的嘖嘖。】【老古板禮部尚書竟與兒媳扒灰!!!】【艾瑪長公主老實巴交的駙馬竟然養了好幾房外室。】每天各路狗血八卦,誰還記得…
54.3萬字8.5 60625 -
完結577 章

重生後,我成了反派的白月光長嫂
上一世,穿越女姜晚澄一步踏錯,淪為王爺後宅妾室。 前有露出真容,將她當做貨物玩意兒的郎君。 後有對她肆意折磨欺辱的主母。 為了自由,姜晚澄慘死窮巷…… 重生後,姜晚澄再一次被那高大威猛,滿臉絡腮鬍的糙漢子獵戶所救。 眼前突然冒出兩個小豆丁! 咦? 這不是未來的大奸臣和絕世妖妃嗎!!? 姜晚澄狂喜:抱大腿,從反派小時候做起! 姜晚澄厚著臉皮留在了獵戶家,做飯、種菜、養雞、采蘑菇。 粘人小妖妃被養得白白嫩嫩。 毒舌小奸臣被馴服的心腹口服。 只是那獵戶變得奇奇...
107.3萬字8.33 1563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