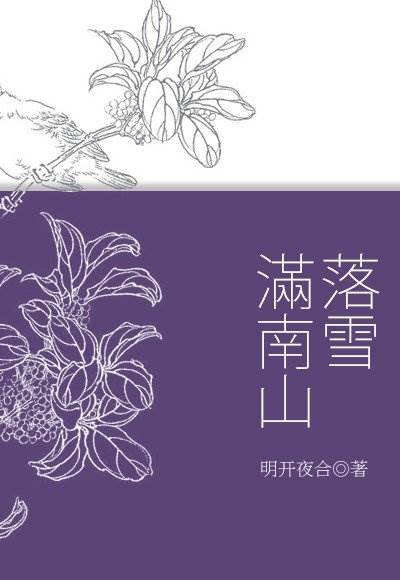《無言之癥》 第1卷 第23章 甲醇
兩個人又坐車回了老家。
兩個人買的是坐票,許彌心好,一路上都在自言自語。他這個人很樂天,自己也能玩的很開心。
“陳荒年,你怎麼突然就想通了?”許彌問他。
陳荒年淡淡道:“我很聽你的話。你不想我殺人,我就不殺。”
“這麼好?”
“嗯。”陳荒年沒說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他害怕許彌把自己搞死了,尸都沒了。他倒是不擔心許彌死了,就怕尸被毀掉了。
“陳荒年,”許彌又他的名字,眼睛亮晶晶的,笑瞇瞇地說,“要擱小說里,我們這就救贖。你心理變態,我年不幸,因為,我們互相救贖。這可是熱門題材呀,寫出來一定會火的。”
“……”
哪想陳荒年驚訝地看著他,說:“我變態?”
“……當我沒說。”
陳荒年說:“我你。”
許彌說:“今天已經說過一次了。”
“這樣嗎?”
“嗯。”
然后陳荒年就笑了,“老婆,我都聽你的。”他所有的退讓和猶豫都是因為許彌,要想擊敗他,只能控制住許彌。
許彌說:“跟我講講你爸的事。”
“以前講過了。”
“講細一點。”許彌說,“我上網查了,他們說你這種心理可能是因為被待,我要查清楚怎麼回事。”
“查這個干什麼?”
“我要救你呀。”
陳荒年無奈地說:“我爸的確打我,但是我高中以后就沒打過了。我媽在我出生的時候,難產死了。聽別人說,我媽在懷我的時候,經常挨我爸打,吃不飽穿不暖,所以才會難產。”
還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帶過去了。
“我都說了,要說的詳細一點!你就沒有什麼悲慘的年想跟我吐槽嗎?”
“沒什麼好說的。”陳荒年他的腦袋,“一些負面緒,我并不想帶給你。”
Advertisement
路途的確遙遠,中午的時候,陳荒年向售貨員買了盒飯。忽然想起什麼,又買了瓶可樂和面包。
許彌知道這是給他買的。陳荒年知道他挑食,火車上的盒飯他肯定吃不慣。
許彌接過可樂喝了一口,氣泡直沖腦門,把他的腦子都給沖清明了。他“嘿”的一聲笑起來,“陳荒年,我懂你怎麼殺他的了!”
陳荒年挑起左眉,不可置否:“嗯?”
“你下毒是不是?”許彌搖了搖手里的可樂,“就跟你知道我喜歡喝可樂一樣,你也知道他喜歡喝酒。你把毒下在酒里,他喝酒的時候就中毒了。你那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就是這個意思。”
“對了一半。”陳荒年看著火車外飛快倒退的景,“下毒很容易被發現的。我沒有下毒。”
“那你怎麼做到的?”
陳荒年說:“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晚上七點多,他們才回到小鎮。陳荒年直奔香火鋪,打開門鉆進去,里面空的,沒有人。
“我爸應該出去打牌了。”陳荒年打開燈,環顧一周,“一會兒他就回來了。”
許彌還是沒搞懂他是怎麼做到完犯罪的,跟在他后,問東問西的,“所以你到底做了什麼?你爸為什麼拖到今天才會死?”
“我說了,我不殺他。你不用著急。”陳荒年帶著他上樓,口氣溫似水,“我答應過你的事,一定會做到的。”
許彌心里居然有點。以陳荒年的人格,讓他放棄殺人,是無比困難的。可是陳荒年愿意為了他放下怨恨,改過自新。
許彌抱住他的腰,滋滋道:“老公,你好我呀。”
陳荒年扯起角笑了笑,沒說話。他走到柜子前,從里面取出一個白的塑料酒桶。他晃了晃,里面裝了半桶散裝白酒。
Advertisement
“你就是用這玩意兒把他殺了?”許彌看了看,“不就是散裝白酒嗎?”
陳荒年打開蓋子,“你聞一下。”
許彌瞳孔地震,“難道你已經研發了通過散發氣味就可以殺人的毒藥!”
“……我要有這水平我還讀什麼大學?”陳荒年拍了他腦袋一下,好笑道,“我說了,我沒下毒。”
許彌湊過去聞了一下,濃烈的酒味撲面而來。他不太會喝酒,不自然地皺了一下鼻子 “就是白酒啊。應該是去酒廠買的燒酒吧。”
“就是這個錯誤的信息源。”陳荒年蓋上蓋子,“這是醇基燃料,甲醇超標,喝一口就死了。”
“啊?”
陳荒年說:“就是甲醇與二甲醚按一定比例配置形的新型燃料,醇醚燃料。部分假酒里面也參雜了甲醇,誤食工業酒就很可能喪命。”他頓了頓,“所以,燒酒本就很容易出現甲醇。”
“等等!”許彌好多年沒讀書了,一下子給他拽專業名詞,他腦子轉不過來,“甲醇……酒是乙醇……啊!你把他的酒給換甲醇了?”
“不是。”陳荒年說,“那樣查起來,我要負刑事責任的。”
他看向那個白塑料瓶,“這是他自己拿回來的。”
“啊?他自己拿回來的?那他怎麼會喝?”
“有人死了,就會吃席。這種小地方就會用到這種醇基燃料。”陳荒年說,“我只是引導了他一下。”
這種醇基燃料的外表和乙醇看上去沒兩樣,氣味相似,喝起來味道也雷同。
這年頭酒貴,陳永言沒幾個錢,舍不得花很多錢去買酒。當吃完了席,他看見有這麼大的一瓶“散裝白酒”放在那,他自然會悄悄地走。
當他把他之前的酒喝完了,就會來喝這瓶致命的“白酒”。
Advertisement
而那時候,離那場席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無可追查。陳荒年也遠在天邊,沒有作案時機。
陳永言獨自在家,人緣又不好,起碼要死了好幾天才會被人發現。大概率會被判定酒中毒死亡。
就算警方真的追查起來,也只能查出他甲醇超標。但是這酒,是他自己回來的,沒有人他。
只能說他自作孽,不可活。
而最后陳荒年作為唯一的直系親屬,只需要表示不追查,那麼這場案件就會直接翻篇。
真正的完犯罪,就是本沒有立案。
許彌后背發涼,他沒想到陳荒年在這場謀殺里,居然只需要站在那,微微一笑,就完了殺人。
所以,就算后面有人察覺到不對勁兒,也沒辦法定罪。因為陳荒年就只是站在那里而已,他連話都沒說,連教唆自殺這個罪名都沒辦法定下。
哪怕許彌已經知道了前因后果,他還是覺得,這場謀殺,更像是一場無法避免的意外。
陳荒年利用的是人的弱點。就像他寫下的那句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陳荒年去買了新的白酒,替換了瓶子里醇基燃料。見到許彌還用那種懷疑的眼神看他,他就自己喝了一口,冷漠道:“我答應了你,就不會殺人。你別這樣防著我。”
他抿著,眼神黯淡:“許彌,你這樣看我,我很傷心。我沒有騙過你。”
見他都代了手法,許彌心神一,抱住他,著嗓子說:“對不起嘛老公,我……我害怕呀。我不會懷疑你了,對不起。”
陳荒年似乎是生氣了,不肯再說話。
他一生氣就這樣,什麼都憋著,死活不說話。許彌心里打著鼓,小心翼翼地親親他,“老公?你生氣啦?我就是問一問嘛,沒別的意思。”
他們兩個從來沒有過信任危機。
陳荒年冷著臉帶著他下樓,關上門,晚上八點過,兩個人離開了這個小鎮。
回程的火車票在半夜三點。
這天晚上陳荒年不愿意再抱著他睡覺,顯然是給氣得夠嗆,寧愿自己一個人睡,也不要跟許彌說一句話。
許彌沒有他陪著,是真的睡不著。
他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為。
人家陳荒年都讓步了,他干嘛還去質疑陳荒年呢?這下好了吧,搞出個信任危機。
許彌想爬上陳荒年的床,但是陳荒年出一只手,抵住了他的口,眼神冷淡,用態度表明了不想和他一起睡覺。
是許彌離不開陳荒年,不是陳荒年離不開許彌。
許彌,干笑道:“老公,你忍心看我整夜失眠嗎?”
“反正你都不信我。”陳荒年說,“你不怕我半夜爬起來把你殺了?”
“不會的,老公,你最好了。”許彌不死心地繼續爬床,鐵質的小床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
旁邊的乘客吼了一句:“別他媽弄得響!大半夜讓不讓人睡覺啊!”
許彌被吼了,心里也生氣了,著嗓子,憤憤不平道:“你不抱著我睡覺,我下站就下車,你就找不到我了。”
聽了這話,陳荒年才手攬住他的腰,把他拉上床,錮在自己懷抱里。許彌親昵地蹭蹭他,也不生氣了,好聲好氣地說:“老公,我知道錯了。我以后都不會質疑你了。我相信你。”
陳荒年悶悶的,“真的?”
“嗯。”許彌點點頭,“我一定不會再質疑你了。”
然而在黑暗里,陳荒年不經意地出一個沉的笑容。
果然,許彌雖然已經離不開他了,但總會有離他掌控的趨勢。不過經歷了這件事以后,許彌應該會無條件信他說的話。
再說了,他只是答應了不殺陳永言。
但他沒說過,陳永言不會死啊。
猜你喜歡
-
連載1502 章
秘愛
是她太傻,太天真,母親慘死渣男之手,她竟不知,要不是抓到他與表妹的廝混,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心,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她恨,可她無能無力,只能出賣靈魂,與惡魔做交易。
288.1萬字5 27959 -
完結351 章

重生八零改嫁鄉野糙漢
重生后,喬聽南才知道上輩子陷害她被捉奸在床的幕后黑手是她未婚夫。弄瞎她雙眼,毀她家庭,害她橫死街頭的人是她的好姐妹。一朝重生,喬聽南誓要讓他們自食惡果生不如死。咦?那個身強體壯的鄉野糙漢為何每次見她都面紅耳赤?不僅幫她報復渣男賤女,還數次救她于危難。知她退婚無處可去,鄉野糙漢把她堵在墻角掏出戶口本和全部家當對她說:“我們假結婚,我養你。”喂,不是說好假結婚嗎?你每晚給我打洗腳水像個癡漢似的捧著我的腳做什麼?假結婚你為什麼要上我的床,鉆我被窩?等肚子一天天鼓起來,她才意識到自己被這個外表憨厚內里...
65.4萬字8.18 29648 -
完結431 章

強撩!暗戀!總統閣下他溫柔低哄
(婚禮現場隨機嫁夫我成為總統夫人)(暗戀,先婚后愛)傳聞寧家那個從小走丟,在鄉下長大還鬧了滿身笑話的寧大小姐愛了京城第一貴公子沈慕白很多年,愛的轟轟烈烈,愛的不可自拔。可是兩家聯姻當天,沈慕白卻當眾拋下新娘,去追尋他的白月光。一時間,寧大小姐成為上流圈笑柄。眾人幸災樂禍,只道那個鄉下土包子純純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活該有此下場。可沒想到……她轉身就嫁了旁人,反將了沈慕白一軍。在排除掉所有上流圈子弟後,眾人又笑:沒了京城第一貴公子,怕是也只有圈外下九流無名之輩願娶這種聲名狼藉的女人。
58.9萬字8.46 65454 -
完結6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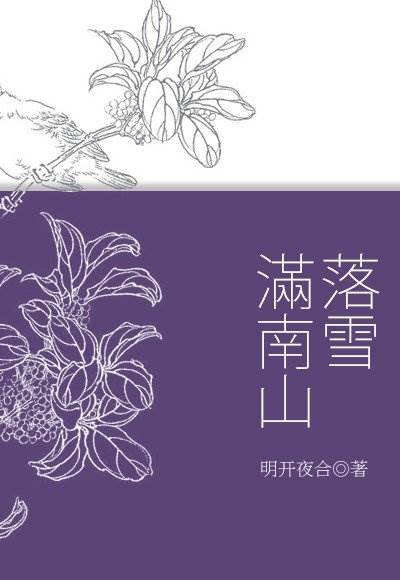
落雪滿南山
[小說圖](非必要) 作品簡介(文案): 清酒映燈火,落雪滿南山。 他用閱歷和時間,寬容她的幼稚和魯莽。 高校副教授。 十歲年齡差。溫暖,無虐。 其他作品:
18.5萬字8 2384 -
完結149 章

婚后熱戀
溫吟覺得沈初霽這人風流又薄情,婚后他能對外面任何女人發情,卻唯獨對她性冷淡。她兩年的婚姻里沒有一日三餐的煙火氣,沒有老公的親親抱抱,更沒有夫妻生活,活的像寡婦。
30.2萬字8.17 347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