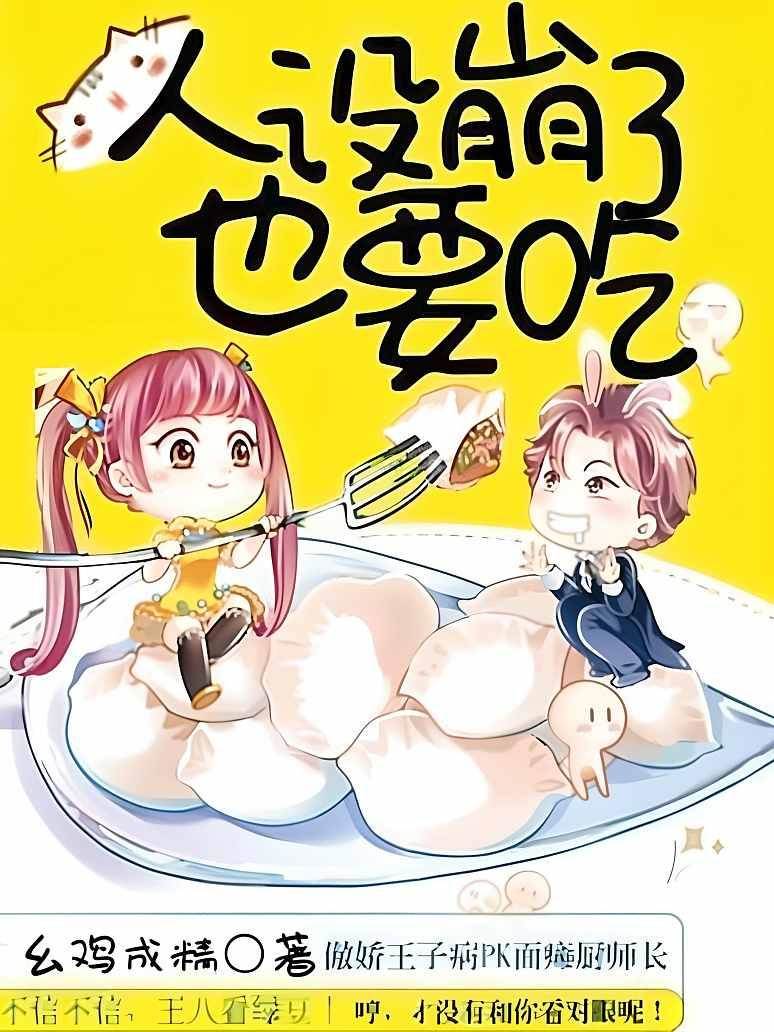《偏寵入婚》 第24章 “手都在抖,還說沒慫?”
原叢荊坐回對面。
他抱起雙臂,沒說話,眼神溫淡,看著。
他很喜歡看吃東西。
跟相時,也會故意引,因為對食的,是未經釋放的,他一直都知道,其實很想暴食,也總會流貪婪。
節制的食,是束縛的繩索,以至于,吃塊蛋糕,都覺罪惡,小口吃東西的模樣,像只想要振翅,卻陷厚繭,不斷掙紮的蝴蝶。
他心髒漲漲,像被的角踩了幾下,傳遞出嗞啦嗞啦的電流,有種不控制的塌陷,讓大腦也發暈,仿佛掉進制造棉花糖的機,但他甘願,被那些旋轉的糖網羅。
因為那些狂熱的愉悅,讓他的理智,都快要炸開。
他確實很開心。
甚至,可以說是,從來都沒有這麽快樂過,他的小青梅,他的丸丸,竟然為了他的人,他的妻子。
從出生,到現在,他只覺得,靈魂被錮在這個牢籠裏,無法掙,包圍他的是無邊的虛妄,混沌的黑暗。
沒有人能理解這種痛苦。
連他那個所謂的父親,都冷漠又厭惡地他小怪。
什麽都很無聊,什麽都很礙眼。
他想毀掉一切,包括他自己。
拋棄他的這五年,他更如被放逐荒島,過著流浪又無依的生活。
不斷被想強奪的念頭拉扯,不斷被想霸占的惡侵蝕,但從今天開始,他終于可以在的土壤牢牢紮。
那些需索,慕,就像不斷延的藤蔓,有著向,本能就會趨向,他甚至想將纏繞絞-,再也不松開。
對的,摻雜了親,友,,但無論是哪一種,他都能確定。
那是亙古不變的意。
這份意,讓他的存在有了意義,也有了信仰,這份意,也讓他一念是天堂,一念是地獄,因為,既能予他極樂,也能判他死刑。
Advertisement
婚姻讓這份意,有了實。
他終于可以明正大地去。
他還是不信所謂的宿命,回,轉世,但也不會再生出,讓毀滅的念頭。
只恨這一世的時間不夠長,他用這副靈魂,這份意志,更久,更久,更久。
其實好想跟有個正式的婚禮。
但又怕,繁瑣的儀式會讓退。
好想看穿上潔白的婚紗。
他想對說,無論順境、逆境;無論富裕、貧窮;無論健康、疾病,他們都會相相守,他也永遠會對忠誠。
也想跟舉行中式婚禮。
他想為揭下紅蓋頭,喝杯酒,對說,死生契闊,與子說。
更想親自為挑選婚戒。
那枚小小的鐵環,將會是他們締結契約的堅固信,但又擔憂,的手指會勒出紅痕。
既想束縛,又怕弄痛。
購買婚房,也讓他興。
因為終于可以名正言順,跟住在一起。
還記得小時候,大人們為了一些目的,讓他住進的家裏,他們好像說過,是擁有超強共力的孩。
一開始,他覺得,住哪裏都無所謂,但到了即將被送走的那幾日,才格外不舍。
分別的那天,孩紅著眼眶,跑過來,不顧大人的阻攔,用兩條纖細的小胳膊,抱住他,邊哭鼻子,邊哽咽說:“阿荊,你要等我,我一定會想辦法,再找到你的。”
他到了滿漲的哀傷和心痛,悶悶地說:“我也一定會再找到你的。”
今天,尹棘為了他的妻子。
的暗面,的挫折,的脆弱,的缺點,的敏,和時常令他惱火,卻又心疼的愚善,都屬于他了。
包括右手拇指上,那塊小小的,月牙狀的疤痕,也屬于他了。
的自由,的夢想全部都屬于他。
Advertisement
再也不要跟分開。
就算再次選擇拋棄他,也別想跟他分開。
他要守護的一切。
雖然擺不掉,對的貪婪和念,但為了守護對的意,也為了守護予他的恩賜。
他要修行,他要持戒。
-
一場秋雨一場寒。
進十一月後,溫度驟降,柏油路被冷雨浸泡,泛黃的樹葉也枯敗,湫隘積水貯存起大都市獨有的氣息,熱意褪散的瀝青,濁重灰白的尾氣,生發腥的金屬。
于阮明希而言,晚秋的氣息,是打印機的油墨味,也是令心安的,職人速溶咖啡的苦味。
尹棘是今晚九點的飛機。
阮明希本想去送,但尹棘說,從機場回市區很不方便,沒必要折騰一趟。
等順利落地,會第一時間跟報平安,還要跟說說,最近發生的一件大事,希不會太震驚。
上午,跑了趟法院。
坐出租車通勤時,還用微信,遠程幫委托人填好了送達地址確認書。
回到公寓後。
阮明希收到母親發給的幾條微信——
【明希,我和你爸爸想好了。】
【二環的一切是很繁華,但那些繁華,跟我們這種普通百姓沒什麽關系。大雜院住了那麽多年,我們的年齡也大了,不想再住在擁的平房,連廁所都是公共的,冬天真的很不方便。】
【上頭承諾會分的房子,雖然在五環,但有一百平,還有電梯,小區的綠化也很好。】
【我和你爸爸決定同意拆遷。】
【這麽多年,爸爸媽媽沒有給你提供好的條件,也知道你一直都很努力,很上進,沒花錢補課,就考上了政法大學,還在畢業後,考下了律師執照,爸爸媽媽很為你驕傲,也覺得很對不起你。】
【審批結束後,還會分到一筆拆遷款,大概有三百多萬,到時候,我們會將錢轉贈給你。】
Advertisement
【五環的那套房子,我們也會在房産證寫你的名字,算作你婚前的財産,反正我們不在了後,也都是你的。】
【雖然跟有錢人家的孩子沒法比,但至,這筆錢,可以讓你在這座城市裏,更有底氣。】
【如果不想再看老板臉,也能隨時走人,留學也好,還是像你們年輕人最近流行的gap year,休息一年,旅旅游也罷。你的人生,也能有更多的選擇,可以松弛些了。】
【我們能為你做的,也只有這麽多了。】
阮明希低睫,熄滅手機屏幕。
沒有立即回複母親的消息,嘆了口氣,眼眶有些發熱,下風,搭在椅背。
沒想到,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的人生也和尹棘一樣,將要迎來巨大的改變,但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
阮明希走到辦公桌前。
看見那本舊手賬後,表微怔,隨即將它拿起,走進尹棘的臥室。
房間僅剩一床一桌,空空。
心底也生,有種難言的傷,蔓延開來,很像從前,父母不準養撿回來的流浪小貓,送走,不舍又悲哀。
阮明希吸了吸鼻子。
尹棘同的親人無異,但清楚,這種大城市合租的室友關系,早晚都會終止,只是沒想到,這一天,會來得這麽快。
雖然生在這個城市的三環,卻住在大雜院的一間矮房裏,擁有這個城市的戶口,卻買不起這個城市的房子。
從小,全家就祈盼,那間矮房能夠遷,但總是抓不住政策的尾,也總是與改變人生的機遇肩而過。
家裏將本就狹窄的矮房,又拓出一個空間,開了家羊面館。
尹棘高中時的舞室,就在面館附近,總來吃面,每次,只要四分之一的面條,連湯都不敢多喝,還對媽媽說,們家的羊面跟老家的很像,可以加煮得爛的白菜。
沒有能夠安靜學習的獨立空間,只能在店裏油膩的木桌上,做卷子,寫作業,對環境的不滿和憤恨,給了向上的驅力,暗暗發誓,一定要考上理想的大學,也一定要擁有屬于自己的房間。
但過于爭強好勝的格,讓一直沒有親近的朋友,也覺得,自己不需要朋友。
考第一,是唯一的目標,篤信,站在頂峰上的人,必然孤獨。
直到尹棘的出現。
孩藝生的氣質很明顯,相貌也,原以為,會不好相,但尹棘對有種天然的親近,每次來店裏,都會熱跟打招呼。
尹棘很認真地問過數學題,為了謝的幫助,還買過很多甜食送,說,自己不能吃這些食,希替嘗一嘗。
或許友跟一樣,也要靠緣分,從那時開始,終于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朋友。
雖然舍不得,卻又由衷為高興,因為尹棘終于擺了那些束縛,這也讓覺得,自己的未來,有了明和希。
剛平複好緒。
就聽見一陣門鈴聲。
阮明希不免覺得奇怪。
這個時間,誰會敲門?那人又沒有出聲,并不像是快遞員,或是查煤氣的。
“誰啊?”過貓眼,看了看外面,呼吸忽然一滯,難以置信地張了張。
男人的語氣平靜又溫和:“打擾了,我想找尹棘。”
猜你喜歡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155 章
她不乖!要哄
【爆甜輕松 雙潔治愈 野性甜寵 校園】【嬌縱隨性大小姐x邪妄傲嬌野少爺】“疼!你別碰我了……”季書怡微紅的眼圈濕霧霧的瞪著頭頂的‘大狼狗’,幽怨的吸了吸鼻子:“你就會欺負我!”都說京大法學系的江丞,眼高于頂邪妄毒舌,從不屑與任何人打交道,只有季書怡知道背地里他是怎樣誘哄著把她藏在少年寬大的外套下吻的難舍難分。開學第一天,季書怡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惹了江丞不爽。所有人都以為她要完。可后來眾人看到的是,大魔王為愛低頭的輕哄:“小祖宗,哪又惹你不高興了?”季書怡永遠記得那個夜晚,尋遍了世界來哄她的江丞跪在滿地荊棘玫瑰的雪夜里,放下一身傲骨眉眼間染盡了卑微,望著站在燈光下的她小心翼翼的開口:“美麗的仙女請求讓我這愚蠢的凡人許個愿吧。”她仰著下巴,高高在上:“仙女準你先說說看。”他說:“想哄你……一輩子。”那個雪夜,江丞背著她走了很遠很遠,在他背上嬌怨:“你以后不許欺負我。”“好,不欺負。”——————如果可以預見未來,當初一定不欺負你,從此只為你一人時刻破例。你如星辰落入人間,是我猝不及防的心動。
24.2萬字8 17171 -
完結1206 章

相親當天,閃婚了個億萬富翁
【甜寵+先婚后愛+傲嬌男主】 相親當天就鬧了個大烏龍,安淺嫁錯人了。 不過,錯有錯著,本以為一場誤會的閃婚會讓兩人相敬如賓到離婚,安淺卻驚訝地發現婚后生活別有洞天。 她遇到刁難,他出面擺平。 她遇到不公對待,他出面維護。 安淺天真的以為自己嫁了個錦鯉老公,讓她轉運,卻萬萬沒想到,自己嫁的竟然是億萬富翁!
192萬字8.18 17167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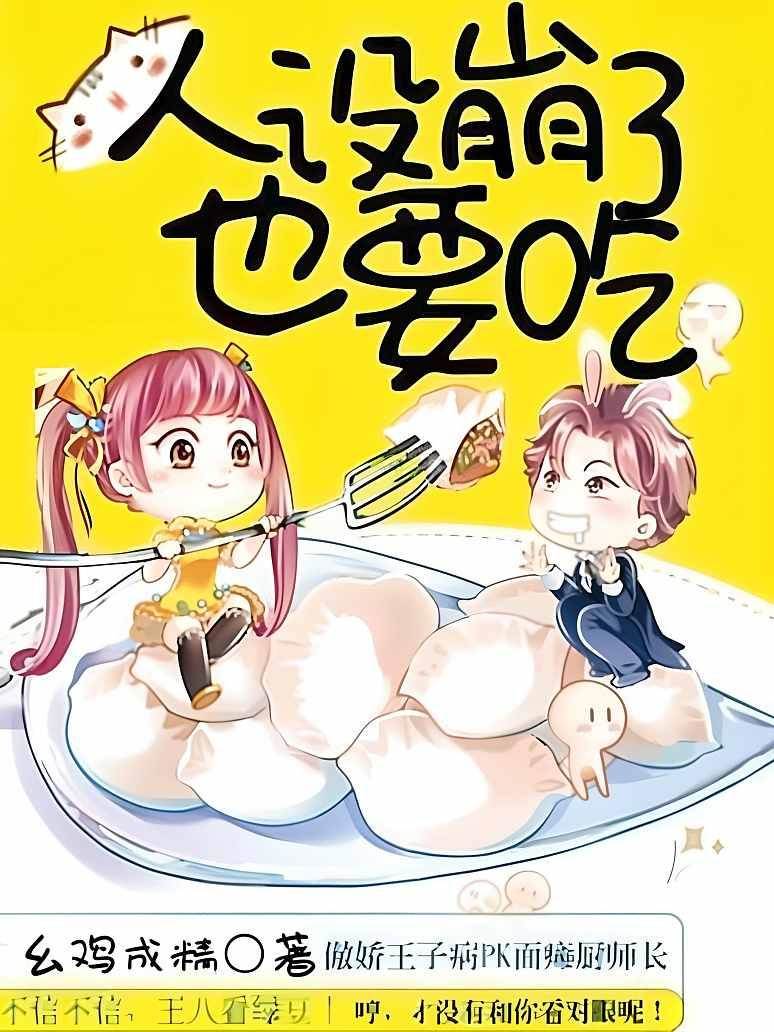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