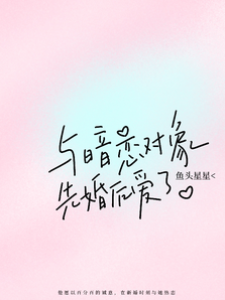《乖乖入局,驕肆大佬無處不低頭》 第1卷 第159章 我哥來了!
謝輕舟的臉有一瞬間的波。
孩兒纖的曲線半掩在垂落的藤條中,頭上還頂了幾顆葉子,笑起來眼睛亮亮的,著可的小梨渦,像是忽然闖進來的過堂風。
他羽睫輕,冷臉轉回頭。
“你有點兒煩人了。”
賀知意聞言,燦爛的笑意緩緩收回,哦了一聲:“那我走了。”
謝輕舟薄啟開,沒說話,也沒轉頭,余瞄見人影消失,有些煩躁的重新甩著打火機,像是后悔剛才說那句話了。
大破。
但下一秒,另一側的藤條嘩啦作響。
賀知意再次探:“謝輕舟——”
謝輕舟兀自勾,細微的弧度帶著一暗爽。
賀知意大大方方的走過來,往他邊一坐,右臂順勢‘哥倆好’般搭在他的肩頭,學著他天,煞有介事的說:“賞月怎麼能不我呢?”
謝輕舟目右移,瞧著白的手指,提著袖子將的手臂甩開,還順勢抖了一下肩膀:“天上就這麼一個月亮,不夠分。”
賀知意:“咱倆一人一半不就得了。”
謝輕舟被逗笑了,掏了顆煙,卻被賀知意走彈飛。
“……”
“點兒吧,嗆死了。”賀知意強調,“我哥都戒煙了。”
謝輕舟嘖了一聲,又取了一顆。
賀斂還能戒煙?
賀知意再次手,卻見謝輕舟舉起手臂,瞪著眼,抓著他的手腕往下拼死用力,卻奈何不了分毫,索一把將邊的打火機扔的老遠。
Advertisement
“……”謝輕舟,“祖宗,你知道我的打火機多貴嗎?”
“不煙,不知道。”
他沉了口氣,把煙盒收了起來。
好在車里還有打火機。
不過,這麼一會兒不煙也死不了。
“我說草莓蛋糕。”謝輕舟偏過頭,孩兒的發撲來一抹清香,他怔了一下才又說,“你老跟著我干什麼?”
賀知意把玩著藤條,漫不經心的回答著:“這是我哥的地盤,本姑去哪兒還用躲著你嗎?”
謝輕舟挑眉:“真就一點兒都不怕我?”
“不怕啊。”
“呵呵。”
謝輕舟輕笑兩聲,沒再說話,就這麼跟坐著。
春夜的風吹拂而來,掃的周遭沙沙作響,但好像沒剛才那麼冷了。
賀知意將那藤條上的葉子全都扯掉,有些無聊的著:“謝輕舟。”
“嗯?”
“你剛才念得那句詩。”賀知意撐著手臂,語氣有些別扭,“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渠,你該不會有喜歡的人了吧?”
沒抬頭,視線定格在謝輕舟的手上。
他的手指關節很細,很長,皮不算白,虎口有道很可怖的舊疤,像是險些被豁開,指甲修剪的很齊整也很干凈,中指戴著一枚黑戒指,寬度一厘米左右,朋克風,帶著蝴蝶翅膀的圖案。
等了等,耳邊才傳來謝輕舟冷淡的嗓音:“沒有。”
“哦。”
賀知意把頭轉去反方向。
謝輕舟這才悄然轉頭,盯著賀知意的耳朵。
Advertisement
孩兒的耳朵廓很小巧,因著皮過于,時能看到細微的管,耳垂墜著一顆做工致的珍珠飾品。
好像很喜歡這枚耳飾。
有什麼特殊含義?
別人送的?
“你呢?”
謝輕舟突然反問。
“什麼。”
“你有喜歡的人嗎?”
賀知意背對著他搖頭。
謝輕舟的表始終沒什麼變化,將要移開目,卻見賀知意又點了點頭。
他倏地頓住。
賀知意的聲線有些尷尬,故作沉的拉長聲:“算喜歡吧。”
說完猛地回頭,謝輕舟躲閃不及,整個人都僵了一瞬,繼而才皮笑不笑的哼了兩聲,有些不屑的說:“那個人還倒霉的。”
“你!”
賀知意揚起拳頭。
謝輕舟沒躲,睨著,眼尾毫不含溫度。
不知道怎麼的,賀知意覺得他好像有點兒生氣了。
鼓了鼓臉頰,把拳頭收了回來:“姑我今天心好,不和你一般見識。”
“呵。”謝輕舟眼譏諷,“心好?今天你喜歡的人也來了?”
賀知意揚聲:“對啊。”
“是,是我忘了。”
謝輕舟口吻無。
沒錯,說好的寸步不離,怎麼可能沒來。
賀知意狐疑的盯著他。
謝輕舟不耐煩的蹙眉:“既然他在,那你去找他啊。”
賀知意跟他一起蹙眉:“你管我呢?”
謝輕舟又不說話了,只是眉眼間的狷狂在煩惱時更加明顯,甚至眼瞼還浮出了一紅線,是嗤之以鼻的態度:“是,誰能管得了啊,祖宗。”
Advertisement
賀知意咬,不知道他怎麼變臉變得這麼快,只是見謝輕舟緒不好,也生出些低落。
想了想,從架子頂上拽了兩顆青的葡萄下來,放進自己里一顆,酸的整張臉都急集合。
但很快調整好,了謝輕舟的胳膊,將另一顆遞給他。
“嘗嘗,可甜了。”
謝輕舟接過直接扔進里,咀嚼兩下。
“……”
他抿著,咽了下去。
賀知意促狹的探頭:“甜不甜?”
謝輕舟:“甜。”
“啊?”賀知意不死心,“真甜?”
“甜。”
他這樣冷淡的態度讓賀知意覺得,里殘留的葡萄味道更酸了。
不過既然謝輕舟懶得理自己,也不想在這里繼續自討沒趣,垂頭喪腦的起說:“那我走了。”
謝輕舟未,目卻跟著的影右移。
賀知意將麻麻的藤條撥開一個小兒,剛要邁步,眼睛陡然瞪大,一個箭步折返回來,用盡最大的氣聲驚呼:“我哥來了!”
謝輕舟也是一驚,不等想辦法,賀知意猛地竄進他的懷里,他也下意識的將風扯開,遮住的子,把的腦袋按在心口。
他謹慎揚聲:“賀斂!”
外面的腳步聲停住。
接著是賀斂帶著疑的聲線。
“你他媽開天眼了?!”
“老子是聞到你的壞味兒了,跟爛葡萄似的。”
謝輕舟說完,低頭看著懷里的人。
賀知意死死的埋著頭,那的雙臂在服環著他的腰,整個人像八爪魚一樣,致使兩人之間不留一隙。
子好,靠得好近。
心跳好快。
謝輕舟的腦袋有些混。
可突然,右側傳來嘩啦聲。
賀斂撥開藤條,在遠探頭:“你干什麼呢?”
月被頭頂的葉遮住,種植廊里的線并不好,他老遠只能瞧見謝輕舟的懷里鼓鼓囊囊的,好像有個人。
但這種況下,別說認出來,就是男也不好判斷。
賀斂口吻輕佻:“談呢?”
謝輕舟摟著賀知意的腰,當著他的面往懷里又帶了帶,聲音僵:“對啊,咋的吧,老子還不能談個朋友了?”
賀知意聽到這話,耳悄然燒紅,想在他腰上擰一把,又怕靜太大被哥發現,只好保持一不的姿勢。
只是……
這才想起來。
這件駝的風,好像是自己上次給他挑的那件。
猜你喜歡
-
完結2307 章

獨家蜜婚:陸少的心尖寵妻
第一次相親,就被他拐進民政局連夜扯了證,婚後才發現他竟然是堂堂的陸家長孫,全國數一數二的陸氏集團的首席總裁。她隻想找個平凡男人過平凡日子,冇想要嫁個身世駭人的大總裁啊!“夫人,既然已經上了賊船,那就冇法再下去了,還是老老實實跟我一起努力造人吧。”麵對她的懊喪,他笑著將她摟入懷中,深深吻住。她情不自禁地淪陷在他的柔情中。原以為婚姻不過是一場豪賭,卻不料這場豪賭如此暖人心脾,讓她甘之如飴。
407.3萬字8 673126 -
連載52 章

超甜!墨爺的小祖宗又美又颯
【馬甲+團寵+微玄幻+古武+異世】夏煙重活一世,不想努力了,只想做個寵老公,愛老公,天天在老公懷里嚶嚶嚶的小嬌嬌。但在所有人眼里,夏煙不學無術,一無事成。廢柴?草包?網上罵聲一片,“墨爺有錢有顏配你,簡直是暴殄天物。”當即,夏煙甩出她的重重…
9.4萬字8.18 8213 -
完結213 章
生崽痛哭:豪門老男人低聲輕哄
【年齡差11歲+霸總+孤女+甜寵+無底線的疼愛+越寵越作的小可愛】 外界傳言,華都第一豪門世家蘇墨卿喜歡男人,只因他三十歲不曾有過一段感情,連身邊的助理秘書都是男的。 直到某天蘇墨卿堂而皇之的抱著一個女孩來到了公司。從此以后,蘇墨卿墮落凡塵。可以蹲下為她穿鞋,可以抱著她喂她吃飯,就連睡覺也要給她催眠曲。 白遲遲在酒吧誤喝了一杯酒,稀里糊涂找了個順眼的男人一夜春宵。 一個月以后—— 醫生:你懷孕了。 白遲遲:風太大,你說什麼沒有聽見。 醫生:你懷孕了! 蘇墨卿損友發現最近好友怎麼都叫不出家門了,他們氣勢洶洶的找上門質問。 “蘇墨卿,你丫的躲家里干嘛呢?” 老男人蘇墨卿一手拿著切好的蘋果,一手拿著甜滋滋的車厘子追在白遲遲身后大喊,“祖宗!別跑,小心孩子!” 【19歲孩子氣濃郁的白遲遲×30歲爹系老公蘇墨卿】 注意事項:1.女主生完孩子會回去讀書。 2.不合理的安排為劇情服務。 3.絕對不虐,女主哭一聲,讓霸總出來打作者一頓。 4.無底線的寵愛,女主要什麼給什麼。 5.男主一見鐘情,感情加速發展。 無腦甜文,不甜砍我!
39.3萬字8 14199 -
完結803 章

煙視媚行
早知道邢錚是披著衣冠的禽獸,林湄一定不會自不量力去敲他的房門。那夜之後,她便落入他精心設計的陷阱中,被他啃得骨頭渣都不剩。
143.9萬字8.18 5961 -
連載810 章

禁止相親!薄總夜夜跪地求名分
【假斯文真敗類VS人間尤物黑蓮花,雙潔,甜寵,1V1,HE】應如願跟著媽媽進入薄家,成了最透明又最引人注意的應小姐。她沒有身份,上不得臺麵,是最物美價廉的聯姻工具。她太美貌,太弱勢,老老少少都如狼似虎地盯著她,用盡手段想占有她。為求自保,她主動招惹了群狼之首薄聿珩,喊了一夜的“聿哥”,天亮後以為錢貨兩訖,他能保她平安離開薄家。萬萬沒想到,男人夜夜進入她房間,拉開領帶捆住她:“妹妹,酬勞是日結。”
94.7萬字8.18 69627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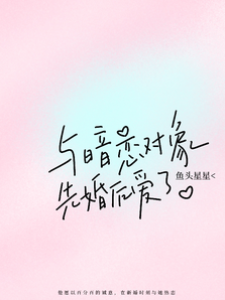
與暗戀對象先婚后愛了
【清冷美人×桀驁貴公子】江疏月性子寡淡,不喜歡與人打交道,就連父母也對她的淡漠感到無奈,時常指責。 對此她一直清楚,父母指責只是單純不喜歡她,喜歡的是那個在江家長大的養女,而不是她這個半路被接回來的親生女兒。 二十五歲那年,她和父母做了場交易——答應聯姻,條件是:永遠不要對她的生活指手畫腳。 _ 聯姻對象是圈內赫赫有名的貴公子商寂,傳聞他性子桀驁,眼高于頂,是個看我不服就滾的主兒。 他與她是兩個世界的人,江疏月知道自己的性子不討喜,這段婚姻,她接受相敬如賓。 兩人一拍即合,只談婚姻,不談感情。 要求只有一個:以后吵架再怎麼生氣,也不能提離婚。 _ 本以為是互不干擾領過證的同居床友。 只是后來一次吵架,素來冷淡的江疏月被氣得眼眶通紅,忍住情緒沒提離婚,只是一晚上沒理他。 深夜,江疏月背對著,離他遠遠的。 商寂主動湊過去,抱著她柔聲輕哄,給她抹眼淚,嗓音帶著懊悔:“別哭了,祖宗。” _ 他一直以為自己與妻子是家族聯姻的幸運兒,直到有一天在她的書中找到一封情書,字跡娟秀,赫然寫著—— 【致不可能的你,今年是決定不喜歡你的第五年。】 立意:以經營婚姻之名好好相愛 【先婚后愛×雙潔×日久生情】
26.1萬字8 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