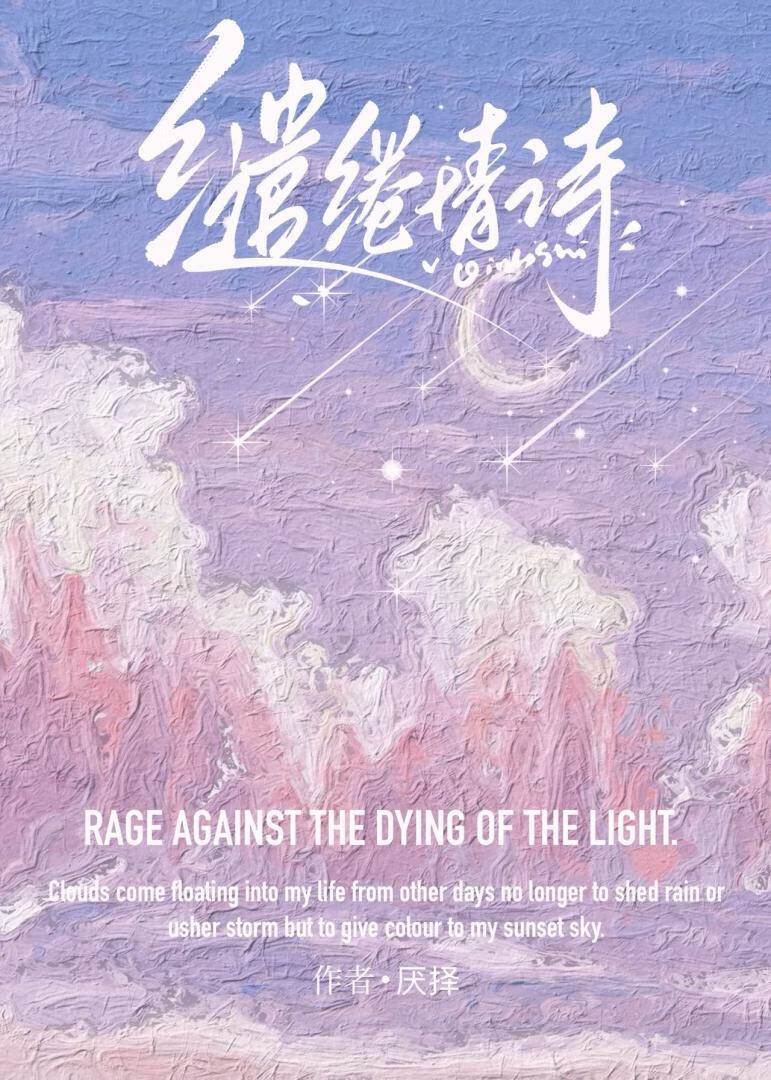《替身夫人死后,薄總瘋了》 第1卷 第175章:下輩子還要在一起
獄友看著他咳得滿臉漲紅,問道,“你沒事吧?我看你進來到現在沒多久,咳了好幾次了,你該不會是不適應這環境,才這樣吧?不過確實,這種環境只有我們從小吃苦的窮人才待得下去,我看你應該家境好的。”
另外一位獄友,“家境好又怎樣?一般有錢人都容易做錯事,走錯路,仗著自己有幾個臭錢,就可以為所為。”
“你這邏輯不對,沒錢才容易做錯事,因為人的賺錢能力是跟思維掛鉤的,人賺不到認知以外的錢,所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功名就,容易使用不正當的手段,走上歪路。”
“害,不管有錢沒錢,進來這里,大家的境和份都是一樣的,你在外面多風,進來之后,不也一樣是個勞改犯?”
那人瞧了一眼薄司寒,“你說是不是兄弟?所以也別分什麼高低貴賤了,在這里我們大家都是難兄難弟。”
薄司寒緩了緩,“我不是什麼風的人,我只是一個凡人罷了。”
“不可能,我怎麼見你越看越眼啊?好像在哪里見過?”
那人絞盡腦地想著。
薄司寒輕描淡寫地回了一句,“大眾臉。”
“不可能!你這張臉絕對不平凡,我想起來了!你好像是那個什麼薄氏集團的總裁?是吧?我在電視上見過你。”
Advertisement
薄司寒沒吭聲,算是默認了。
那位獄友頓時就來勁了,跟他聊了起來,“話說,兄弟,我還沒驗過有錢人的生活呢,你跟我分分唄,有錢應該沒煩惱吧。”
薄司寒告訴他,“不,你理解錯了,其實有錢人的煩惱更多,力更大,而且,還不盡人意。有錢人只是錢多罷了。”
“都有錢了還愁啥啊,要是我有錢,人一天一換,沒有錢買不來的。”
薄司寒笑著搖頭,“你不懂,每個人的追求不一樣,我只想要一個彼此相陪我度過一生的人。”
“兄弟,沒想到你堂堂公司總裁,也會有這麼深的一面。”
薄司寒嘆了嘆氣,“可惜我的那個已經不在了。”
那位獄友湊近拍了拍他的肩膀,“看開點兄弟,等出去了,一切從頭開始。”
薄司寒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有生之年,會淪落到這副田地,跟一幫勞改犯在這里討論人生,談論。
真是可笑。
他怎麼會活這樣啊!
等出去從頭開始,薄司寒想著,恐怕他再也不能出去了。
到了晚上,深夜之時。
牢房里的人倒頭就睡,千奇百怪的睡姿,呼嚕聲也有。
薄司寒皺眉,這群人怎麼睡得著,只有他無比清醒。
銳利的眼眸在黑暗中出絕和痛苦,增添了幾分黯淡。
Advertisement
薄司寒著狹窄的牢籠,他此時就像一只被折斷翅膀的雄鷹一樣。
他一想到溫言,心口就絞痛。他的小言,當年被他無地送監獄,薄司寒一想到在無數個充滿期盼又絕的夜晚中,懷著孕,到底是怎麼熬過來的。
一定經常哭,也很抑郁,孕期各種不適的反應,一定也有,直到生產的那一天,又是做了多久的心里準備,才會不顧一切,冒著生命危險,不顧以后的艱辛,選擇生下這個孩子,又是怎樣一把手養襁褓之中的嬰兒長大。
直到出獄,牽著那個四歲的小男孩重見天日,那一刻,走出監獄的那一刻,薄司寒未曾看到,曾經有什麼樣的心境。
漆黑的夜晚,以前薄司寒在家失眠時,還可以站在窗前賞月,著夜空中的星星。
但現在,他抬頭,只能看見發黃且骯臟的天花板,再低頭,只有那扇閉且腐朽的鐵門。
這就是他的境,也是溫言曾經的境。
他在走走過的路,在牢里生育孩子,他去分.娩驗中心過了。
坐牢,他也坐牢。
牢房里,蟑螂老鼠出沒是正常不過的事,還有各種各樣的小蟲子,更讓他不了的是,這里面有一種怪味。
他只能認命地接這一切,這是他應有的報應。
Advertisement
薄司寒又想咳嗽了,但是怕吵醒獄友,于是他盡力憋著,用手捂住了,把那陣不適強行了下去。
實在忍不住了,他才背過去,靠著墻,小聲地咳幾聲,緩解不適。
薄司寒自己都想不到,有一天,他也會為別人著想,咳個嗽都得小心翼翼。
他此刻心抑、痛苦、煎熬,以前,他會借用喝酒和煙來緩解緒,用酒把自己麻痹,喝得爛醉然后睡一覺。
即使第二天起來頭暈得要命,但起碼昨晚睡著了。
現在,手里空空,沒有煙沒有酒,只能干地坐著。
監獄的第一個夜晚,特別難熬,特別漫長,一晚如同一生。
薄司寒坐到了天亮,依然沒有困意。
但白天和黑夜對他來說沒有任何區別,因為他能看到的只是鐵門外一條狹窄的通道和那面墻。
如果非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人在夜晚的時候更容易傷,所有不好的緒在夜晚統統都發出來了。
換白天,起碼還能到那麼一點微弱的希,還有一點盼頭。
呵,可笑。坐牢的人,一無所有的人,還在期盼什麼?
監獄的第二晚。
薄司寒出乎意料地睡著了。
也許能兩天一夜沒合眼了,撐不住了。
這一次,他睡得很沉,睡夢中,他好像看到了溫言。
那張刻進骨子里的漂亮臉蛋浮現在他面前,他很開心,手要去,卻什麼也不到。
他和溫言之間隔了一層障礙,他不到,但溫言卻能到他。
這種覺,很難。
溫言纖細修長的手指,著薄司寒的臉頰,在他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話,“薄司寒,你知道我的愿是什麼嗎?”
薄司寒急切地問,“是什麼?小言,快點告訴我,我幫你實現。”
溫言的聲音很冷漠,“如果,有下一輩子,我希我去到一個沒有你的人間。”
薄司寒搖頭:“不,小言,下一輩子我們還要在一起,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猜你喜歡
-
完結391 章
閻王愛上女天師
白梓奚只是隨師父的一個任務,所以去了一個大學。奈何大學太恐怖,宿舍的情殺案,遊泳池裡的毛發,圖書館的黑影……白梓奚表示,這些都不怕。就是覺得身邊的這個學長最可怕。 開始,白梓奚負責捉鬼,學長負責看戲,偶爾幫幫忙;然後,白梓奚還是負責捉鬼,學長開始掐桃花;最後,白梓奚依舊捉鬼,然而某人怒摔板凳,大吼:哪裡來的那麼多爛桃花,連鬼也要來?白梓奚扶腰大笑:誰讓你看戲,不幫忙?
33.8萬字5 34513 -
完結1074 章

我渣了死對頭的哥哥
司西和明七是花城最有名的兩個名媛。兩人是死對頭。司西搶了明七三個男朋友。明七也不甘示弱,趁著酒意,嗶——了司西的哥哥,司南。妹妹欠下的情債,當然應該由哥哥來還。後來,司南忽悠明七:“嫁給我,我妹妹就是你小姑子,作為嫂嫂,你管教小姑子,天經地義。讓她叫你嫂子,她不聽話,你打她罵她,名正言順。”明七:“……”好像有道理。司西:“……”她懷疑,自己可能不是哥哥的親妹妹。
90.2萬字8 35281 -
完結462 章

傅爺的王牌傲妻
寧洲城慕家丟失十五年的小女兒找回來了,小千金被接回來的時灰頭土臉,聽說長得還挺醜。 溫黎剛被帶回慕家,就接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警告。 慕夫人:記住你的身份,永遠不要想和你姐姐爭什麼,你也爭不過。 慕大少爺:我就只有暖希這麼一個妹妹。 慕家小少爺:土包子,出去說你是我姐都覺得丟人極了。 城內所有的雜誌報紙都在嘲諷,慕家孩子個個優秀,這找回來的女兒可是真是難以形容。 溫黎收拾行李搬出慕家兩個月之後,世界科技大賽在寧洲城舉辦,凌晨四點鐘,她住的街道上滿滿噹噹皆是前來求見的豪車車主。 曾經諷刺的人一片嘩然,誰TM的說這姑娘是在窮鄉僻壤長大的,哪個窮鄉僻壤能供出這麼一座大佛來。 兩個月的時間,新聞爆出一張照片,南家養子和慕家找回來的女兒半摟半抱,舉止親暱。 眾人譏諷,這找回來的野丫頭想要飛上枝頭變鳳凰,卻勾搭錯了人。 誰不知道那南家養子可是個沒什麼本事的拖油瓶。 南家晚宴,不計其數的鎂光燈下,南家家主親自上前打開車門,車上下來的人側臉精緻,唇色瀲灩,舉手投足間迷了所有女人的眼。 身著華服的姑娘被他半擁下車,伸出的指尖細白。 “走吧拖油瓶……” 【女主身份複雜,男主隱藏極深,既然是棋逢對手的相遇,怎能不碰出山河破碎的動靜】
176萬字8.46 260012 -
連載120 章

限時閃婚:傅少追妻不要臉
閃婚一個月后的某一晚,他將她封鎖在懷里。她哭:“你這個混蛋!騙子!說好婚后不同房的……”他笑:“我反悔了,你來咬我啊?”從此,他食髓知味,夜夜笙歌……傅言梟,你有錢有權又有顏,可你怎麼就這麼無恥!…
20.6萬字8 11589 -
完結8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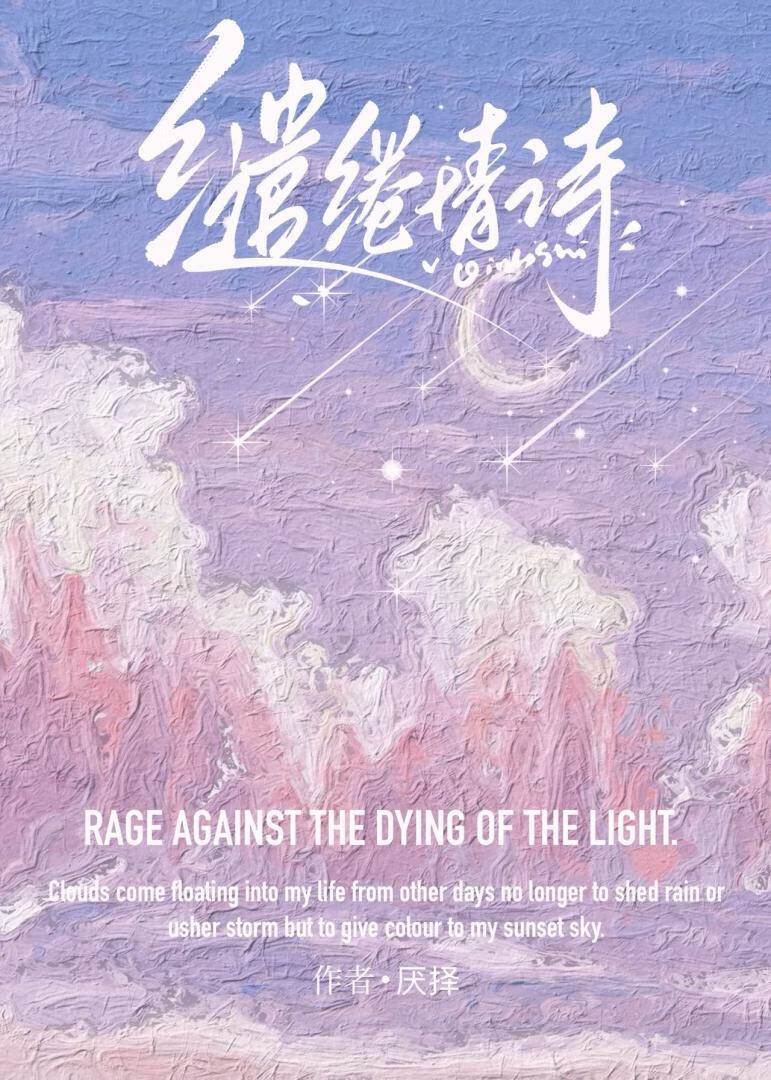
繾綣情詩
謝祈音從小泡在蜜罐子里長大,除了婚姻不能自主外可以說是過得順風順水。 未婚夫顧時年更是北城權貴之首,條件優渥至極。即使兩人毫無感情,也能護她餘生順遂。 可這惹人羨豔的婚姻落在謝祈音眼裏就只是碗夾生米飯。 她本想把這碗飯囫圇吞下去,卻沒想到意外橫生—— 異國他鄉,一夜迷情。 謝祈音不小心和顧時年的小叔顧應淮染上了瓜葛。 偏偏顧應淮是北城名流裏最難搞的角色,不苟言笑,殺伐果決。 謝祈音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小命和婚後生活的幸福自由度,決定瞞着衆人,假裝無事發生。 反正他有他的浪蕩史,她也可以有她的過去。 只是這僥倖的想法在一個月後驟然破碎。 洗手間裏,謝祈音絕望地看着兩條槓的驗孕棒,腦子裏只有一個想法。 完了,要帶球跑了。 - 再後來。 會所的專屬休息室裏,顧應淮捏着謝祈音細白削瘦的手腕,眼神緩緩掃至她的小腹,神色不明。 “你懷孕了?” “誰的。”
26.2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