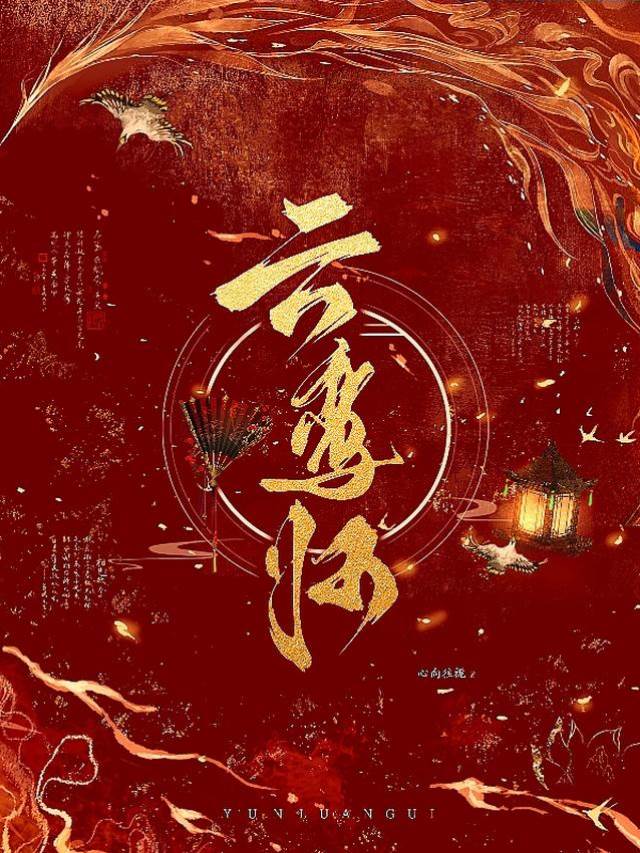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白月光小將軍他人設崩了/嫁給前朝小將軍》 第20章
第20章
謝苗兒一窘。
扭了扭自己的手指,道:“人如何知曉自己在夢裏說了什麽?我猜不到。”
秀氣的眉都耷下去了,瞧著就蔫蔫的。
陸懷海原是想看赧的樣子,眼下願達,他卻來不及竊喜,只覺把自己被無條件的信賴架到了火堆上,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剛剛理布坊的事時,放出氣勢來,連做了幾十年生意的程遠道都被收得服服帖帖的。
可眼下他隨口編了句瞎話逗,卻一點沒看出來。
就這麽相信他?
陸懷海悄悄嘆氣,一點逗的心都沒了,隨即道:“我騙你的。”
謝苗兒眼神撲朔,似有狡黠的閃過,說:“小爺,你不用替我圓場。今晚回去,我捂著自己的睡,絕對不吵你了。”
聞言,陸懷海幾乎是哭笑不得,“當真只是逗你,別多想。”
西城的市井氣比東城更濃重,街巷裏人聲嘈雜,陸懷海聽見謝苗兒若有似無地“哦”了一聲,他一垂眼,卻見的腦袋比先前埋得更低,梳得高高的椎髻幾乎都要到地上去了。
看起來很沮喪的樣子。
陸懷海良心不安,一面又替覺得那發髻墜得頭皮都痛,便拿胳膊肘了,道:“惱我了?”
了一會兒也沒反應,頭上的素銀釵子一顛一顛的,就像哭了一樣。
這樣棘手的場面是陸懷海理不來的,他暗道,小姑娘就是麻煩,隨便逗了兩句就掉眼淚,以後再也不招了。
他了自己的掌心,邦邦地說:“別惱,請你吃……”
陸懷海瞥了一眼路邊的小攤,繼續道:“請你吃貓耳朵。”
“我不想吃,”小姑娘聲音悶悶的,“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小爺,你一定要回答我。”
Advertisement
陸懷海已經丟了幾個錢與小販,買了兩份,塞了一份到謝苗兒手裏,“你問。”
這便宜零沒有紙包來裝,小販拿摘來的葉子盛。
上說不吃,但謝苗兒還是接過了。
終于擡起了頭,陸懷海看臉上一點悲傷的痕跡也沒有,恍然發覺也在逗他。
謝苗兒臉上寫滿了求知,從善如流地問了:“小爺,我想知道,馬上風是什麽意思?”
開蒙讀書時,有一個句讀理不清,都會纏著問謝太傅半天。先前文英神神地捂,讓對這個陌生的詞愈發好奇了。
陸懷海還沒從被反將一軍的驚訝裏緩過神,就被的問句問了個措手不及。
兩人并肩而行,謝苗兒沒瞧見陸懷海形一僵,自顧自地念叨著:“我只聽說過卸甲風。卸甲風是將軍打完仗,回營帳就了盔甲,風而死,那馬上風,說的是下馬後力而死嗎?”
陸懷海不是個臉皮厚的,這種事如何和直接解釋?耳聽得猜得越來越離奇,他終于忍無可忍,打斷了的猜想,道:“你……算了,回去同你說。”
謝苗兒乖覺地閉,快步跟在陸懷海後。
咦?
他耳朵怎麽紅了?
謝苗兒不明白。
——
杜家村裏,一個布麻的婦人正在小河旁捶打。
謝苗兒的繼母、杜氏窩著火,一下捶的比一下用力。
男人死了,現在帶著兩個娃娃住在兄嫂家,兄嫂嫌他們吃閑飯,正想把再嫁了。
杜氏著氣,憤憤地漂完服,提著沉重的簍子往回走。
夕西下,村裏的人家紛紛起了炊煙,都沒什麽葷腥味,不是農忙的時候,有茶飯吃就不錯了。
杜大郎家卻是冷鍋冷竈。
杜氏沉著臉走回去,才進門,謝金福前頭娘子留下的五歲兒子謝藤,和自己親生兒謝瑩兒,一大一小兩娃娃就來抱大,都嗷嗷喊。
Advertisement
見回來,杜大郎斜眼覷,說道:“鍋裏還有粥,你自個兒熱熱吧。”
杜氏看見旁邊的侄子侄,一個喊的都沒有,正安安靜靜地玩著泥,一看邊還有殘存的油漬,就知他們是吃過了的。
下心頭的火,牽著謝藤和謝瑩兒去了竈房。
所謂稀粥寡淡得像刷鍋水,撿個石子兒都能在鍋裏玩打水漂。
杜氏終于忍不住了,提起菜刀沖到了堂屋,直接一刀剁在了杜大郎眼面前。
“前些日子才給你們拿了銀子回來,今日一口飯都沒了?”
杜大郎卻一點也不慌。
他這個妹妹脾氣比本事大,回回都鬧,回回都被他拿得死死的。
杜大郎說:“不幹活的,誰家不是這麽吃的?好妹妹,你要吃你大哥的骨髓不?你若待不下去,就走吧,哥哥也不留你。”
這話拿住了杜氏的命門。
爹早死,就一個老娘半癱在床上跟著杜大郎,杜氏帶著孩子,除了杜大郎這兒,連落腳的地方都沒有。
“從我嫁到謝家,何時短過你們東西了?前前後後不知補了你們多,眼下你倒嫌棄起我了。”
杜氏眼淚說掉就掉,杜大郎看了厭煩。
不過今日有人找他談了一筆合算的生意,他還是耐著子同杜氏說道:“好妹妹,有一件事,只要你做了,日後你和孩子還是能回城過好日子。”
杜氏尖:“把我嫁給老頭子做妾,你想都不要想!”
杜氏的事杜大郎門清,他冷哼一聲:“你前幾天找人遞信想跑回城,我不跟你計較,你那便宜兒在城裏又如何,當了別人的妾,手底下縱然有點銀子,但謝家的産業房子都賣了,別指著能接你回去了。”
心思被穿,杜氏眼神一閃,嫁給謝金福那幾年,因為那前頭的大兒謝苗兒,乖得很又勤快,連家務事都甚持。
Advertisement
杜大郎繼續道:“張端死了,你知道嗎?”
張端?
杜氏倒吸一口涼氣,還沒來得及為這個害死丈夫的人橫死而好,就聽見杜大郎說:“他娘張夫人就這麽個兒子,你便宜兒做了陸小爺的妾,覺得是陸小爺害死了他,要我們幫一個忙。事後銀子好說。”
杜大郎把張夫人要他們做的事說來,杜氏聽了,慌擺手。
急道:“這種喪良心的事,做了會禍子孫的!”
杜大郎終于不再掩飾他的臉,直白威脅:“你有旁的選嗎?長兄如父,我讓你給陳員外做妾都是擡舉你!乖乖聽話,想想你的瑩兒。”
來完的,他又放低聲音來的:“我這個做哥哥的,是為你們好。這件事妨害不到你們,最多是那便宜兒以後日子難過,但親弟弟如今都是你在養,吃虧了也是當還你的債。以後你帶著兩個孩子,拿上錢重新立戶,日子好過得很。”
杜氏瞳孔閃爍,不知將杜大郎的話聽進去了幾分。
——
陸懷海帶著謝苗兒去衙門更改了契書的所屬,換了的名字。
謝苗兒如今弟弟妹妹都還小,是長姐,持這些也很正常。
衙門裏管文書契約的小吏忙得不可開,謝苗兒在旁一聽,發覺最近賣房屋産業的人極多,很是意外。
陸懷海垂下眼眸,解釋道:“倭患越來越兇,很多人想搬到離海更遠的地方去。”
回去之後,為了避免繼續纏著自己問“馬上風”是什麽意思,陸懷海久違地回了自己的屋裏,從書房中挑出本醫書,翻到某一面,折了角送到謝苗兒那去了。
謝苗兒見他送醫書來,一開始還不解其意,直到一行行讀過,終于明白了什麽馬上風之後,臉已經比的桃還要紅了。
那日陸懷海微紅的耳和比起來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
——男子氣上湧,卒于行房,謂之馬上風。
什麽啊!謝苗兒憤得幾乎要死掉了。都纏著陸懷海問了些什麽?
足足把自己埋在枕頭裏冷靜了一刻鐘。
平生第一次,謝苗兒發現有時候好奇心太旺盛也是缺點。
隨後的幾天裏,兩人極其默契地都沒有再提起這個話題。
又一天晚上,陸懷海照常來到這裏。
今天他來得很早,謝苗兒才從東苑回來,陪陸寶珠玩耍了一下午。
晚飯後,月憐收拾了碗筷,而陸懷海卻沒有和往常一般坐不住,他定定地坐在桌前,雙手撐在膝蓋上,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樣。
見他好像有話要說,謝苗兒也就沒。
陸懷海略作思考後才開口,他說:“有件事,想問問你的意見。”
他補充:“不是我,是我一個朋友的事。”
謝苗兒有些詫異,說:“什麽事?”
陸懷海專注地看著的眼睛,說道:“我有個朋友,他想要投軍。”
作者有話說:
你說的那個朋友是不是你自己.jpg
謝投出地雷的小天使:阿小鍋同學 1個;
謝灌溉營養的小天使:阿諾裏斯本汀 6瓶;
非常謝大家對我的支持,我會繼續努力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179 章

毒妃駕到,王爺請賜教
一朝穿越,竟成了個聲名狼藉的草包棄妃。夫君心有所屬,對她棄如敝履。前有綠茶青梅嫁禍,後有囂張公主針對。這麼一手爛牌,且看她如何逆風翻盤,一雪前恥!想她當代特工,手持秘寶相助。下得了毒,醫得了病。文可手撕綠茶白蓮花,武可上陣殺敵平天下。這般寶藏女孩,你不珍惜,自有大把人稀罕。所有人都在問:鎮遠王妃今天和離了嗎?鎮遠王眸色一斂,和離是不可能和離的,這輩子都不可能和離的!想跑?扛回去,跟本王生猴子!
140萬字8 32996 -
完結478 章

狂傲世子妃
一、特工穿越,一夢醒來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絕境之中,各種記憶跌撞而至,雖然危機重重,但步步爲營,看一代特工如何在宮廷中勇鬥百官滅強敵,譜寫自己的傳奇。我狂、我傲,但有人寵著,有人愛,我靠我自己,爲什麼不能。
84.4萬字8 16764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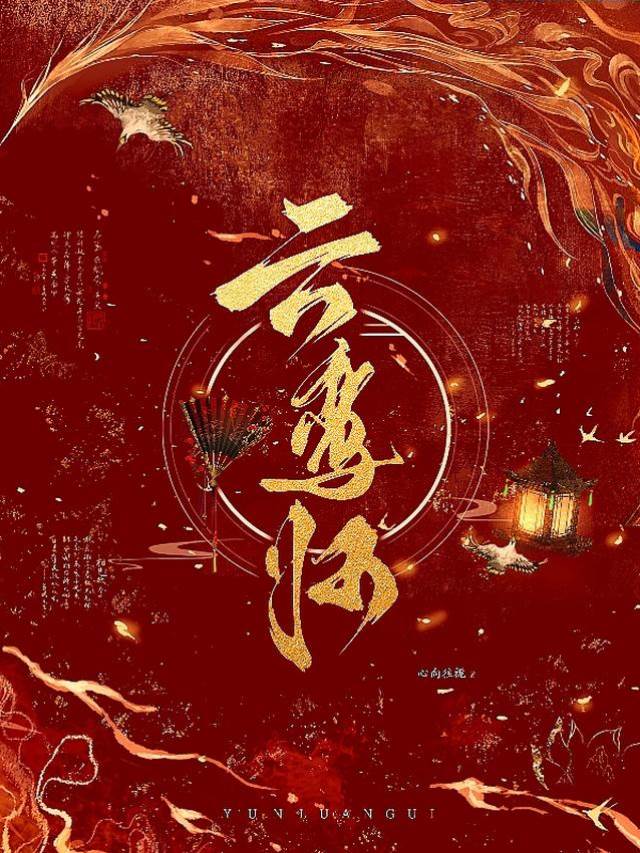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