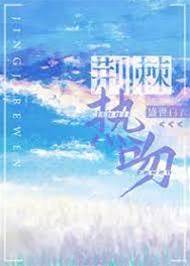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急紅眼!京圈太子爺被甩後徹底淪陷》 第114章 她在Y國
手裡攥著一塊瓷片,使勁向楚寒舟脖頸劃過去。
楚寒舟一把抓住了的手腕,跡順著溫夕的手心流到了楚寒舟手臂上…
他將溫夕手中的瓷片奪過,扔到了後,他的手一把拽住溫夕前的布料,試圖將的服撕開。
傭過來敲門,低下頭,“爺,小姐暈過去了。”
楚寒舟手上作一頓,“等我回來在教訓你。”
說完,他跟著傭快速離開。
溫夕這才鬆了一口氣。
……
另一邊。
顧遠喬開著車停在景灣,“我找溫夕。”
小棠聽見靜,出來後正好看到站在門外的男人。
“溫小姐不在家。”
“不在家?”
顧遠喬正在說什麼,就看到許肆渾戾氣的走了出來。
許肆也注意到了他,“顧遠喬?”
顧遠喬攔住要走的許肆,“溫夕呢?我要見。”
許肆剛得到訊息,溫夕人在Y國,他要抓時間過去。
耽擱一秒,楚寒舟那個瘋子不知道會做出什麼事。
“不在。”
顧遠喬再次將人攔住,看著許肆的態度猜測,“你跟吵架了?”
“這跟你有什麼關係?”許肆對著顧遠喬彷彿有一種天生的敵意。
Advertisement
顧遠喬失笑,“你不會…把我當敵了吧?”
顧遠喬眼神異常認真。
許肆的臉瞬間沉如水,這也讓顧遠喬證實了自己的猜測。
顧遠喬緩緩靠近許肆,低聲說:“如果真是這樣,那你就猜錯了…”
“我對小丫頭並不興趣。”
說完,他輕輕拍了拍許肆的肩膀,“說吧,人在哪兒?我有急事兒找。”
旁邊的江七小聲說:“許總,Y國咱們沒有人脈,要是去了只能搶,恐怕會損失慘重。”
“Y國公爵羅南·格雷索恩的妻子是顧總的姐姐。”
許肆看了顧遠喬一眼,“跟我來吧。”
兩個人上了車,“溫夕在Y國。”
顧遠喬有些震驚,“Y國?怎麼去國外了?”
許肆提到這兒,拳頭攥,“是被楚寒舟帶走的。”
他不應該讓一個人回溫家的。
“什麼?”
圈子裡的人多多都聽過楚寒舟和許肆之前的恩怨。
顧遠喬皺眉,“什麼時候的事?你就不會照顧好嗎?”
許肆無力的靠在椅背上,“我當時去了F國。”
顧遠喬想到那張楚楚可憐的臉,語氣不明,“也是…我差點忘了,我那個外甥最近做了手。”
Advertisement
他轉頭問道:“鎖定他們的位置了嗎?”
江七控著電腦,回答:“暫時沒有,那邊人手不夠…我剛調了人過去。”
“等你們的人在過去就太晚了。”說著,顧遠喬拿出手機找到了一個電話。
那邊剛接通,就傳來溫潤的男聲,“小舅舅怎麼想起給我打電話了?”
顧遠喬直主題,“阿宵,幫我找個人。”
“誰?”
“溫夕,一個華國孩。”
沈宵聲音著笑意,“小舅舅,你這萬年不聯絡我一次,上來就是找人,怎麼看上人家了還是把人家嚇跑了?”
顧遠喬之前跟這個外甥相的還算不錯,畢竟相差不了多歲。
只是後來他們都逐漸忙了起來,聯絡就了。
“阿宵,別開玩笑了,抓找人。”
沈宵漫不經心的又問了一句,“你說什麼?”
“溫夕。”
聽到這個名字後,沈宵微微攥了手機。
那會兒他不過是想到自己妹妹,所以勸了季思純一句幾句。
結果就哭哭啼啼的。
跟他說了一大堆…
自然也在季思純那裡聽到了溫夕的名字。
“不找。”
顧遠喬微微蹙眉,“阿宵。”
Advertisement
沈宵一無能為力的語氣,“小舅舅,我不在Y國。”
“阿宵,你必須找…不然你會後悔。”
沈宵嗤笑,“我後悔什麼?左右一個無關要的人。”
“我發給你一個東西你看看,再決定找不找。”
說完,顧遠喬結束通話了電話,將手機裡儲存的東西發給了沈宵。
許肆抬腕,囑咐江七,“讓江六帶著人去搜楚家在Y國的所有產業,小心點…別打草驚蛇。”
“別擔心,我這個外甥會幫忙的。”
顧遠喬的手機響了,是沈宵打來的電話。
他沒接。
這小子偶爾也欠教訓…
訊息彈來:
【小舅舅,是真的嗎?人在哪兒?出什麼事兒了?】
隔著螢幕都能察覺到沈宵的緒。
【楚家,趕找人。】
顧遠喬打了幾個字過去,沈宵那邊比了一個大大的“ok”。
許肆手指挲戒指,心思早就飄去了Y國,“你為什麼這麼關心溫夕?”
顧遠喬聽著他酸溜溜的語氣,“不會還當我是敵吧?”
他沉片刻,“我看了那天的直播。”
“我懷疑溫夕是我姐姐的兒,所以儘快找到。”
許肆聽他一說,皺著的眉頭鬆散,“季家?還是…”
…
飛機降落後,一個男人快步朝著他們走來。
沈宵沒有戴眼鏡,顯得整個人凌厲了不。
“小舅舅。”
沈宵往前跑了幾步,倒也沒了教授的架子,“不是不在Y國?”
他說:“剛下飛機。”
沈宵在看到東西以後就聯絡了私人飛機。
顧遠喬勾,滿意的看了一眼,“作快。”
“位置鎖定了嗎?”
沈宵拿出手機指看到一個位置,“嗯,剛發來的…是Y國一個小城鎮,在南邊。”
“只是…那邊深就是森林了,到時候我們分三路搜尋。”
許肆的人也趕來了,他抬眸,“那就趕出發吧!”
…
楚寒舟給楚寒涵請了醫生,就回到了客廳。
溫夕被兩個大漢看管著,本沒機會跑出去。
他蹲在溫夕前,“夕夕,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遊戲‘了。”
的臉上、上都有傷。
上的服也被楚寒舟撕開了一個大口子。
男人語氣心疼,“非要跑,吃苦頭了吧?”
砰。
門被人力撞開。
楚寒舟一臉不耐的抬起頭,誰活的這麼不耐煩了,這種時候來打擾他。
猜你喜歡
-
完結1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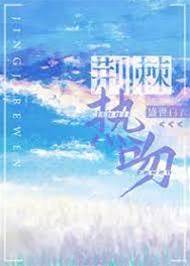
荊棘熱吻
季弦星有個秘密,她在十六歲的時候喜歡上了一個人——她小舅的朋友,一個大她八歲的男人,后來,無論她怎麼明示暗示,鐘熠只當她是小孩。她安靜的努力,等自己長大變成熟二十歲生日那天,她終于得償所愿,卻在不久聽到了他要訂婚的消息,至此她一聲不響跑到國外做交換生,從此音訊全無。再見面時,小丫頭長的越發艷麗逼人對著旁邊的男人笑的顧盼生輝。鐘熠走上前,旁若無人的笑道:“阿星,怎麼見到我都不知道叫人了。”季弦星看了他兩秒后说道,“鐘先生。”鐘熠心口一滯,當他看到旁邊那個眉眼有些熟悉的小孩時,更是不可置信,“誰的?”季弦星眼眨都沒眨,“反正不是你的。”向來沉穩內斂的鐘熠眼圈微紅,聲音啞的不像話,“我家阿星真是越來越會騙人了。” 鐘熠身邊總帶個小女孩,又乖又漂亮,后來不知道出了什麼事,那姑娘離開了,鐘熠面上似乎沒什麼,事業蒸蒸日上,股票市值翻了好幾倍只不過人越發的低沉,害的哥幾個都不敢叫他出來玩,幾年以后,小姑娘又回來了,朋友們竟不約而同的松了口氣,再次見他出來,鐘熠眼底是不易察覺的春風得意,“沒空,要回家哄小孩睡覺。”
51.8萬字8.18 232480 -
完結522 章

沫沫生情霍少寵妻如命
沐家見不得人的私生女,嫁給了霍家不能人道的殘廢二少爺。一時之間,滿世界都在看他們的笑話!然而,夜深人靜之時,某女扶著自己快要斷掉的腰,咬牙切齒!“霍錦廷,你不能人道的鬼話,到底是特麼誰傳出去的?!”————————整個桐城無人不曉,雲沫是霍錦廷的心頭寶。然而許久以後雲沫才知道,一切的柔情蜜意,都不過是一場陰謀和算計!
56萬字8 50687 -
完結102 章

是禍躲不過
林荍從小在霍家長大,為了在霍家生存下去,只能討好和她年紀相差不大霍家二少爺。 霍圾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做什麼都是第一,斯斯文文從不打架,不發脾氣,不抽煙,不喝酒,沒有任何不良嗜好,溫柔體貼,沒有缺點…… 可只有林荍知道她討好的是一條溫柔毒蛇。 林荍:“你到底想怎麼樣?” 霍圾摘下眼鏡,斯文輕笑,“姐姐不愛我,為什麼對我笑?” 一句話簡介:腹黑年下的占有欲
29.7萬字8 39025 -
完結452 章

偷生豪門繼承人,被大佬溫柔誘哄
【萌寶 馬甲 雙重身份】那一夜,她走投無路,闖入司家植物人房間,把人吃幹抹淨逃之夭夭。五年後,她攜寶歸來,第一時間就是和孩他爹的雙胞胎弟弟劃清界限,不想他卻丟過來一份醫學報告,“談談吧。”“談什麼?”男人將她堵在牆角,“撫養權,戀愛,你自己選。”這還不算完,她的四個小祖宗一下子給自己找出來兩個爹!沈歌謠蒙了,她睡得到底是誰?男人直接把她按住:“既然不記得了,我幫你好好回憶回憶!”
50.2萬字8 371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