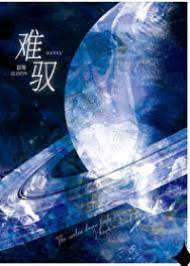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疏離童話》 第44頁
“懷生,怎麼了?”
“你不是回北縣了嗎?”
周懷生并未回答任原這兩句話,單刀直切話題。
“蔣澈……”他頓了頓,“他現在還在醫院嗎?”
幾番猶豫不決,周懷生到底還是問了,他這人表面裝大度,其實自走后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盡管他也不知道自己現在到底有什麼可怕的。
可他還是覺得,不問他這一次不能放心。
那旁的任原笑了笑,“我以為你找我是什麼事,合著是打聽他啊?”
他在心里暗詡周懷生沒出息,但也能明白人之心令人盲目無措,于是如實同他代。
“他兩周前就辭職了,我聽人說他跟那朋友也鬧掰了,他們科的人說他回了老家,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畢竟醫院這麼大。”
任原實話實說,也很有分寸,多余的話一句不問,解答完他的問題就再也不多說一句,周懷生說了句謝了,掛斷電話后卻失了神。
他降下車窗,過分練地從儲格里拿出一盒煙。周懷生知道的,他擔心的不是蔣澈,而是他自己。他這雙眼曾見過溫姝宜熱烈真摯向一人時的,見過這段青懵懂的初次悸,他怕什麼呢,他怕溫姝宜有朝一日回頭看看,發現自己對他不過是敗于現實而妥協的事實。
Advertisement
那這樣的婚姻,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呢?
*
溫姝宜并沒想好再見老同學應該如何開場,不過剛進包間,張倩就興沖沖起迅速走到跟前,熱地拉起的手臂。
“咱們班花來了啊,大家快歡迎歡迎!”
溫姝宜迎著目去看,滿桌座無虛席,三十個座位幾乎全滿了,倒還真是一次齊全的同學聚會,就連蔣澈也在其中。
他穿了件淺,淡然坐在幾個發福的了男同學之中,一眼看上去竟有種別樣的松弛和安靜。
盡管,覺得他從來都不是個松弛的人。
“大家好久不見。”
溫姝宜客套一句后落了座,只剩下一個空位,也不知道是誰安排的,蔣澈就在左手邊。
一坐下,旁便響起不大不小的起哄聲,上學的時候大家都知道他們兩個之間的關系,多年過去時過境遷,卻也逃不過被人戲弄。
溫姝宜不喜歡這樣的方式,主將椅子往外面挪了挪,目不斜視,從進門到現在并未看向蔣澈一眼。
是漠視,又像是毫不在乎。
這一作落旁的蔣澈眼中,他的臉幾乎是瞬間就暗了暗。
Advertisement
“我們姝宜現在可是不好請,要不是我前幾天在超市見跟老公,恐怕還不能見到呢。”
張倩主說是自己邀請,但眾人的注意力很快被旁的事吸引了。
“姝宜你結婚了啊?”
“什麼時候的事,怎麼都沒通知我們一聲,大家都可高興參加這樣的喜事了。”
“對了,那你老公今天怎麼沒來?”
幾個同學嘰嘰喳喳說起來,一言一語十分熱鬧,安靜坐在一旁,并未打算回答,但有時候越安靜,反而越給旁人刨問底的機會。
眼下實在不是個適合八卦私事的好時機,找了個空子,不給旁人過多窺及的機會。
“也是前不久的事,過陣子辦酒了我會告訴大家的。”
至此,再不多言,只坐在一旁看著大家七八舌的跟說起這些同學的近況。
有人家,有人創業,也有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日復一日做些自己厭煩但逃離不開的工作。大家看起來都不怎麼快樂,借著酒杯述說著各自的艱難和不如意,倒是難得真誠熱烈的一副場景。
大概人長大的代價是要舍棄一些緒。年人連開心的時間都之又,更別提從前義薄云天提起的理想。那些在年時被高高吊起的水晶夢想到了如今也只能是酒杯撞破碎的聲音。
Advertisement
一頓飯下來,溫姝宜說得寥寥無幾,倒是聽了旁人的許多故事,聽著,看著,覺得人長大真是沒什麼意思。
蔣澈也跟這些人喝起酒來,杯杯的白酒落了肚,人也開始不太清醒,溫姝宜坐在他旁邊,每一次手夾菜,他都能看到他手上過于晃眼的鉆戒。
那顆閃耀的石頭像一把鋒利的刀尖,在下,在眾人視線中明晃晃他肺腑深。
他旁的男同學也快醉了,看蔣澈的目一直在溫姝宜跟著流連,他借著鬧哄哄的氣氛對他開了口。
“你倆當年為什麼分手啊?”
聲音不高不低,離得遠的人或許聽不清,但溫姝宜清清楚楚一個字都聽到了。
屋悶得很,如坐針氈,也不想再聽這樣的話,找了個借口先走了。
出了鬧哄哄的包間,蔣澈卻跟在后一起走了出來。
溫姝宜停下腳步,回頭看看,蔣澈也停下腳步,站在走廊墻邊離不遠。
他五很好,即使是在頂下也并不遜分毫,分開這四年,他確確實實長不,以前看起來弱不風,現在,上倒也有棱角了。
環境,環境最造就人。
“這就走了?”
他開口,話音懶散,是喝了酒后的模糊,有幾分頹然。
連帶著看向時的眼神也不太清明。
“不走在這干什麼,看一群別有用心的人跟你聊過去談嗎?你知道,我沒這麼閑。”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870 章

大佬的大佬甜妻
一次意外,她救下帝國大佬,大佬非要以身相許娶她。 眾人紛紛嘲諷:就這種鄉下來的土包子也配得上夜少?什麼?又土又丑又沒用?她反手一個大……驚世美貌、無數馬甲漸漸暴露。 慕夏隱藏身份回國,只為查清母親去世真相。 當馬甲一個個被扒,眾人驚覺:原來大佬的老婆才是真正的大佬!
169.3萬字8.33 11991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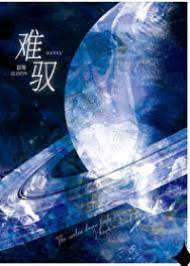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879 章

閃婚秘寵:首富大佬愛妻入骨!
為了擺脫原生家庭,她與陌生男人一紙協議閃婚了!婚后男人要同居,她說,“我們說好了各過各的。” 男人要豪車接送她,她說,“坐你車我暈車。” 面對她拒絕他一億拍來的珠寶,男人終于怒了,“不值什麼錢,看得順眼留著,不順眼去賣了!” 原以為這場婚姻各取所需,他有需要,她回應;她有麻煩,他第一時間出手,其余時間互不干涉…… 直到媒體采訪某個從未露過面的世界首富,“……聽聞封先生妻子出身不高?”鏡頭前的男人表示,“所以大家不要欺負她,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些千金富太太渣渣們看著他驚艷名流圈的老婆,一個個流淚控訴:封大首富,到底誰欺負誰啊!
163.7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