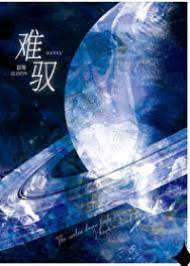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親愛的暴食癥女孩》 章四十 夢境與現實
紀蘭楨醉得厲害,但不妨礙眼睛像嬰兒一樣晶晶亮眨啊眨地瞧著鄭麒。
臉此刻因為酒意,整個都是紅撲撲的。
“我們回去吧。”
“休息好了?”鄭麒問道。
坐在椅子上的小孩乖巧不已,點點頭,然后像下了什麼重大決定:
“我們走回去好不好?”
哪有好不好?他現在心都快要化了。
鄭麒走之前跟老板打了聲招呼。從飯店出來,第一眼就是紀蘭楨。
站在人群的近,旁邊是熱熱鬧鬧的食客。眾人頭頂上都冒著白氣,升騰并接照不到的上空。
而,安安靜靜的,有點嬰兒的臉,還有鹿兒般純凈的眼睛,一瞬不眨地盯著飯店門口。看見他出來眼睛頓時亮了,像藏有無數的星星。
只在等他。
江邊有風,鄭麒顧著,一起慢慢走過江橋。
一明月皎潔,朗朗照在江面上。觀景燈五六,把橋也照得像個仙。
江水就更別提了,江聲沉如裂帛,讓人以為遠是浪打著浪,等它像個醉漢似的栽到跟前,結果發現還是如同褶皺的波痕,才能辨出它綠松石一樣的。
“好看。”紀蘭楨說話還是有點鈍重。
江天云影里,霓虹燈下的年個子顯得更為頎長。他側著臉角噙著笑意,語氣淡淡:
“紀蘭楨,你最近是在躲我嗎?”
紀蘭楨人僵了下,子。
Advertisement
“沒有啊——”然后自言自語:“好冷。”
拙劣的演技沒有逃鄭麒的火眼金睛,只是他沒再繼續問下去。而是把自己的校服了,蒙頭罩在紀蘭楨上。
鋪天蓋地的雪枝松香,暖意從各而生。
“謝謝。”
視野被服罩得一片晦暗,但并不妨礙知道他在哪。
鄭麒沒接話。
酒醒了就不撒了,反倒還沒剛才喝醉了坦誠。
他心里全是剛才酒窩里盛滿酒的甜甜笑意,有些懊惱,早知道就不攔著喝了。
紀蘭楨被鄭麒送回學校后,回到宿舍倒頭就睡。
次日清晨和往常一樣的鬧鐘響了,睡眼惺忪地摁掉鬧鐘,拿了牙刷牙杯去洗漱臺洗臉。
一抬頭人不怔住了。
那是自己嗎?
鏡子里的自己雙眼無神,臉很腫,下、額頭還長了幾顆紅腫的痘痘。
是昨晚吃了烤串的緣故?還是見鄭麒之前就已經是這樣了?是頂著這麼一張好丑的臉去見的他們嗎?
冷汗涔涔,一時間竟然忘記了自己原來的規劃。
——幾點了?
換,理書包,手忙腳地出了宿舍,整個走得風風火火。
快七點十分了,今天本來想再背篇英語小作文的,時間來不及了。文綜卷還有一套要訂正的,得先回去做那個。
肚子怎麼有點,算了,昨晚吃多了今天早飯就別吃了。
從宿舍跑到教室,短短十分鐘路竟然跑出了種短跑沖刺的覺。
Advertisement
可人到了,的心還是沒能坐定。筆盒書卷“哐當哐當”,跟一起合演了一場早已了節奏的稽喜劇。
一晃中午的飯點也過了,早已的前后背。
吃什麼?有點饞,包子?面條?酸辣?上次祝繁帶去甜品店,兩人都看中那家的松小貝和酸菌芝士,真想吃啊。
好。
這是暴食的前兆。
盡力避免,但再次清醒面對的只有拆開的和沒拆開的食渣滓。
不敢被別人發現,只有吃完一家再下一家,到后來舌尖早就沒有覺了,但大腦還在控進食。即使是茶店里摻了香的免費飲料,在食快要漫到嗓子眼的況下還是喝掉了。
怎麼辦?的頭腦發漲發酸,這樣怎麼見人?
吐掉。
大腦變得遲緩,的心跳驟然加快,腦袋里只有“嗡嗡”的鳴。
走到宿舍拿起牙刷,把尖端抵住自己的嚨,跟之前做的一樣——
“不要!”
紀蘭楨大喊一聲,從床上掙扎著坐起來。
宿舍窗簾被人掀開了,和鳥鳴說明今天是個好天氣。
紀蘭楨頭昏腦漲,手還抓著棉被一角,顯然還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樣子。
那個夢、太真實了,以為自己真的要去催吐了……
想到這里,看了看自己手,沒有牙印。
那是給自己設下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線。
紀蘭楨松了口氣,看了看手機繼而環顧四周。
Advertisement
八點十分,宿舍里沒有一個人。
明天就是月考的日子。
……
教室門口的考場安排表沒有好,在愈演愈烈的寒風的威下,終于飄落在水泥地上,而紀蘭楨看到了落在地上的那紅一角。
這是心神最不安定的一次考試。往常從來不會注意到除了試卷以外的東西,可這次卻狀況頻出:
考語文時男監考老師中途出去過,還窩在墻角和別人說話;考數學不知怎麼有條狗從教室門前經過……
的腦子不能很好地集中在題目上,胡思想,上又冷汗直冒。
不知道為什麼事會演變這樣。
卷子上的試題是從沒有過的陌生,幾乎每一道題檢索腦中的知識庫,檢索出來的都是“此題為空。”
心如麻。
卷鈴聲宣告著所有一切都結束了。上考卷的前一秒,掃一眼試卷,才發現英語完型第十一個空沒有填。
這意味著后面的順序全錯了。
一瞬間幾乎頭暈目眩。
考試結束,同學們三五一群都收拾東西準備去吃飯。祝繁卻見到紀蘭楨趴在窗邊,拳頭握。
“怎麼啦?”笑,看起來考試答得不錯:“一場惡戰結束,紀蘭楨勇士怎麼不去補充一下能量?”
“祝繁,”紀蘭楨強撐著笑:“我好像考砸了。”
“啊。”祝繁的眼睛里劃過一驚詫,但馬上就恢復了臉上的從容:“不會的,你放心。”
像是在給紀蘭楨加油鼓勁:“你這麼努力這麼用功,肯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不要想啊。”
紀蘭楨張口,卻連一個音節都吐不出來。
連回答的勇氣都沒有了。
為了不留在教室,到食堂窗口看到陳列的包子、麻球、炸春卷,卻是連一點食都無。
紀蘭楨拎著書包一個人來到場。
天氣冷可怕,在天場逗留的學生也很寥寥。
紀蘭楨沒管,一個人沿著跑道一圈圈地走,天由昏到暗,卻一直沒停。
猜你喜歡
-
完結1870 章

大佬的大佬甜妻
一次意外,她救下帝國大佬,大佬非要以身相許娶她。 眾人紛紛嘲諷:就這種鄉下來的土包子也配得上夜少?什麼?又土又丑又沒用?她反手一個大……驚世美貌、無數馬甲漸漸暴露。 慕夏隱藏身份回國,只為查清母親去世真相。 當馬甲一個個被扒,眾人驚覺:原來大佬的老婆才是真正的大佬!
169.3萬字8.33 1199148 -
完結485 章

感化暴戾大佬失敗后,我被誘婚了
桑家大小姐桑淺淺十八歲那年,對沈寒御一見鐘情。“沈寒御,我喜歡你。”“可我不喜歡你。”沈寒御無情開口,字字鏗鏘,“現在不會,以后也不會。”大小姐一怒之下,打算教訓沈寒御。卻發現沈寒御未來可能是個暴戾殘忍的大佬,還會害得桑家家破人亡?桑淺淺麻溜滾了:大佬她喜歡不起,還是“死遁”為上策。沈寒御曾對桑淺淺憎厭有加,她走后,他卻癡念近乎瘋魔。遠遁他鄉的桑淺淺過得逍遙自在。某日突然聽聞,商界大佬沈寒御瘋批般挖了她的墓地,四處找她。桑淺淺心中警鈴大作,收拾東西就要跑路。結果拉開門,沈大佬黑著臉站在門外,咬...
87.4萬字8.18 30340 -
完結2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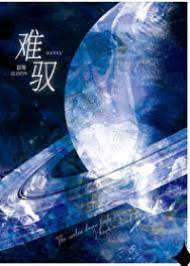
難馭
檀灼家破產了,一夜之間,明豔張揚、衆星捧月的大小姐從神壇跌落。 曾經被她拒絕過的公子哥們貪圖她的美貌,各種手段層出不窮。 檀灼不勝其煩,決定給自己找個靠山。 她想起了朝徊渡。 這位是名門世家都公認的尊貴顯赫,傳聞他至今未婚,拒人千里之外,是因爲眼光高到離譜。 遊輪舞會昏暗的甲板上,檀灼攔住了他,不小心望進男人那雙冰冷勾人的琥珀色眼瞳。 帥成這樣,難怪眼光高—— 素來對自己容貌格外自信的大小姐難得磕絆了一下:“你缺老婆嘛?膚白貌美…嗯,還溫柔貼心那種?” 大家發現,檀灼完全沒有他們想象中那樣破產後爲生活所困的窘迫,依舊光彩照人,美得璀璨奪目,還開了家古董店。 圈內議論紛紛。 直到有人看到朝徊渡的專屬座駕頻頻出現在古董店外。 某知名人物期刊訪談。 記者:“聽聞您最近常去古董店,是有淘到什麼新寶貝?” 年輕男人身上浸着生人勿近的氣場,淡漠的面容含笑:“接寶貝下班回家。” 起初,朝徊渡娶檀灼回來,當是養了株名貴又脆弱的嬌花,精心養着,偶爾賞玩—— 後來養着養着,卻養成了一株霸道的食人花。 檀灼想起自薦‘簡歷’,略感心虛地往男人腿上一坐,“叮咚,您的貼心‘小嬌妻’上線。”
34.9萬字8.57 11698 -
完結879 章

閃婚秘寵:首富大佬愛妻入骨!
為了擺脫原生家庭,她與陌生男人一紙協議閃婚了!婚后男人要同居,她說,“我們說好了各過各的。” 男人要豪車接送她,她說,“坐你車我暈車。” 面對她拒絕他一億拍來的珠寶,男人終于怒了,“不值什麼錢,看得順眼留著,不順眼去賣了!” 原以為這場婚姻各取所需,他有需要,她回應;她有麻煩,他第一時間出手,其余時間互不干涉…… 直到媒體采訪某個從未露過面的世界首富,“……聽聞封先生妻子出身不高?”鏡頭前的男人表示,“所以大家不要欺負她,不然別怪我不客氣。” 那些千金富太太渣渣們看著他驚艷名流圈的老婆,一個個流淚控訴:封大首富,到底誰欺負誰啊!
163.7萬字8 17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